酹酒闻韶话乐土
——济阳大舜文化与中华礼乐精神
胡春雨
题记: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人民富有,而在于它的人民幸福
——孙中山
上篇:古逄奇遇
黄河彼岸的济阳,在我心中,曾经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县;至于属下的曲堤,固然是黄瓜之乡,似乎也算不得大雅之域。当我漫不经心的听到,闻韶台曾经在此矗立,对这片土地立刻燃起了景仰——哪怕今日的闻韶台,依然湮灭在历史的断层中。我这才想起,这里毕竟是五千年来大河哺育的热土,遥想曲折的河堤,岂非浅唱着优美的乐章?
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时代的塌方中,孔子踏上了齐国的土地。《史记·孔子世家》载,在与三桓势力的内讧中,鲁昭公败逃齐国,国家随之陷入动乱。在这并不那么起眼的历史瞬间,却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太史公记载的第一个典故,就是孔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然而,历史长河中无关紧要的高昭子,当时却是齐国公室重臣。郑玄云:“师,乐官,”齐太师也应是诸侯典乐之官——孔子闻韶的故事,似乎更应发生在齐都临淄。惯于疑古的我们,不难否定一切。然而曲堤的土地,埋藏着显赫的前生,容不得后人的无知与傲慢。
远在齐鲁之邦前面的,是东夷古国。早在夏商时代,贵为炎帝后裔的逄氏一族,就在后来的齐国核心区发展壮大,直到商朝初年正式受封,逄国长期位列东夷大国。商朝末年,迫于薄姑压力西迁济阳,在曲堤重建国都。历经商周革命,与周王室缔结婚姻,成为新朝的诸侯。这段历史,为孔子与济阳结缘埋下了伏笔。在济阳人深情的记忆里,当孔子游历齐国,来到曲堤寻访周文王表叔逄公之墓,忽然传来《韶乐》悠悠,从此留下千古回音。中国人是诗意的民族,总是喜欢超越现实的枝节末叶,用诗性的语言为历史传神写照。这在“科学史观”面前,也许没有多少“合法性”可言,却扎根在民族的心灵记忆里。
先君的陵寝,当然属于它的子民。千百年后,曲堤人仍然相信,墓中的神明会在急需时把家什借给子民,只是世人的贪婪阻断了恩泽的施予。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折射出中国式的“神学”:人与神的历史纽带,在于忠厚与惠爱。如今经过考古发掘,证实曲堤古城北面的古墓,正是逄国公族的墓地,并且发现了与周王室通婚的青铜器,其文化遗存可上达与五帝相当的龙山时代。如果说历史的密码,命名龙山文化的城子崖就在曲堤正南方向,舜耕历山的故事就发生在附近。远在广东的韶关,尚在大舜南巡时留下了韶乐,何况在这与历山相望的古城?四千多年来,济南人世代奉祀着大舜,怎能留不下“尽善尽美”的韶乐!
在济南人的历史版本中,曲堤古城西面的石门村,才是《论语-宪问》中子路夜宿的地方,为中国人留下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义担当精神。这才是济南人应有的样子:有足够的正念,有足够的厚道,曲堤先民不仅郑重修建了子路庙,而且把古城的西门也命名为“达圣门”。这条文化脉络的制高点,便是闻韶台的崛起,在济北平原上俯瞰着整个古城,成为济阳古八景之首。闻韶台始建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确切考证,也许可以上溯到汉唐盛世,至少在少数民族建政的金元时代,已经巍然耸立。历经无数次劫难与重生,直到民国时代,高达四十余米的高台占地三千余平,大成殿和一系列附属祠庙高踞台顶,荫庇着一方文运。济阳人为一次次重修,给出了一个最为简单的理由:这里曾经是先师“过化之地”,也就是文脉落地生根的地方。济阳人为他们的虔诚得到了福报,数百年间,高台脚下的闻韶书院,培养出张尔歧等大儒。
临淄也有“孔子闻韶处”,虽然比起来貌不惊人,但我相信,孔子同样有机会在齐都留下来精心“学之”。但全国只有一个闻韶台,千百年间,是济阳人把这份文化重任但在了肩上,传承着闻韶余音。同样是齐地,孔子具体在何处闻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只有这座高台才是历史最大的见证。毕竟,世上原本没有闻韶台,只是因为信仰的力量,才有了永远的闻韶台。

中篇:舜庭赓歌
我想闻韶的瞬间所以永恒,不仅是下学上达、好古敏求的治学精神,更是因为孔子对中国最高文化精神的阐扬。《论语-宪问》云:“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这一评价明显高于对周武王《武》舞的评价:“尽善矣,未尽美也”,可谓无以复加。朱子解释:“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在中国文艺传统中,美是艺术表达,善是精神实质,包含了今日所谓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表明中华文化的精神是追求美好,止于至善。
个中道理,还是此前吴公子季札观赏韶乐时说的明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蔑以加于此矣!”一切艺术,观止于斯。可见中华文化里,美的实质是善,善的实质是德,德的实质是仁。仁的至处,譬如天地无私,让万物生生不已,是为天人合德。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文化所谓“乐”,不能片面理解为吹拉弹唱,而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内涵,所以支撑起中华文明,在于“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艺术的价值从来不是感官刺激,让人们“以欲忘道”,而是凝聚价值、“以道制欲”。至于韶乐的中心思想,《礼记-乐记》一言以譬之:“韶,继也”。郑玄解释:“韶之言绍也,言舜能继尧之德。”历史因延绵而悠久,文化因传承而博大。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唐尧时代,舜的父亲瞽叟引领艺术革新,“瞽叟乃伴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透露出大舜出身音乐世家,而礼乐源于宗教,以独特的祭祀之礼赓续精神血脉。自古礼乐的关系,郑樵《通志》云:“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孔子所谓“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乐文化共同构成了价值内核、社会规范与艺术形式的铁三角。到了大舜时代,《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以国家最高祭典体现历史继承关系,五帝世系,彰彰可见,先民对自己的时代应比后人更清楚。其中,大舜直接继承了唐尧,以毕生奋斗“奋庸熙帝之载”,完成先帝的未竟事业。这是一曲开拓历史的华章,尽管时常淹没在噪音中。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早在走出蒙昧的时代便与音乐结缘,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骨笛流传至今。《吕氏春秋-古乐》对音乐史的追述,便从三皇时代的朱襄氏开始。经过漫长积累,发展到大舜执政时,对中国文艺哲学作出了经典概括,《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至今咀英嚼华,道理颠扑不破。历经尧舜时代的接续奋斗,总结历史经验,歌颂伟大胜利,这才有了韶乐——虞廷之上,“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时感天动地,百兽率舞。其中的文化传统,《礼记-乐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又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凝聚着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吕氏春秋-适乐》所谓“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礼乐可谓沉浸式的“行为艺术”,让主流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到了汉代,儒家继续阐扬中国文艺的精神:“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进一步提炼了礼乐文化中诗歌、舞蹈、音乐的密切关系,以及艺术与人性、信仰、德业的内在联系。“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始于内心的真诚与感动,从音声节奏到肢体语言,自然而然,道法自然。
大而言之,中国文学无疑以诗歌为最高形式,中国人是诗性的民族,而诗之所以为诗,同样与礼乐精神相通。譬如朱子《诗经集注》云,“颂者,宗庙之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与乐、乐与德、礼与乐密不可分;从汉代乐府到宋词元曲,无不可弦可歌风流百代;从六朝辞赋到唐代律诗,无不出自汉语言天然的音律和谐之美。《文心雕龙》云:“林籁结响,调如琴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璜。”大自然的清音原本响彻万古,只不过惟有人类的性灵可以捕捉。
其中的原理,程子一语道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史记-乐书》在总结礼乐文化时亦重申,“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在礼序乐和中生生不息,可大可久。“故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父天母地的胸中写满了诗意,恰是一部“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哀”,让万物在天地氤氲中繁荣滋长,井然有序。可见,礼乐文化不拘于有限的表现形式,而是在秩序与和谐的营造中,实现美的感受与善的归宿,让世间成为生命的乐土。
诗曰:“逝彼乐土,爰得我所”。与基督教文明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天堂就在人间,我们相信道德理性,而非依靠宗教救赎。一曲韶乐所以千古传音,绝不仅仅是因为高超的艺术表达,一定是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奋斗与文明理想,让至德之世超越时空,可感可触。

下篇:逝彼乐土
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是相信人性、扎根人心、致力人为,礼乐文化的伟大,同样来自人类的天性与美好的向往。《荀子》云:“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如果说欢乐是人类最大的财富,那么内心的欢乐必然要形成外部表见,通过礼乐文化的艺术表达,“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文艺创作可以服务于人类进步事业,“夫声乐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乐中和,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发挥文艺的陶冶作用。其中包括了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二者似乎在礼乐文化中达成了调和。
相反,一个社会倘若“姚冶之容,郑卫之音”大行其道,“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娱乐无下限,势必在醉生梦死间酝酿时代的危机。耐人寻味的是,《史记-乐书》收录了晋平公令师旷弹琴的故事,仅仅因为“君德义薄”,一时在音乐的沉湎中,导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道破了历史真相:“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鲁迅先生说,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一旦精神鸦片泛滥,必将贻害无穷。“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向方矣。”人们追求欢乐,但至关重要的是追求什么样的欢乐,怎样追求真正的欢乐。
说到底,“礼者,理也;乐者,节也”。礼乐文化的本质,包含了现代哲学所谓人的道德理性,以及在秩序中保障人的自由。礼乐的仪节范式与艺术形式均是末,“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蕴含的道德情操才是本。其终极社会理想,则是成就王道乐土——安顿人类的身心,实现人民的幸福。《孔子家语-论礼》云:“夫民之父母,必达于礼义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有动于中,发为歌诗。誓将社会治理纳入礼的规范,将人类情感融入乐的表达。继承刚健有为、坦荡无私的民族精神,足以让“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夙兴夜寐、严以律己、视民如伤,才是听不见的乐,才是看不见的礼,才是无须说的爱。总之以毕生修为,让天下之人安居乐业,才是礼乐文化彼岸的追求。
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男女老少各得其所,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平等富裕,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分明是一曲响彻天地而又侧耳不闻的乐章。孙中山先生说,“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力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中国传统政治所谓“为民父母”,不过如此。等到“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谋求社会种种之幸福。历经凤凰涅槃,告别古典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核心理念仍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来自永恒的民族理想,与固有的礼乐精神血脉贯通。百王之道,一脉相承;协和万邦,方为韶音。
然而一切生命,总是在盛衰中轮回,在轮回中永生,闻韶台也不例外。只是走过悠远的时空,经历了更多沧桑,阅尽了更多兴亡。民国末年,又是一场天崩地裂的轮回,在洪水的冲击中,慌乱的人们拆除闻韶台上的古碑,用于堵截洪水。此后文革的空前浩劫,更是让整个闻韶台涤荡无余。然而天下只有一个闻韶台,承载着中国人抹不去的记忆,是济南人丢不得的荣耀。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走出历史的断层,闻韶台终将重生。
因为,我们向往着乐土,终将在历史中走向未来。

黄帝纪元四七二零年夏历三月于海右鹊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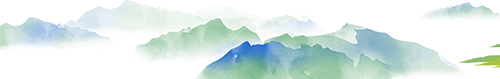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