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没有想到我会得奖,这是意外之喜。我在高校教书,写得最多的是学术论文,可是我的论文都“有心栽花花不发”。令人安慰的却是,我有感而发或偶尔为之的文学性的文字就“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我非常感谢红色日记征文活动主办者——广东省文化学会颁发奖项给我。这对我是莫大的肯定与鼓励。
古人有以文会友的说法。它道出文学在我们生活里的重要功能,就是起相互沟通的桥梁作用。原来陌生、散落各处的人们通过阅读,彼此会心,于是便熟悉起来,有了沟通,相互切磋,成为朋友,有了精神的收获。要以文会友,就首先要有文;没有文,也无从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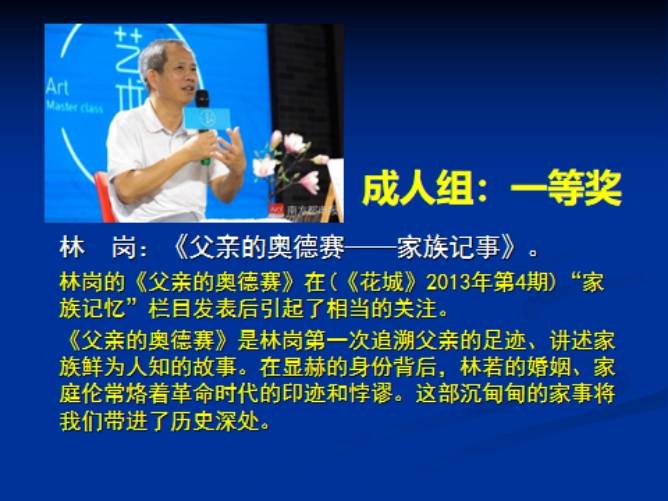 我觉得,征文活动其实是把文会起来非常好的活动方式。尤其像红色日记的征文,雅俗皆通,有广泛的群众性;上到退休长者,下到小学在读,都可以参与。广泛的参与性应了一句俗话: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文还不够,还要文而能会。征文评奖就是会的方式。
我觉得,征文活动其实是把文会起来非常好的活动方式。尤其像红色日记的征文,雅俗皆通,有广泛的群众性;上到退休长者,下到小学在读,都可以参与。广泛的参与性应了一句俗话: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文还不够,还要文而能会。征文评奖就是会的方式。
评出等次固然是题中应有,但这个题中应有的根本精神却不在等次,而在鼓励与肯定。有了肯定,有了鼓励,自然能推动写作的繁荣,有利于保持初心,有助于红色精神深入人心。
红色日记征文草创至今已经四届,参与日众,影响日广,成为众多征文活动的佼佼者。最后我衷心祝愿红色日记征文活动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更上层楼。
林 岗
2023年2月18日

林岗在第四届体育彩票·红色日记征文大赛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


这是文坛身份最为特殊的一对父子:父亲林若曾是广东省委书记,儿子林岗是中山大学教授。《父亲的奥德赛》是林岗第一次追溯父亲的足迹、讲述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显赫的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伦常烙着革命时代的印迹和悖谬。
林岗:我对父亲所知甚少
我自从略识人间事,记忆里就是一个缺乏独自身份标识的人。出现在社交场合,换了他人可能有种种头衔,如经理、董事长、博士、教授、处长之类,但我不可能。从小到大,叔叔、阿姨或朋友、熟人把我介绍给新认识朋友的时候,一张嘴都是说:“这是林若的儿子。”我则含笑点头,表示默认。
这经历使我想起了卡夫卡,与他同病相怜。在他心目中,他的父亲又高又大,衬得他卑微、渺小,必须仰视。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摆脱父亲“成功人士”的遮蔽,卖力证明自己,洗刷人生失败的耻辱,但无论他有多努力,都无法为世俗所接受。
我从卡夫卡的命运中得到了安慰,父亲的光芒笼罩了我,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无论我的心里怎样“抵赖”,都不可能改变世人对于我的外部标识的认知。就拿约稿来说,《花城》看中的并不是我,而是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切,我的作用在于,我知道他身边的一些事儿,说出来也许有益,如此而已。我早早就认命了。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东莞县委书记;我念大学的时候,父亲就是湛江地委书记;而我还在为自己晋升为助理研究员而得意的时候,父亲已是广东省委书记了。在重视事功和人情人脉的中国社会,难怪别人用父亲的所有格来介绍我。
不过我又为我有这样一位受世人敬重的父亲而自豪。在我的记忆中,各种场合、数不清的次数,刚相识的前辈和同辈,他们知道我是他儿子的时候,就当面称赞起先父,称赞他的品行、作风,称赞他为广东这片土地做过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真诚的赞美,它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孤立的举动,几乎是只能用有口皆碑来形容。
最感动我的一幕出现在父亲刚离世的哀悼期间,海康县北和镇潭葛村的村支书带了七八位乡亲赶到远在广州的母亲家,吊唁父亲。一众乡亲蹲在院子里,那位我素未谋面的村支书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说了好几遍:“我们有今天的生活,全靠林书记。”其实,他已经是先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当时海康县县长陈光保在潭葛村试点“包产到户”的第三代村支书了。我心里清楚,这完全不是先父的英明,如果没有清除“四人帮”、“文革”结束、思想逐渐解放的大背景,父亲就是吃了豹子胆,他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一段几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依然令相隔一代的乡亲如此动情,他们的淳朴也令我为之动容,我的心里不禁浮现像谜一样的疑问: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过去我从未想过类似的问题,随着先父的远去,我自己想弄明白与他相连在一起的往事的念头,不时浮现出来。我过去忙于自己的专业,从来没有动过念头要了解父亲走过的足迹。即使在他耄耋之年,随时都能见到他,但他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位慈父。我对他依然所知甚少。
(全文刊于《花城》2013年第4期,原题为《父亲的奥德赛》,林岗著)

来源丨《时代中国》杂志
总编辑丨何金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