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七十年》连载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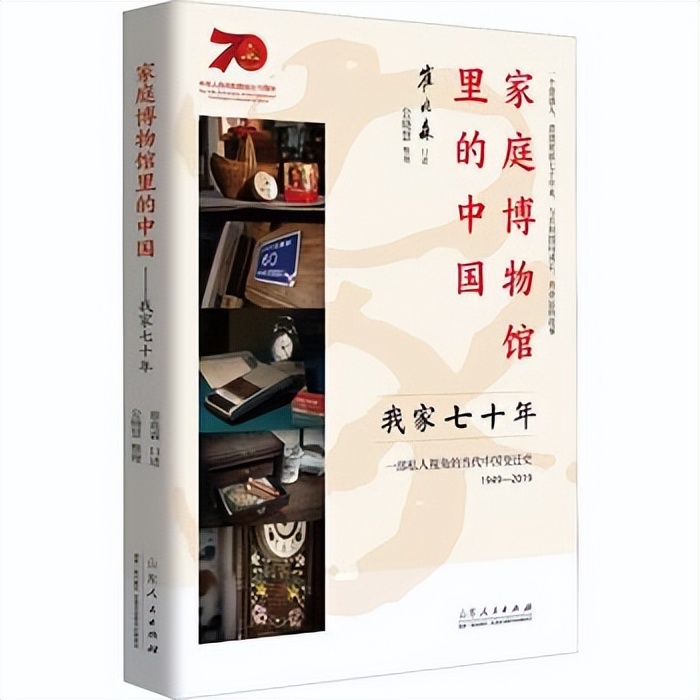
崔兆森 口述 公晓慧 整理
从干粮筐子到饼干桶
编者的话
五六十年前,老百姓家家户户的房梁上都悬挂着那么一个干粮筐子。盛着窝头、卷子的干粮筐子,房梁上那么一挂,既防老鼠又防孩子。物质匮乏的年代,干粮筐子里的存储,对总也吃不饱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无可抵御的巨大诱惑。改革开放以后,干粮筐子淡出视线,铁皮饼干桶风靡一时。1979 年, 崔兆森为女儿买了一桶饼干。当看到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直奔饼干桶里找饼干吃的情景,让崔兆森一下子想起了他年幼时踩着凳子、支翘着脚从干粮筐子里摸窝头啃、掏卷子吃的情景。
六十多年前,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自己蒸干粮,没有像现在买主食的,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干粮筐子。家里的主妇们,都是用大锅蒸干粮,用两层笼扇蒸够一家人几天的口粮,有时候是圆圆的窝头、有时候是方方的卷子。她们蒸好主食后,就把它们放在干粮筐子里,在上面再罩上一个笼布,挂在屋梁上、虚棚a 下垂下来的钩子上。
那个时候,济南大部分老百姓的房子没有虚棚,一抬头就能看见屋梁。那时候不少人家的屋梁上都有燕子窝。春天,燕子就在屋里梁下孵小燕,燕子飞来飞去,好不温馨!老百姓把屋梁上拴上一根绳,绳子末端坠上个钩子,就可以挂东西了,干粮筐子就挂在这样的钩子上。之所以挂得这么高,是为了防止老鼠,更是为了防止孩子“ 搬腾”( 济南方言,意指随意拿。编者注)干粮。那个时候,一个成人一个月也就二十七斤至三十斤粮食,一个月算下来,平均每天一斤粮食,窝头、卷子都得省着吃,算计着吃,算计不到就得有几天挨饿。在我们家里,母亲把干粮筐子看得很紧,不许我们轻易“ 染指”。

饼干筒和大白兔糖盒(郑涛 摄影)
吃不饱的年代,却压不住孩子们的疯长。十来岁的年纪,饭量渐增,看见馒头、卷子就两眼放光。为了防止孩子们随手就够到干粮, 母亲精准地把控着干粮筐子的高度,让孩子们光踮个脚是够不着的, 必须下面踩个凳子才能够着。被强大的馋虫、饿意驱使着,我们即便搬不动又沉又重的方杌子,也能拖拖拉拉地把凳子拖到干粮筐子下方。

2018 年8 月22 日,给孩子们讲“ 过去”(郑涛 摄影)
时光飞逝,我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改革开放之后, 万物复苏,人们的衣食住行条件不断改善。1979 年,我为女儿买了一桶饼干,饼干桶是铁质的,上面印着非常流行的“ 美人图”。吃完饼干后,我们又把一些小点心、小零食放进了饼干桶里。女儿幼儿园放学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从她的铁皮饼干桶里,掏些小零嘴吃。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想起几十年前,我们兄弟姊妹踩着凳子从干粮筐子里够干粮吃的场景。这是何其相似又和其不同。
这一搬一拖之间,肯定是要闹出动静来的,母亲总能马上寻声而来, 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然后大声呵斥,试图将我们轰走。在我们进一步的央求甚或是乞求下,母亲也禁不住心软下来,就掰下一块给我们。我们兄弟再找地方另分。哥哥尽管饿得厉害,也总是分给自己不多, 多分一些给我和妹妹。如此精准、严苛地控制干粮支出数量的这种情景,放在今天物质富足的年代里,真是想象不到。
干粮筐虽悬得高,却高不过我们日渐窜高的个头。随着年景好转、物质渐丰,大人对干粮筐子的监控也渐趋放松,对我们频繁上演的小伎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我们从干粮筐子里获得了更丰盛的吃食。每逢过年过节,我们还可以和邻家的伙伴比着谁的馒头好吃。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 崔兆森口述 公晓慧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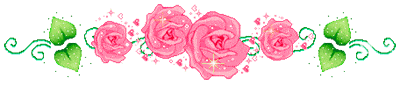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