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七十年》连载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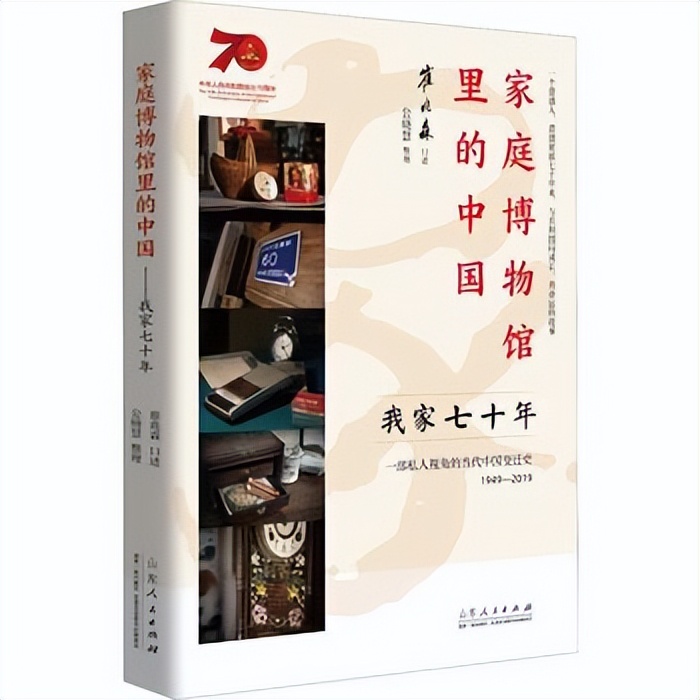
崔兆森 口述 公晓慧 整理
染衣,为生活上色
编者的话
说起“ 染衣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件陌生的事。但对于崔兆森这一代人来说,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在一件衣服“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里,衣服之所以能地反复穿着,有“ 缝缝补补”的功劳,将其重新染色也是延长衣服使用率的重要因素。
那个时候,买布要凭票购买,穿新衣无异于一种奢望。那个时候, 衣服几乎都是纯棉的,洗的次数多了会变浅、变旧,扔掉吧舍不得, 再穿又显得不精神。面对这种情况,劳动人民有劳动人民的智慧,自己动手把旧衣服染上了新颜色,也就有了“ 新”衣服穿。
每年春天,母亲会把全家人的棉衣拆洗好,该补的地方用布头补好,就差遣我到街口的七大马路大众洗染店去买“ 颜色”。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济南到处都有洗染店,洗染店里分洗部和染部,以染为主,以洗为辅。洗衣也是洗名贵换季衣服,能在家洗的没有人会拿去洗染店去洗。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直接把要染的布送到店里,让店家帮着染色。更多的人家,是把颜料买回家,回来自己动手,“ 染旧变新”。
在去洗染店的路上,年幼的我经常一边走一边反复嘟囔着母亲让买的“ 颜色”,但还是有一次把“ 一九蓝”( 长大后才知道,所谓 “ 一九蓝”就是德孚洋行生产的“ 阴丹士林蓝”的标号190 的俗称)说成了“ 九一蓝”。除了“ 一九蓝”,我记着母亲让买过藏青色、古铜色、赭石色、瓦灰色。一小包“ 颜色”一毛来钱,能染一大锅衣服。
等吃完饭,母亲把做饭用的大铁锅刷净,把锅里添上大半锅水, 就开始点火烧水。我在一旁使劲儿拉风箱,一边瞅着母亲如何操作。母亲不一会儿就把手指伸进锅里试试,等她感觉水热了但刚好不烫手的时候,就把“ 颜色”一下子倒进锅里,随倒随搅和。等水快烧开时, 母亲又把要染的衣服放到锅里。正式开始染颜色了,母亲用提前准备好的两根细长的“ 竹劈子”均匀而有节奏地搅动衣服,也会挑起衣服不停地上下翻动,让衣服的角角落落充分“ 吃”透染料,避免出现“ 深一块浅一块”的情况。这个时候,母亲就不让我用力拉风箱了,衣服要上色好就得用小火慢慢煮。煮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感觉衣服染好了, 就把它们捞起来,放在洗衣服的大盆里漂去浮色。每次染颜色过后, 母亲的手总是“ 难逃一劫”,颜料在手上好多天都洗不掉。

染料商标(聂传声 摄影)

解放初期的洋布布标广告

济南北大槐树染料广告(聂传声 摄影)
那时候,母亲用来染衣染裤的“ 颜色”大部分都是藏蓝色。那是那个时候的全国统一色,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儿都通用的颜色,走到哪里既不生疏也不突兀。那个时候,人们染的都是棉衣或者外衣,衬衫和内衣一般不染,因为万一大汗淋漓,染料就会染到皮肤上,使身上画满“ 花地图”,洗都不好洗下来。

万年青染料外包装

济南仁丰纺织染料公司产品外包装(聂传生 摄影)
染好的衣服晾干后,母亲就用它们来缝制棉衣。在此之前,她会找弹棉花匠重新将老棉花套子弹一弹,再续上一些新的棉花。缝完棉衣之后,把它们整整齐齐叠好,用包袱皮包好放好,等着冬天再穿。
这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没有人再染布染衣了。染衣的事, 成为时代留给我们这代人的一种念想。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年轻人们竟然喜欢上了穿掉色的牛仔服。这让我们这些老朽们看得心生蹊跷, 早年衣服掉色是穷和寒酸的表现,今天许多牛仔服却要故意地砂洗作旧,越掉色发白越有价值。想起那句话:“ 不是我不明白,是外面的世界变得太快”。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 崔兆森口述 公晓慧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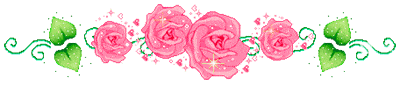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