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地名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济南市市中篇10
土屋记//陈玉珍
编者按: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符号、一种标志,更汇集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还蕴含着一种乡恋、乡爱、乡愁,连接着乡土人情、家国情怀,孕育了一种地域独特的民风民德。
2022年8月25号,国家民政部发布了“深化乡村地名服务 点亮美好家园”全国试点名单,在省、市民政部门的领导和大力指导支持下,济南市市中区成功入选。
市中区的地名试点工作,得到了市中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市中区第一时间成立由区长任组长的乡村地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调度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将试点工作各项任务分工负责,落到实处。
区民政局作为牵头部门,坚持聚焦特色,打造亮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研制乡村地名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组织部分专家作家深入试点村发掘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完善村碑、路牌等地名标志设置,编制乡村片区地名规划和地名采词库,搭建数字村落博物馆、线上电子地图,并拓宽旅游、农产品等多渠道路径,着力提升乡村地名信息服务水平,积极探索乡村地名管理服务市中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他们还邀请了省内部分专家,通过查阅资料、访古探幽,实地采风调研,走访乡贤名宿,撰写出十几篇美文。今天起系列刊发部分专家撰写的与市中区相关的文章,以更好地进行地名文化研究,助力助推乡村振兴。

土屋记
陈玉珍
土屋的黄昏是喧闹的。
被暮色追逐着的山峦,柔和地呈现在遥远的天空。森林将它暗绿的身影,自远处的山谷一路投送下来,在小河边上蓦然停下了脚步。河滩上有白鹭呀,它们只需轻轻一啄,水面上那些树的影子,草的影子,就全都欢笑着跑开了。几个孩子在水边上嬉戏,扑哧扑哧地打着水花。不远处,有晚归的农人扛着镢头从桥上走过。桥头上还有两家售卖瓜果的摊位,都是自家园子里的作物,见有人经过,吆喝得就更起劲了。暮霭在玉符河上渐渐升腾,看上去越发辽阔起来……
玉符河,《水经注》里也叫它“玉水”。是济南南部一条顶顶重要的河流,先后做过济水和大清河的支流,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又成为黄河的支流 。
玉符河边上的这个小村庄就是土屋村,是玉符河两岸众多沿河而建的小村落之一。
自百度输入“土屋”两个字,能出来一长串的搜索结果。
单是在济南一带,名叫“土屋”的地方就有两三家:长清区张夏镇有个土屋村,市中区党家镇有个土屋村,历城区仲宫镇也有个土屋村。
可见,土屋这两个字,应该是个极好的名字。并不因“土”而遭到人们的嫌弃,反而颇受大家的欢迎。
号称阳春白雪的诗歌里,也有它婀娜的身姿呀!
你瞧,元代袁桷的《云州》诗:“毡房联涧曲,土屋覆山椒。”
宋代梅尧臣对土屋也青睐有加,他在《季父知并州》一诗中写道:“土屋春风峭,毡裘牧骑狂。”
诗歌里的土屋好像分外妖娆。
百度词条中给出的解释,则极简到了极点:土屋,用土筑成的房子。
是啊,最初的土屋,不过是在土崖上掏出“洞”来,再稍加修缮,变成了房子而已。且往往依山而建,与山连成一体,说起来,应该算是最具原生态的一种“建筑”了吧?
比起故宫、圆明园那些雕梁画栋的经典建筑,土屋实在算不上什么。但是,当一切跟先民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维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土屋的出现,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它,让我们的先祖从幕天席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粗鄙境地中解脱出来,有了能遮风挡雨的容身之地。家的概念,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出现并建立起来的。
由此可见,土屋,实在是一种很古老的建筑。
1 、土屋.老井.辘轳头
明代中期,玉水河畔的卧虎山下,迁来了两户人家。一户姓陈,一户姓边。两家人在山下盘桓良久,各自选定了自己心仪的地方定居下来:陈姓人家选择在山北的谷地依山而居,边姓人家则选择了山的东面,依河落户。
两块地说不上谁殊胜一筹,偌大的区域有山有水,不愁吃住,对于庄户人家来说,已是风水宝地,足够休养生息了。简单的休整之后,两户人家不约而同地看中了山脚下的一溜土堰---那土堰又高又厚,看上去有7、8米高,有的地方高度甚至达到了十来米,成年的男人可着劲夯一镢头下去,土层就哗啦啦地往下掉。经验告诉他们:这里,将会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最新居所。于是,静寂的山谷里第一次响起了工具和人的声响。随着镐头和镢头的交替推进,土屋的雏形,就这样,一点点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是多少年颠沛流离的求生之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善用自然,也教会了他们点石成金的谋生手段。生活中的一切困厄,在勤劳与智慧面前,似乎都算不上什么。身边的一草一木,哪怕是一块小石头,都能有它奇妙的用处。
土屋的诞生,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正式开启。解决了后顾之忧的人们,很快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起来,一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村居图缓缓铺展开来……
再后来,先人们为了区别这两个村落,依照姓氏将他们分别命名为“边家土屋”和“陈家土屋”。两个土屋距离虽近,但如今却分属于市中区和历城区。村内仍然保存着几栋老式土坯房,券门格窗,花脊小瓦,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见证……
倘若你去打听,街边上的老百姓还是会沿用祖上传下来的惯例,用边、陈两家来区分提醒你:“恁问的是哪个土屋村嘛?边家的在这边,陈家的在那边,别走叉喽……。
今年79岁高龄的韩文才就是生土长的边家土屋村人。说起土屋村的变迁,他就会摇着一把大蒲扇,慢条斯理地说:“边氏是土屋村最早的人家不假,只不过后来嘛,边家衰落了,反倒是迁过来的杂姓越来越多。俺们土屋村才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俺们韩家祖上就是逃荒逃过来的!”说着,他把搭在肩膀上的白衬衣取下来,又慢条斯理地穿在身上,遮住了原先的汗衫,“来的都是客儿。俺老汉可不能怠慢喽!”
我们在一旁听得乐呵,忙说:“韩大爷,您随意,您随意就好!”
村委会的小刘给他递上一杯热水,说:“韩大爷,您可是俺们村的能人咧!早年在人民公社干过炊事员,是俺们这远近闻名的大厨呐!听俺婆婆讲,韩大爷年轻那会儿,可受大姑娘小媳妇待见来!您说是不是呀?”说着还调皮地吐了下舌头。于是,爱笑的韩大爷摇着蒲扇又笑了起来,脸上的褶子就更深了些。
话匣子就这样在谈笑声中被打开了,土屋村那些被尘封的历史也渐渐清晰起来……

话说早年间,土屋村靠着玉符河,虽说用水是方便了些,可玉符河毕竟是条季节河,一到枯水季节,老百姓吃水就犯了难。不得已,人们只好拿着瓢呀、罐子之类的家伙什,排着长队到河沟里面去刮水。就这样,刮上来的还常常是半桶黄沙,连做出来的饭都带着股子泥巴味。后来,不知是谁有眼力见儿,发现这里地下水丰富,人们就在河沟两岸挖了不少的井,按上支架,辘轳和井绳,有了它们,再羸弱的妇人都能轻松地提上水来,别提多方便了。
“我家屋头上也有一口。”韩大爷说,“你沿着河沿儿走走,能碰上好多口这样的井。”只不过,现在这些老井大多用不上了。村里打了机井,安装了管道,家家户户都喝上了自来水,人们就用铁板把井口盖了起来,“娃娃们就像庄稼,一茬一茬地长,得防着那些调皮捣蛋的往下掉!”说着,这个可爱的老人又笑了起来,紫棠色的脸庞上隐隐泛起幸福的光泽。
“那这些井里还有水吗?”我好奇地问。
“有哇!”老人信誓旦旦地说,“不信,跟我去看看。”说着,老人起身往外走去。
我们也跟着往外走。果然,离村委大院不远,我们就看到了一口这样的老井。井口用雕花的围栏围了起来,石砌的围栏四四方方的,取四平八稳之意,上面还刻有莲花浮雕的纹饰,清丽婉约,令人一见就心生欢喜。辘轳头是铁制的,看上去锈迹斑斑,上面挂着三块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石板。我走过去,试着用手去推动把手,辘轳头就吱吱扭扭地转了起来。
“这水甘甜着咧,常年不断!”旁边的韩大爷看着我们忙活,笑得没了眼,手里的蒲扇一摇一摇的,像极了画里的老神仙。
我们也跟着大爷去拜访了村南边仅剩的几家老土屋。历史走了这么久远的路,太多的痕迹,早已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湮灭了,消散了,但岁月慈悲,到底还是留了些许痕迹。山脚下的老屋几乎都已斑驳。轻抚一下门板,上面厚厚的尘土就簌簌地往下掉。其中有一户,主人家还在屋子顶部加了一层厚厚的石头。风从北边吹过来,又从门洞的一角溜走了。屋脊上,野草青青,在这个夏日的午后,很深沉地沉默着,我彷佛看见历史的车轮,从上面呼啸而过。
2、 老庙.古柏.七圣堂
村里的小巷都静悄悄的。人家的门也静悄悄的。有的很豪气地敞开着,似乎谁都能不客气地走进去;还有的羞答答的,只拉开了一道小小的门缝,让人忍不住想瞧瞧里面的风景。
我们开着车在小巷里转悠。小巷很窄,窄得只能容一辆车单向行驶。有扛着锄头或者推着小推车的农人从对面走过,就不得不停下来,侧着身子,贴到墙根儿里去。等车子走远了,锄头和小车又晃晃悠悠地向远处去了,悠闲地像是人家院子里的一株老梧桐,总是从犄角旮旯里探出头来。
我们去的这个时候,正值晌午,庄户人家歇晌的当儿。荒村沉寂着,一声不吭。偶尔有一两只大鸟呱呱叫着从屋顶上飞过,令人分不清是喜鹊还是老鸹。
我们的目光被这几只大鸟牵引着,直到遇见一棵老柏树,在街边上矗立着。枝叶异常葳蕤,占据了全村唯一的小广场,一半的天空。柏树已经很老了,大抵是村子里最古老的一棵了。和村子一样古老。几个年老的妇人,清一色穿着露肩的花布汗衫,也摇着一把蒲扇,坐在槐树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偶尔用扇子的边沿从小腿上划一划,挠一挠蚊子留下的痒痒包。见我们一群外乡人走过来,惊讶地忘记了摇手里的蒲扇。

柏树后面,藏着一间小屋,木门虚掩。韩大爷说,这里便是七圣堂,是村民们祭祀供奉的地方。推开门走进去,便看见屋子中央有一张简易的案桌,上面零星摆放着供奉用的香炉。正墙上,挂着一溜木制的牌位,像是旧时客店里挂着的水牌,上面用黑漆的字体写着郎神、土地爷、关老爷等七位圣人的名字。
韩大爷说,这里原先也曾经有一座老庙的,庙里正位上还供奉着观音菩萨。老庙东面,也曾经有过一栋老式的钟楼,钟楼内有一口大钟,还是乾隆年间铸造的呢。算是村里一样老物件了。每逢每月的初一、十五,就会有敲钟人铛铛地敲起钟来。那声音,据说能传出去很远很远。“河水有多远呀,嗯,那钟声就有多远。”村里人总是这样说。
可惜后来,七圣堂不知所踪,就连旁边的钟楼和大钟也不见了踪影,只余下门口这棵老柏树,还在不知疲倦地清点着从旷野吹来的晚风,一如当年的模样。
但总有一样东西,是能留得住的吧?我们的心隐隐期盼着。
就真的还有一座“活着”的老庙。顺着蜿蜒的河道往回走,穿过七拐八拐的小巷,便能看见一座石桥。桥头上,立着一座庙。当地人称它 “地母庙”。是村里人敬奉道家“四御尊神”之一的“后土娘娘”的神庙。也是济南地区已发现的唯一一座地母庙。

地母庙始建于民国时期。形制呈正方形。倘若从空中看下去,像极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青石垒砌的门楼上,上书“地母庙”三个大字,内侧另书“修真道院”四个大字,庄重古拙。进得院内,便见到一方照壁,同样也是四四方方的,前面还竖着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刻有繁复的花纹。有些像是祥云的纹样,但也有可能不是。咨询村里陪同前来的工作人员,都不甚了了。
院子正前方,便是三间主殿,俱是硬山顶的样式。雕梁画栋的,屋脊上装饰着二龙戏珠。左右有配殿,左边的一间,还供奉有泰山碧霞元君的神像。依稀还能看出当年香火鼎盛时期的样貌。
庭院深深深几许。看得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了。里面的花草长得极为茂盛。青砖铺就的甬道埋没在草丛中,几乎看不见踪影。柏树和梧桐各得其所,各自占据了院子一角的天空。牛筋草、稗子草、拉拉秧……一些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野草都能在这找到自己的影子。殿门口一侧的石榴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与殿门前红漆的柱子相映成趣。
村委会的小刘介绍说,之前还有一位姓王的老居士经常来这里打理,后来因年事渐高,也就不再来了。院子西北角上,还有一口巨大的灶台,黑黢黢的,如今也荒废下来。灶前野草萋萋,有些甚至比人还要高出许多去了。
流光总是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里的人来了又去,唯一不变的是植物的信仰,它们抱紧了脚下的土地,努力地长叶,努力地开花。用自己的方式向着天空顶礼膜拜,阳光在哪里,他们的方向就在哪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将它们的信仰改变……
3、 老泉.花椒林.芦笋园
村南,有一口老泉,名叫吴家泉。是玉符河的支流。
村里的老人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和这里的居民有关。边姓人家在建立村落后,天长日久,逐渐式微。清末民初,一户姓吴的人家取得了村南河谷周围的土地居住权,遂将这口泉眼以自己的姓氏为名,换作吴家泉。
泉水顺着山势汩汩而下,将土屋村分作东西两部分。人们在河上架起石桥,往来行走。河岸一侧建起雕花的围栏,看起来十分华丽;另一边却做成了垛形,远远望去,像是微缩版的长城在河道上蜿蜒。坐在垛子上或者河边的顺水亭里吹吹风,听听耳畔传来泉水叮咚的声响,都是极好的事情。
一路沿着河道溯河南行,穿过一大片庄稼地,河的源头便是吴家泉。主泉源镶嵌在山谷西侧的崖壁上,被修葺成方池状,池内清平如镜,耳畔却有潺潺流水声。寻声去,原来底下有暗渠通河堰,泉水自堰下而出,汇集成一片波光粼粼的湖面。
我们所处的位置,恰好在湖的出口处,抬眼望去,只见一道大坝将湖水拦腰截住,坝上长满了青苔,湛绿的湖水顺着青苔滚滚而下,溅起朵朵水花。 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坝上玩耍。一会的功夫,就听见扑通一声,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水里的孩子已经从水面上冒出头来,一把抹去脸上的水珠,咧开嘴巴嘿嘿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回去的路上,我们还遇见了好几波前去湖里游泳的人们,有大人,也有小孩。其中有一对父子,骑着摩托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父子俩一样的寸头,光着膀子,露出精干的上身,晒得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正是山里人特有的光泽。

路边是大片的花椒林。有些已经成熟了,青红色的小果子一簇一簇的,在枝头上含笑而立。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山上摘花椒的情景。树梢上的小刺可真多,一不小心就会扎到手,钻心地疼。可现在想起来,却只觉得无限美好。岁月的衣衫多么不经拽呀,一晃眼的功夫,几十年的时光就这样悠忽而过。童年时摘过的那片花椒林,却再也没能回去过。
“你摘过花椒吗?”我紧走几步,问前面的小刘。她是从临近的宅科村嫁过来的,儿女都已经很大了。
“没有呢,俺们家不种这个,屋头上有几棵,足够吃了,都是俺们家婆婆去摘。不让我插手。”小刘回头朝我笑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咱村里现在有啥好的特产没?”我好奇地问。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小村庄,2019年就已经被评为齐鲁样板示范村,怎么能少的了特色农业的支撑呢?
“有的呀!”小刘欢快地说,“从这里往下走,有一大片芦笋种植区,是俺们村出了名的新型农产品!出产的芦笋可好吃啦!有绿的、白的,还有紫的笋,好多品种呢!俺们佘书记说,村里未来的头牌农产品,可就靠它了!”
说着,小刘带着我们往公路下方走去。走得不远,果然见到一个大型园区,用绿色围栏围了起来。围栏上爬满了拉拉秧,叶子边缘和茎条上都布满了细小的刺儿,你一蹭到它,它就会在你皮肤上留下一小片红红的印子,火辣辣地疼。
我们猫着腰,从拉拉秧的缝隙里往里面看去,只见密密麻麻一大片类似青稞的植物,竟是看不清它的样子。我们有些不甘心,四处转悠,找寻能进去的入径。小刘指引着我们,找到了一小棵芦笋,正从拉拉秧的绿云堆里酣睡着,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我趴过去仔细瞅,发现它的叶子有些像是茴香苗,叶子细细长长的。摸一摸,触感软软的。

“俺们村紧靠着玉符河,村里还有特色大棚农庄,一个幼教研学基地,俺们佘书纪说了,一定会带领俺们村人一块致富!”小刘骄傲地说。此时,夕阳的余晖已经渐渐洒落下来,照在这个小媳妇年轻的脸庞上,打上了一层薄薄的光晕。看上去,越发娇俏了。
湿润的河风,拂过远处的山峦,也一定拂过田野里的每一棵庄稼。我们彷佛看见,土屋村的明天早已在来的路上,迈着步子跨过山岗,喊着幸福的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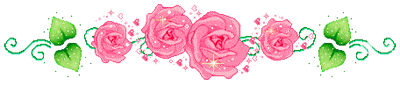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