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由于两个月以来的持续干旱,导致我们河底镇大明村塬区秋作物禾苗枯萎,夏玉米无法播种,就是抢种上的,也是白白浪费了种子和播种费用。大片大片的麦茬地就这么闲置着,土黄一色,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绿意。就是田地里的大秋作物,也是在太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叶卷棵萎,精神不振。看到这些景象,老百姓的眉头紧缩,心情不畅。

前几天的一场雨,让百姓们看到了一丝希望,最少大秋作物能缓解旱情,多少有点收入。而麦茬地,又能种上点啥呢?7月将尽,10月种麦,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只能种一些生长期短的作物。
俗话说:入伏三天种犟豆。可如今已进中伏,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面种白菜,也许还能有点收入。再种玉米和谷子,还不知道有没有收获的希望,老百姓出力不怕,就怕种下去后,既拔去了地力,再熟不下来,耽误下一季种麦时节,一季不收耽误两季,那可是最不划算的。要按以前,不收就不收吧,还可以有“白露不出头,割了就喂牛”的俗言。
可如今,多是机械化耕种收获,喂牛已是一种拖累,少了不赚钱,多了没钱投资,还要捆绑一个壮劳力。拾草喂牛,牵牵拴拴,饮水喂料,垫圈除粪,一个女人在家,这是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再说,如今的大牲畜,吃饱喝足,不劳耕种,耍开了倔犟脾气,那可拾掇不住,还容易发生危险。再一个,喂牛需要场地,没有闲置的地方,农村也讲究干净卫生,夏天牛粪招蚊惹蝇,臭气弥漫,在居民附近,肯定会受到邻人的嫌弃和白眼,嘴上不说,心里也是厌恶的很呐。
今年村里头种植结构调整,让种玉米大豆套种,可玉米种进去一直干旱没出来,豆子也没敢再种。可如今早过了大豆的种植时间,就让种谷子,可有些农民对此并不看好,就不愿意种,而想种一些生长期断的绿豆、小红豆,跑了附近的几个乡镇,也都没有卖的,所以我就想去县城一趟,买一点豆菜种,另外去马老师家坐坐,毕竟马老师也说过几次了。想想也是,自从马老师的母亲下葬那天,我和城头红军哥冒雨骑车去了一趟,由于当时人多事杂,马老师也没时间过来应酬,我们也只有在他家里吃了饭,就随众人到灵堂前,鞠躬告别。之后,马老师在微信上致谢说:“那天下雨,还麻烦你们俩个那么大老远骑车过来,希望有空来县城了,一定到家里来坐坐。”

26号早上起来,阴天有乌云,虽说预报没雨,但也不敢贸然前行。待到10点左右,天气转好,没有了下雨的迹象,这才和马老师通了电话,以免到时马老师不在家。还好,马老师说:“上午回家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就回县城。”听到这话,我才敢放心前往。
在骑往县城的路上,我看到我们这道塬的西王,坡头,直至仁村岭上,麦茬地都没种啥,只有秋地里的玉米、花生、红薯,在一场透雨过后,才发出翠绿色的光泽,生机盎然。到了川底,大路两旁的杨树,高大窜天,在没有阳光的今天,更加阴凉。三乡连昌河桥下,河水依然混浊,只是水势回落,两边水泥堤坝上的泥沙痕迹还在,往日河道里枯枝落叶,都已不见,被河水冲刷的干干净净。古镇上的李贺雕像,手拿诗卷,目视前方,泰然自若,丝毫不会为了一场大暴雨,而惊慌失措,这也许就是雕像和活人之间的区别吧,没有一丝的感情在里面,也不会为了生活上的柴米油盐而奔忙。

古镇上的人们,还一如既往地忙着各自的事情,沿街的商户,忙着摆摊,和顾客之间的讨价还价,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车辆,杂乱有序,奔向各自的远方。到了崛山,正赶上集市,大路两旁店门口的路面被破开,要埋污水管道。卖水果小吃的摊贩,就在这路两旁摆摊叫卖,骑车购买的顾客,就随时停车,停在路上,让本就不宽阔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来往的车辆,也都慢腾腾地如同龟爬,谁也不想有个闪失,再添拥堵。好不容易出了崛山街,才算畅通,可就在庄上村的大路旁,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中年妇女侧躺在大路上,一辆电动车也同样侧翻着,引来众多路人的围观,有一中年男人在维护着交通秩序。这时,我看到对面的路上,有一辆警车开过来了。
危险无处不在,小心行驶,是每一个驾驶员的职责,交通安全,关乎你我的家庭幸福,这可不分你开的大车或者是小车。进入县城,车多人密,各行其道,小心行驶,但我仍能看到有电动车,三轮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而有的机动车则停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上,让本就不宽敞的自行车道,更加难行。

我在烈士陵园仓颉石像处,拐到里面的道路行驶,把车停在了凤翼山公园入口处的停车点,就下车往凤翼山下的河洛书苑走去。到了跟前,才发现门已上锁,只能隔着玻璃门看到内部的情况,整齐的书柜,摆满了各类书籍,如此优雅的读书环境,在农村是没有的。而农村的书屋,也不是经常开放的,在农村想看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凤翼山公园出来,我沿着往邮政局的方向走,边走边看,两旁的种子店,手机店林立,如今信息时代,每个进入社会的人,手机谁都离不了,看书、上网、听课、聊天、耍游戏等等,都在手机上能找到对应的APP,真是方便的很呐。新邮政局大楼,高大气派,远比旧的邮政所高大尚。在邮政局对面街上,看到有家小书店,我就拐了进去,书店里的书摆放整齐,中外名著,学生教辅,课外读物,各种字帖,琳琅满目。当我问店员,可有我们县的作家作品没有,店员笑着摇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
自洛宁书店被拆后,多少个年头过去,依然没能建起来,洛宁古称书城,但洛宁却没有一家大的书店,给洛宁爱好读书的读者们,增加的难题。这让我想起前几年,我去宜阳县书店购书的情景,除了各类图书以外,另外设有本县作者图书,能让本县作者了解本县的历史地理,人物故事,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更能为外地读者对了解宜阳县的文学,提供一个平台。看看没有自己想要的图书,我就走出书店。沿着县政府门口的路,走到公安路,又拐回来到政通路,快到头时,我才想起来吴电智老师就在这附近,就给吴老师打了个电话,才知道他在县委隔壁的办公室,和杨小沪老师在聊天。
我快速走到凤翼山下,骑回电动车,来到吴老师所在的易典通办公室门口。就在这时,接到了马老师已经从他家里回到县城的电话,让我上午去他家里吃饭。经常到洛宁来,总是麻烦他们,我可不想这样。就让他们自己做饭吃吧,我在吴老师这里,就挂了电话。这才把车停好,走进了易典通的办公室。
易典通办公室,我已来过这里几次,因此对这地方很熟悉。进了办公室,我直接走到后面的休息区,看到杨老师和吴老师正对面坐在茶几那里,看我到来,吴老师忙起身让座,杨老师也笑眯眯的望着我,把茶几上的果盘往我跟前推,果盘里放着削成片的桃子,还有一把水果刀,杨老师把水果刀递过来,示意我直接用刀扎住桃片往嘴里送。吴老师说:“先吃几块桃片润润嗓子再说”。
当我吃着桃片的时候,吴老师又说:“你不打电话,我们可能就回去做饭了,杨老师的爱人和我家孩子妈都有病了,得我们回去自己做饭”。我忙问啥情况?杨老师说他的爱人感冒了,而吴老师的爱人则是腰背出疱疹。听了这话,我说:“那咱们都赶紧回吧,家里有病人,还得做饭,让你们在这里久等了”。杨老师问我:“你现在要不要跟我一路回家属院,你去马老师那里”。我说:“马老师从家里回来,刚和我打过电话了,这几天他忙,我就不先打扰他们了,等我吃了饭再去他家里叨扰”。等杨老师骑车走了,我才和吴老师各乘一骑,往他住的地方奔去。
到吴老师楼下,停好车。由于我家离县城较远,又是长距离骑车,每次来县城都需要充电,吴老师和我是同乡,也都明白我来趟县城的不容易,就上楼插了插头,我便在楼下用充电器把电车和电线连好,电就充上了。当弄好这一切,吴老师让我和他一道上楼做饭吃饭,吃了饭再坐下来聊聊。我怎能让吴老师管我的饭,便让吴老师和我一起出去吃,吃好回来的时候,再给他爱人捎一碗饭回来吃,可吴老师不肯去,一再拉扯,我只能说:“我还真有事儿,不能在此长时间停留,来趟县城不容易,时间又紧,我得先办完事情再说,能在你这楼下充电,已经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怎能再在这里吃饭,麻烦你们呢”。
吴老师只好依了我,并让我骑他的电动车,说去哪里方便,我怕骑车出去耽误吴老师出行,就没答应他。就说步行好,正好可以锻炼一下身体,近距离看一看洛宁县城。吴老师上楼做饭,我便步行出了家属院,往种子公司方向走去。在“老闪扯面馆”吃了饭,随后出来买了豆菜种,这才往马老师家里走去。
推开马老师家虚掩的门,他们正在屋里休息,看到我进来,马老师忙起来让他爱人张老师张罗着给我做饭,当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的时候,又吩咐张老师给我切西瓜,我又忙制止。说在我们农村,这西瓜可不缺,还是留着你们自己吃吧。
但我哪里能制止得住,张老师还是把西瓜洗好切开了,只是可惜西瓜已经坏了,只好用塑料袋装起来,提到下面的垃圾桶里丢掉。在卧室外面的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说了这段时间在外的事情,张老师便拿出她和马老师合编的作品集《同共和国一起成长》送给我,又去倒了一杯开水让我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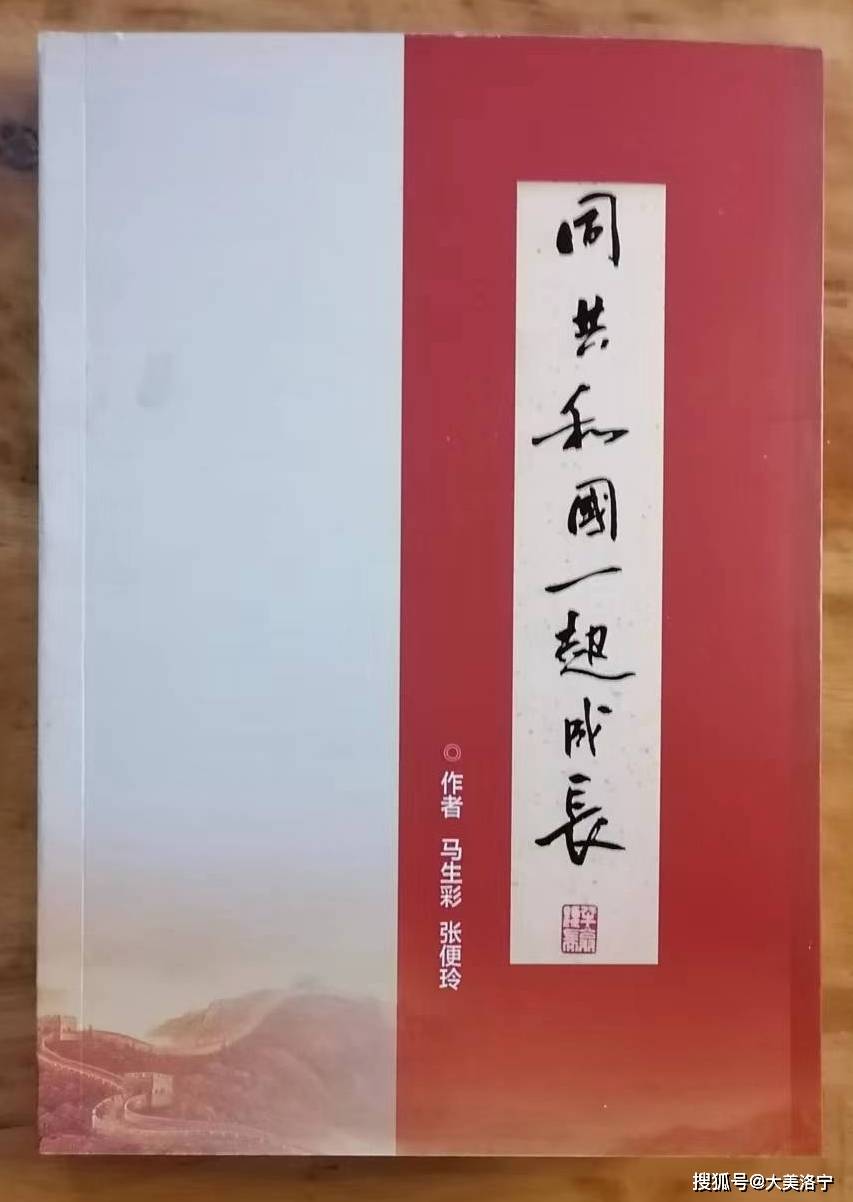
我和马老师就在客厅里说了一会儿话,因为我还有别的事,也为了不打扰他们的休息时间,就起身告辞。马老师也没强加阻拦,知道我来一趟县城的不容易,办事要紧。马老师送我出门,我也没让马老师下楼梯,我知道上下楼梯,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走在大街上,我就给杨青显老师打电话联系,和他说起《竹风》的事情,也许杨老师家里有事儿,他让我去太阳花家里拿,虽说我和太阳花是老乡,称姐道弟,可我却不知道花姐家住在哪里,杨老师就告诉我她家的大概地址,县政府对面,正好我有她的微信。到县政府的时候,我用微信电话和她联系,她让我在防疫站门口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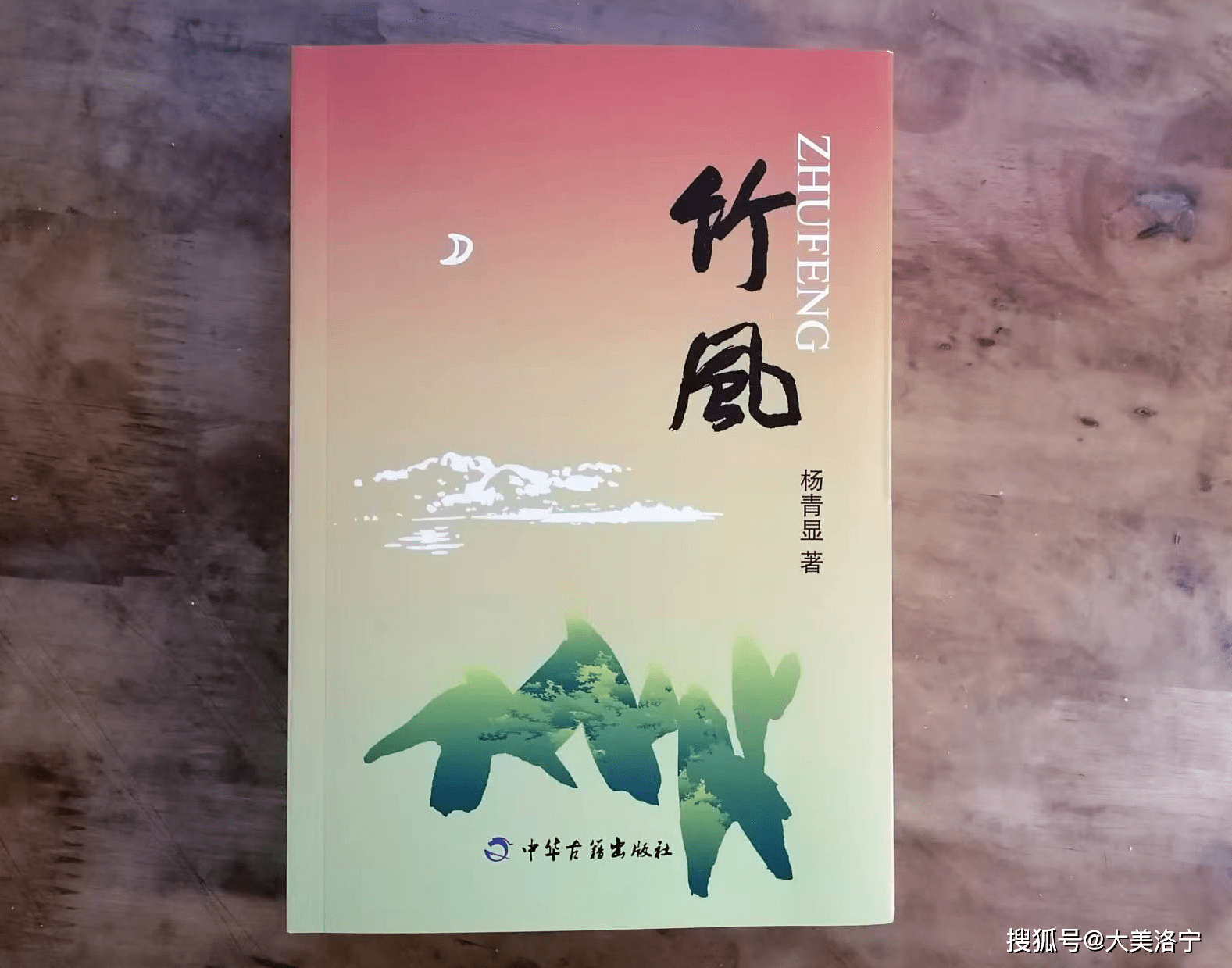
不一会儿,花姐就丢下手边的事情赶来了,既是同乡,就显得格外亲切,并邀我到她家里去。因为花姐家的房子拆迁,只好租住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客厅和卧室里都摆放得满满当当,过光景的家什是一样也少不了的,虽说杂乱,但也摆放整齐,各归其位。
花姐热情地端来水果桃子,茶叶水,并打开家里的风扇,怕我一路走热,让我润嗓子吹风,让我感到了回家的感觉,没有丝毫的陌生和拘谨,和她谈起她和她爱人的工作和身体,讲出来的生活都是磕磕绊绊,人生不易,生活艰难,是各有各自的苦。没有深入谁的生活,都会觉得人家活的风光无限,一旦走入进去,才会知道谁的生活都是大同小异,生活琐事一大堆,离不开的柴米油盐,在人面前的开心,在人背后的辛酸。
农村人总觉得城市人的生活过得舒坦,没有那么多的杂事儿,可不知道城里人的吃喝拉撒都离不开钱,若是没有了工作收入,其生活可想而知,有公司职位的还好,退休了还有退休金拿,生活有个好的着落,要不然吃饭都是问题。而对于城市人看农村人,都会觉得农村人有地种,就有粮食蔬菜吃,手勤快的人,还可以养鸡养猪,有鸡蛋吃,有零花钱。可他们哪里知道,如今的农村,种地也是够维持个温饱,除去投资,不敢算人工。在农村,有稳定收入的打工人,都不愿意回家种地,既出力还不挣钱,好的还一年回来种茬麦,不好的,直接就把地租给别人种,拿个地租多轻松。塬区没有水浇地,若是遇到持续干旱,就是拉水浇地,也解决不了问题,毕竟天雨水发苗,井水太冷,属于生水,周围的环境干燥,只能越浇越旱,越是没有生机。
而天雨水能促进根部生长,叶绿枝旺,开花结果。至于养鸡吃蛋,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散养鸡,鸡每天放出去散养,捉虫吃粮,可嬎了鸡蛋,也并不舍得吃,都攒起来卖了,给孩子们交学费,买作业本用,农民们说过一句话很形象:拿粮食换鸡蛋,鸡屁股就是小银行。可如今都是铺水泥地,鸡粪遍地,不讲卫生,便会迎来邻居们的冷嘲热讽,圈养拿粮食喂,更不划算,就不再养鸡养猪了。
花姐把杨老师的书给我,并提到前几天她们去参加原教育段局长的新书发布会盛况,我也惊喜得很,为洛宁能在这一年内出版发行几本书而高兴,书城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对于段局,我也只是在微信群里知道他,以前听群友们谈论过他的小说《残缺》,说是写得很好!这算是他在我心里有了第一次印象。
那年出去打工,到洛阳后,去周王城广场,在不远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了谭杰老师和他两个人的书,对于谭杰老师,我是认识的,那还是在武装部后面盖楼的时候,在工地上见过他,只是人家并不认识咱。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能在这里买到,怎能错过,这也是缘分啊,随即收入囊中,在外打工之余拜读学习。从这本书,我知道了段局,但一直没有谋面,也算是一种遗憾。再说,咱是一个农民,而人家是一个当过局长的人,身份不同,学历不同,接触过的事物也不同,咱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人家,直接去人家家里索要书籍,他会送给我吗?
就在这时,我在微信群里发的信息:
今日有空进永宁,只为《共和》与《竹风》。
旱塬俩月终降雨,随带买点豆菜种。
先与杨吴简会面,再赴马府叙衷情。
得到了杨小沪老师的回复:
信手拈来,装入诗囊。
嬉笑怒骂,即赋华章。
才思敏捷,质朴安详。
记录生活,边走边唱。
好诗好诗!
我们这一发一回,引起了段局的注意,段局就在群里回复我:
@塬上草 想看书,来拿就是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我放下了顾虑。雷冰老师告诉我,直接加了段局的微信,方便要他的家庭地址,也方便联系。并对我说:“一个读者,若能上门去他家里求书读,是他很高兴的事情,段局可不会在乎一本书价的问题。”
听了雷老师说的话,让我联想到农村人说的一句话:一个厨师,最希望看到的是他做出来的饭,被客人吃得净光,这样才能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厨师的价值。我试着添加,段局立马就通过,并说了家的地址。为了不让段局久等,我遂告别花姐,往吴老师楼下去,好骑车往段局家去。在吴老师的楼下,和吴老师打了电话,得知吴老师陪伴爱人去了医院,我就告诉他我把车骑走了,不让他再操心车的事情,一心看病,就挂了电话。骑上车,往段局家去。
段局家住四楼,我把车停在楼下,怀着忐忑的心,背起挎包,踩着楼梯,走上四楼,厚着脸皮,如同一个索取知识的乞丐,敲响了段局家的房门。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只能拭目以待了。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打开后,我说我约了段局,她就把门打开,并对着一个房间说了一声什么,就看到一个精神矍铄,面戴眼镜的老人,从房间里出来,我一下就认出来这就是我要找的段局,遂慌忙上前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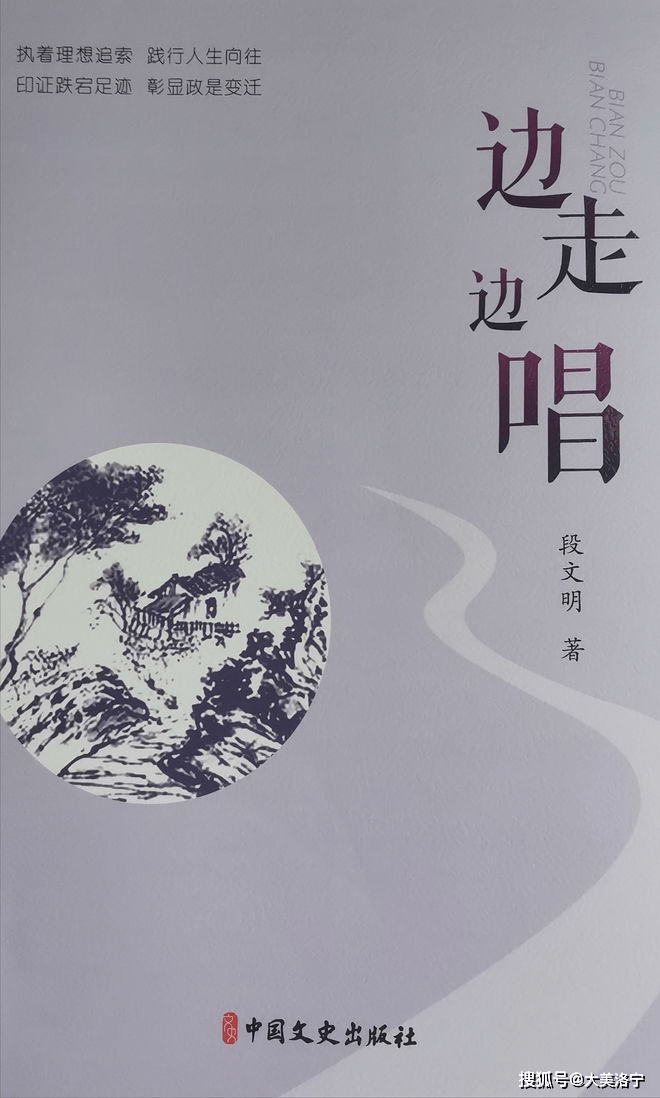
段局请我随他进入房间,我才看到这是他的书房,挨门的墙边放着一个书柜,迎门的墙边放着两个书柜,在另外一侧,则放着一个茶几,两把椅子,在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大桌子,三个书柜放满了厚的、薄的,平装的、精装的各类图书,桌子上放有书籍和笔墨,木雕,墙上挂着几副字画,书香味儿浓厚,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段局不仅仅只是一位退休的干部,也是一位热爱文化,著书立说的作家,更是一位书法家。这时,段局从桌子上拿过来一本签了名字的书籍送给我,还请我多雅正。我接过来,连忙说:“我应该拜读学习才是,怎敢说雅正的话,段局真是太谦虚了!”接下来,段局又拿了一瓶水让我喝,我们这才坐下来。他询问了我在外面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俨然如同一位长者对晚辈的关怀备至。并问了我的业余爱好和读书情况,我都一一作答。
当他得知我热爱家乡文化,利用闲余时间,进村收集碑刻资料,整理出来发布平台;打工之余,关心家乡农事,及时回家帮助家人收获庄稼;利用在外面下班时间,能看书写点东西,很是赞成,并倍加鼓励。想想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入一个领导家里,坐下来能和他畅谈半个小时左右,从工作到家事,再到读书写作,续修家谱,还能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心里的忐忑不安恢复平静。但我也不能过多打扰段局的时间,就随即起身告辞,段局把我送至门外,在楼道里再一次握手道别,他提醒我骑车注意安全,我劝他留步,多保重身体。直到我下到第三层,看不到他时,才听到段局回屋关门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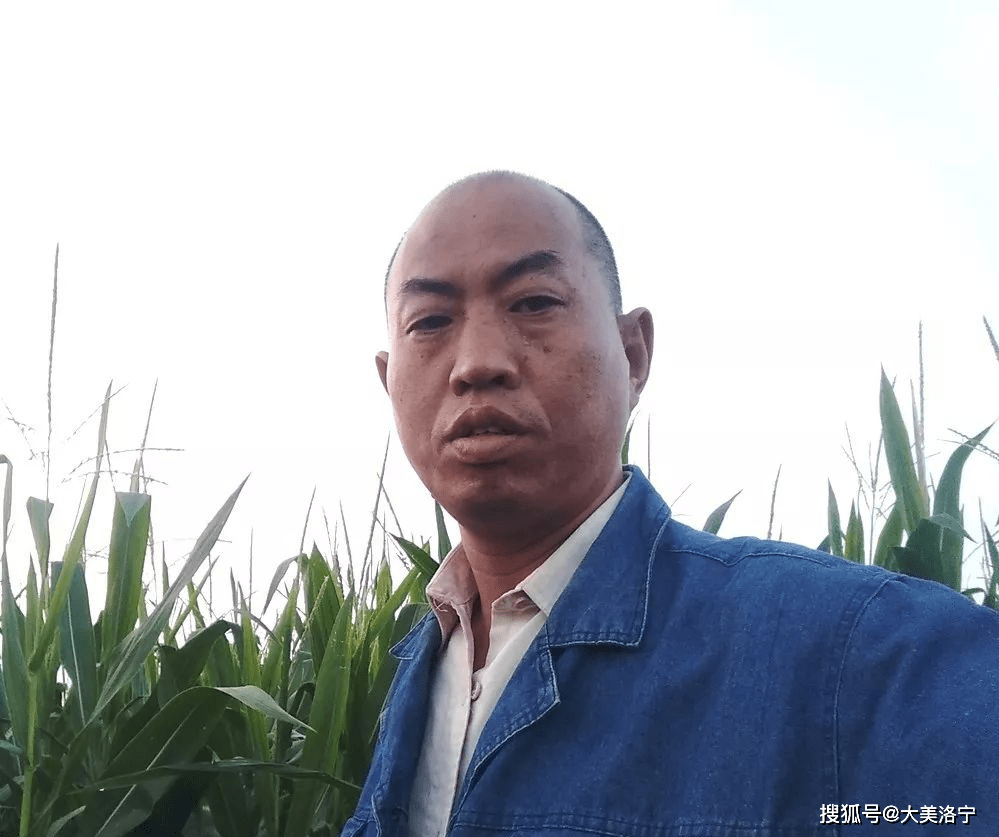
作者简介:张红歌,洛宁县河底镇人。2017年加入洛宁作协,同年加入洛宁县姓氏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