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城晨话(三十八)
每天早晨醒来第一时间想在济南说的话
杨延斌
想起麻子
咋也想不起老家的麻子学名叫什么,前几天晚上打电话请教老家的红色作家牟书会先生,才知道叫蓖麻,并说这东西早就绝迹了。管它学名土名,反正在我记忆里就叫它麻子。儿时记忆里麻子可真是能变现的好东西。但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不记得像庄稼那样成片成片地种它,年年只在道边上种上两溜,或者在地头种几颗,株距在两米左右之间。也不记得有人像收庄稼那样年年收它。
记得儿少时期,每到最热的天儿,麻子秧就长到一人来高了,成嘟噜的麻果由绿变黄变黑,在阳光暴晒下渐渐裂开嘴,麻粒儿就蹦出来掉在地下。那时候,我经常提溜着高粱杆儿编的四方小篮子,老家叫小盒子(发音huo二声),顶着炙烤人的烈日,蹲或趴在麻颗下捡麻粒儿。麻粒儿掉在地上,被晒得热热乎乎,有时感觉烫手。那麻粒儿要一粒儿一粒儿地捡,一个晌午头下来,能捡个一斤二斤,心里就感觉发财了。
因为麻子用处大,曾是我心里的宝贝。把麻秧嫩尖儿掐下来,用热水焯一下,撒上盐就是下饭的菜。麻叶长得很大,凡卖馍馍或者卖肉的,一大早就去道边掰麻叶。那个时候在集上买俩馍馍或者买斤肉,都是用麻叶一包拿着就走。麻子还是油料作物,它的含油量比棉籽儿花生都高,划跟火柴就能点着。

我几乎天天顶着烈日捡麻子,就指望拿五斤麻子能到集上换一斤油。现在说什么东西好叫“金贵”,那个年代若说啥东西好叫“贵如油”,可见那个时期油在人们心目中有多么重要。最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点的是煤(洋油)油灯,一年的灯油钱也是家里的愁。为了能省灯油钱,我几个姐姐就把麻粒儿剥了皮,用针线或者小树棍儿把麻仁儿穿成一串儿,斜竖到碗边,划跟火柴一点,点着的麻仁儿就能当油灯使。
在那种艰难困苦年月,一般人家要是不来个贵客,也不炒菜吃,主要是因为家家穷的没油。那时家家锅台里角都有个装油的瓶子,瓶嘴上塞个木塞子,因为说不定多少天也不动一下油瓶子,即便赶上炒菜的时候,也是拔下瓶塞后,把一根筷子伸进瓶嘴蘸一下,往锅里一滴答,所以每家油瓶子都是黑乎乎油滋滋的沾满灰尘。那个年月不是有个油越用越多的说法嘛,那是因为把筷子伸进瓶嘴前,都要在水里蘸一下,而筷子上的水珠儿就滴在瓶子里,久而久之,沉在瓶底的水就把瓶里的油顶到上面来,不就显得瓶里的油越来越多嘛。在那个年月呀,没听说谁家把油瓶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可能就看着那个油乎乎脏兮兮的模样舒坦。
我想起个能让人心里发酸的故事。那个时候只有过年才可能吃到油香,而家家炸油香时,都让孩子拿着油香到道边上吃,而且大人会嘱咐孩子哪里人多就到那里去吃,还要慢慢地吃,意思是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家的孩子吃油香才好,最后再拽着孩子耳朵叮嘱,要是有人想咬一口,说死说活也不能让人家咬。吃完了,把手上的油往头发上使劲儿搓搓,意思是把粘在手上的油抹在头发上,好让人家几天都能闻到头上的油香味儿。说白了,就是好不容易吃顿油香,得好好向人们现谝现谝。那时候我记得这样的情节,我和许多人看到人家孩子吃油香一样,馋得嘴上咽着唾沫,眼睛直勾勾盯着人家手里的油香。眼睁睁看着人家吃完了,也看着人家把手上的油抹在头上,就有人凑到那孩子身边,抓起人家的手举到脸前,使劲儿闻手上的余香。这个时候,我也会凑过去闻闻人家手上的香味儿。可是,五十多年后想到这个情节,难过得只想流泪。
记得有个集我拿着几斤麻子去换油,在往回家走的路上,不小心踩到一块玻璃碴子,脚下一疼身子一歪,只听啪的一声响,手里的油瓶子摔在地下。我顾不得脚疼,急急忙忙把没碎的半截瓶子拿起来,可是,多半的油都洒了,把地下浸湿一片,我急得哇哇大哭。记不得是在谁家门口了,只记得从那个有哑巴的人家走出一个婶子来,她看明白是咋回事儿后,回家拿来一个簸箕和铲子,把浸着油的土小心挫到簸箕里,俯下身子贴在我耳朵上说让我把这堆土拿回家,大意是说,回家叫你姐姐把土倒进锅里多添水烧开后,等水凉了,油珠儿就都漂在水面上,再用勺子一点点把油撇出来。就是不能吃,点灯也行啊。现在我再想起来,认为那个婶子真是有智慧。
那次几个姐姐真是那么做的,我眼见姐儿仨忙活了好一阵子,撇出了大半碗油。这样一折腾,我对麻子的印象就一辈子也不能忘了。
2022年6月24日于济南

作者简介:杨延斌,笔名水务。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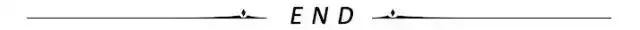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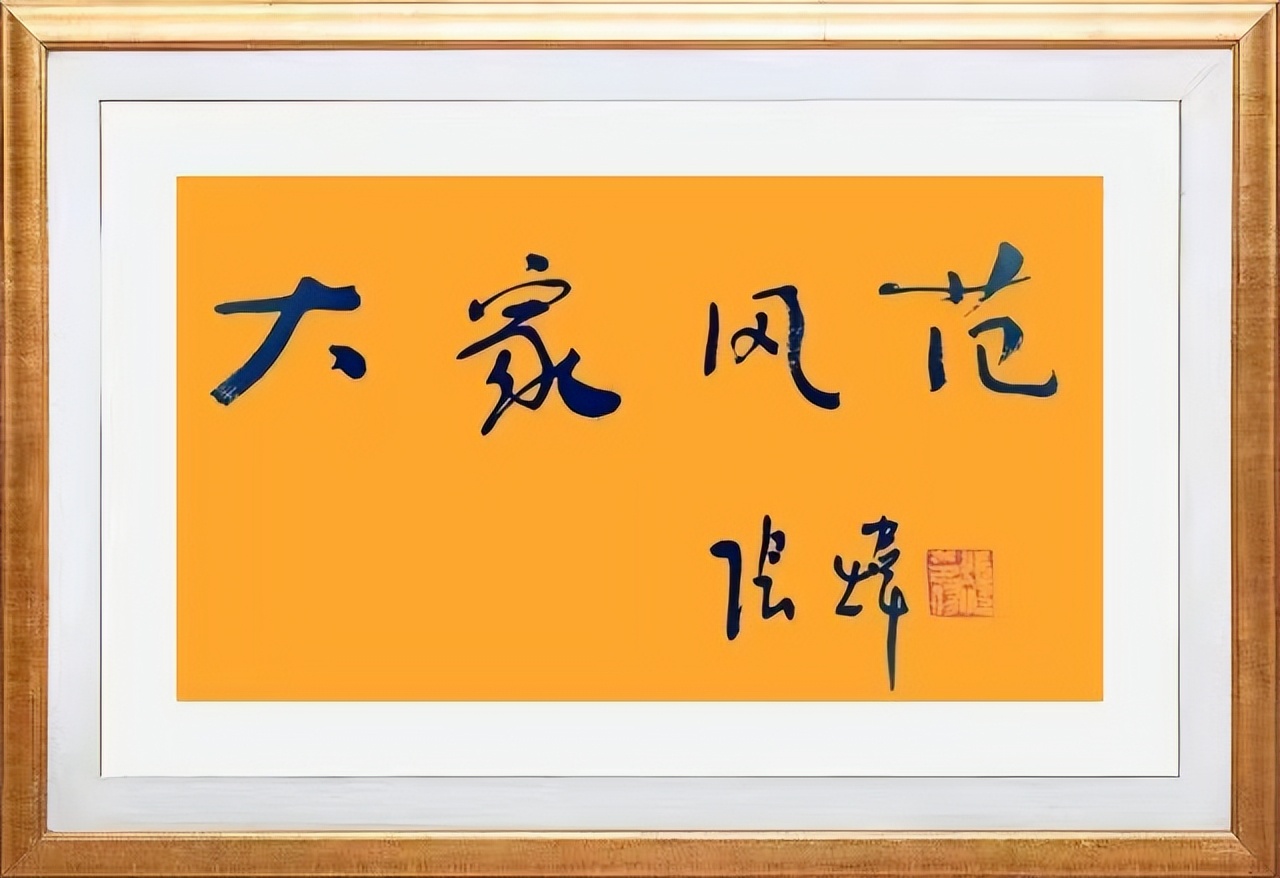
图书出版
文学、论文专著、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
国内单书号、丛书号、电子音像号、
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