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作者:赵宗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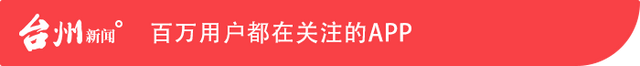
01
陈汝法先生来电,说要出版一本自己学术作品的回顾集,向我了解一些编辑体例上的问题,我随即尽我所能地作了回答。说到结束时,他突然提出,这本书的序言要我写。这真是吓我一跳。我赶紧回绝:陈老师,我无论是年龄、学识和声望都不足以当此大任,决不敢接受。等您的书出版后,我可以写一篇学习体会,作为书评。但陈老师固执己见,一定不愿妥协,再三推辞无果,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两天后,陈老师的全本书稿快递到了,我先睹为快,得以提前学习。
说起同陈老师的交往,可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兄长也毕业分配,同陈老师是同事,住宅又相邻,所以常常能相遇,并聊上几句。回首过往,居然已近四十年了。我印象中的陈老师,是儒雅学者形象,衣衫永远整洁,言语十分准确。平时讲话,既不急促也不拖沓,不疾不徐,很有师者的风范。他退休后,住在临海,偶尔也回老家住,见面较少,时有电话联系,也多是关于他家乡仙居的事。他的故乡历史积淀深厚,台州最早的文明遗址下汤、最早的摩崖石刻蝌蚪文,都在那边,加上唐宋以来,仙居文人辈出,历代古建筑保存完好的较多,所以,常有让人惊喜的古迹重新被发现。
陈老师是热心人,常常推荐故乡的一些新发现,提供他人不知的历史掌故,让记者去看看,许多内容因此得以报道。有些他推荐的内容,在当地可能新奇,在全市,却属平常,没有见报,我就向他详细解释原因,他虽然能够接受,但是,最后总是强调,他那边的东西肯定不一样的。拳拳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02
我花了两天时间,认真通读了陈老师寄来的全部书稿。
全书分两大部分,一是学术方面的内容,是他以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或文章,包括其他学者对他的评论,分为《拙撰补遗》《审稿随录》和《学界评述》。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到最近。尤其难得的是,居然还有1952年发表于《漫画》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登的艺术评论,评的是中国版画大家赵延年的作品,而作者当时只有十八岁,还是台州师范二年级的学生。稿子登了后,还收到了不菲的稿费。由此可知,陈老师少年的才华与勇气。陈老师的论文,都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对平时提笔作文的人,特别有帮助。即使今天再读,仍然没有过时,许多对我都很有教益。其中一些词义辨析方面的成果,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重读陈老师的论文,则时有追本溯源方知其详的欣喜。
二是他的自传部分《生平碎事》(包括《蒋师恩润》),虽然以短章段子体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写下,并无章节标题,但依然脉络清晰,印象深刻。人生寿命有长短,事业成就有大小,但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各人的体会都会很深刻。这些深刻的记忆,在不到三万字的篇幅里,得到充分的呈现。
对陈老师的自传部分,我特别喜欢,有三点感受最深。一是陈老师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经历十分曲折,尤其是童年和少年的生活,艰苦程度远逾想象。他少年早慧,非常懂事,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一步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教师、一位学者,其中的过程,如非当事人亲历亲记,常人难以想象,让人动容。二是陈老师非常勤奋。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甘平庸,认定目标,不惧权威,刻苦学习,钻研学问,不断自我超越。能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是花了比他人更多的努力获得的。以当时的台州地理交通条件和学术氛围,做学问非常不容易。三是陈老师坚持原则,有着台州式的硬气。这既是耿介的个性使然,更多的,则是价值取向所决定。因为出身贫寒,他更懂得百姓的苦难,对不正之风,有着天然的排斥。传统中国士的气质,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言义不言利。事关公正,必然挺身而出,不计成败利钝,有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一个文明社会所需求而恰恰当下反而在日益减少的。
陈老师博闻强记,学术成果丰硕。2019年,他出版了《管窥集》,我曾认真地学习。这次作为上次作品的补遗,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并且作为自己一生的回顾,增加了简历和生平的内容,读来更为亲切。可以说,这一本《蠡瓢集》与上一本的《管窥集》,比较全面地呈现了陈老师作为学人的立体形象。
03
国有国史,家有家史。作为一个能够执笔为文、从事一方研究的学者,写一些回顾自己经历的文章,留给后人,是非常必要的。于自己,是对一生做一个小结,于后人,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历史的丰富性,是因为人性的丰富性。而这些丰富性,只有通过大量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记录,才有了意义。台州地处江南海隅,进入正史的人物,直到《晋史》才有。缺少记载,我们就不知道前人的生活。台州在唐代,才出现了两个进士,第一个是孙郃,第二个是项斯,都是陈老师的同乡。关于台州的第一个进士,我们除了他的姓名,其他的一无所知。对项斯,除了留下一个“逢人说项”的成语,还有若干的诗篇。
陈老师此书的另一意义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生活的样本。
陈老师是新中国的同时代人。他上小学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许多经历,都已不可复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生,到九十年代以市委党校的教授身份退休,他完整地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数十年黄金时期。陈老师从一个山村的孩子,因为时代的需要,更因为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社会的脊梁,家庭也从赤贫,变成小康。这其中,既有新社会时代潮流的成分,更多的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一个人的奋斗史,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的发展史。以我个人的阅读兴趣,如果陈老师不要如此谦虚,而将自己的简历部分写得更详细,这本书就会更加精彩。
历史,无非是人生活的记录,一般有正史和野史、官方历史与民间历史之分。官方的记录,容易保存,当然需要,但民间的记录,却更加珍贵。古代因为读书人少,记录者少。最近几年,我因为写《二十五史里的台州人》一书,要翻阅大量古代的文献。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就是宋以前的台州,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前人留下的资料太少。作为一个台州人,有时候,更愿意看看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前人是如何生活的,这就希望有先人的个人记录。对社会世态的了解,正史远远比不上并不显眼的笔记更有意趣。历史,事实上都是有记录的历史。台州几千年前生活过越人,但是,现在除了他们遗留的悬棺之外,因为没有记录,对他们的生活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再如清代太平(今温岭)人戚学标,虽然《清史稿》里只有寥寥几百字的记录,但是,他的三本《回头想》《回头再想》《回头再想想》,记录了河南、浙江的官场生态与民间生活,都非常丰富和生动。尤其是作为一个官员,其敢于当众动手打一个无耻的上司,以致轰动河南官场,确实非台州式硬气而不能为。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像陈老师这样的有心人,将他的经历记载下来。陈老师的书,会因为时间的延续,愈加显示其珍贵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凡注有台州日报、台州晚报、中国台州网或台州新闻APP的稿件,均为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独家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不得转载;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台州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