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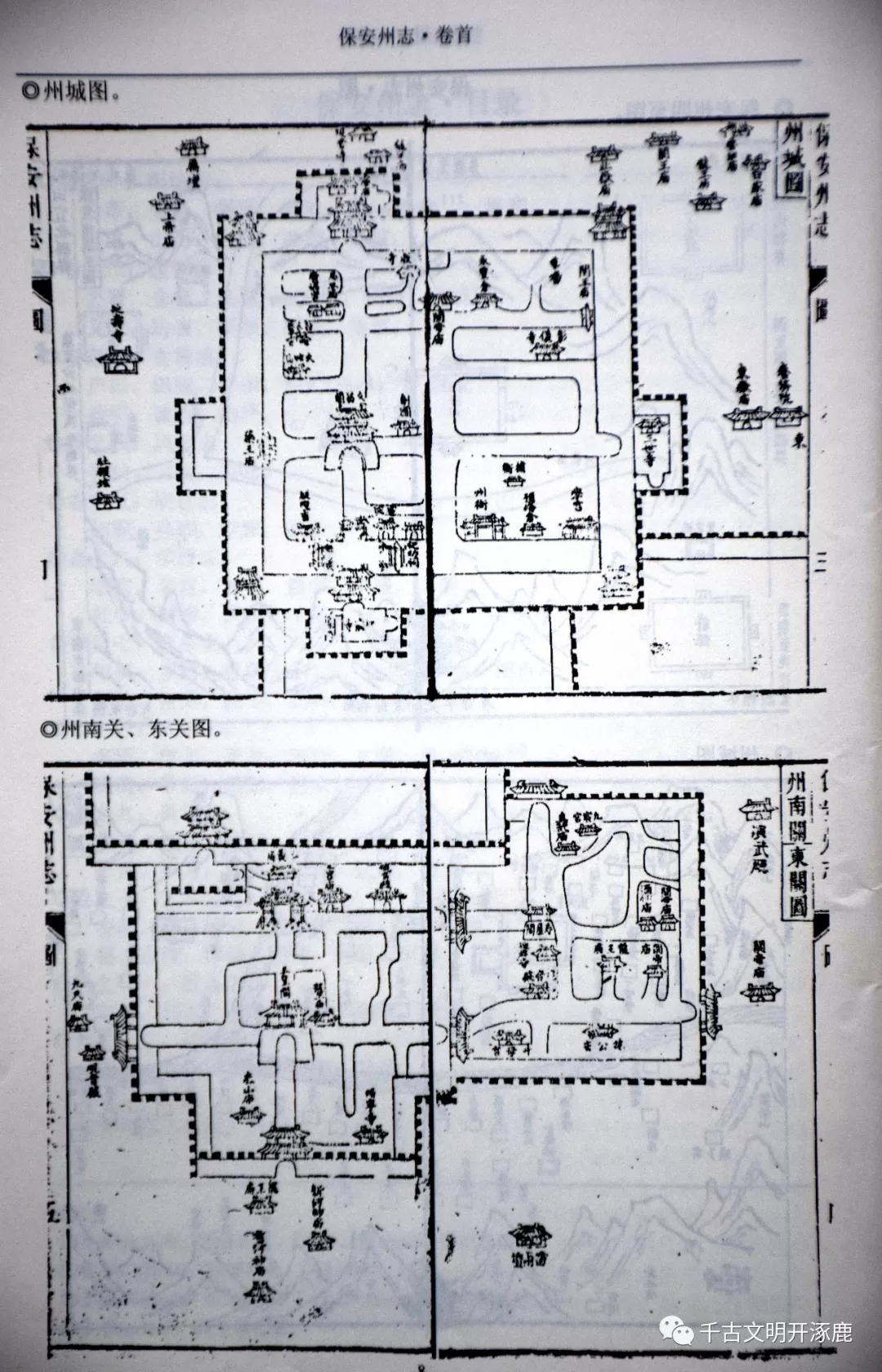
三
从葛家场西行就到石桥,所说的石桥,不是真正意义的桥,而是城里下水道的出口,桥有1.5米宽、高,上面铺着厚石板,人们就叫石桥。桥附近有一棵大槐树,北面有一个小卖铺。这个下水道一直通往现在的东风街,负责全城的排水。石桥往北是乐胜街,往南是吴油坊,往西是涿鹿剧场,这是五六十年代涿鹿最热闹的地方。那时候天天唱大戏(晋剧),下午、晚上挤得水泄不通。夏天卖冰棍的、卖汽水的、卖水果的,冬天卖糖葫芦的、卖瓜子、花生的摆满了街道两旁,到散戏后街上才安静下来。演员蔡有山、刘仙梅、郝金锐、“斜眼黑”都是人们崇拜的梨园名家。
1958年9月20日 晚上,剧院台口突然坍塌,死伤观众53人,其中死亡2人,三四百人自觉抢救伤员,小孩子们都跑回家,不敢出来了,不久剧场又修复了。1964年,演出了在我县打游击的老干部张雷编写的《变天记》,后又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等现代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彻底不演了。人们所崇拜的那些演员成了“牛鬼蛇神”,街上贴满了批判他们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后,看戏的人也少了,剧团被解散,有的调到了外地,有的改行分配到化肥厂、供销社、药材公司等企业。
盐店街
过了剧场往西,南边是盐店街,这条街没有一点变化。小时候每年在这里开物资交流会,两边一家挨一家搭满了布棚,里面放满各种商品供人们购买,非常拥挤。往南是南十字,再往南过个城墙洞就到了苑庄。南十字往 西,南边是东关小学,北面是妇幼保健站,再往 西过了城墙就是阁东街了。
涿鹿影院
从剧场往西是马站街,在我儿时它可是一个“大地方”,东边是东楼,建于清末,是东关一位姓麻的人的开的回民饭馆,也称东馅饼。我六七岁时是文化馆,一共两层,木制小楼,上下有七八十平方米吧。一楼忘了是干什么的,二楼是图书馆,我爷爷常带我来看小人书、杂志,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拆的,后来成了木制厂的车间,现在盖了商品楼。再往北一点是一家生产大车的木匠铺,现在也变成了商品楼了。对面路西 ,最早是德和森药铺,后来变成了房产管理处,转角处是“景华兴”, 这是一家综合门市,针头线脑、油盐酱醋、针织鞋袜、烟酒糖茶、食品糕点应有尽有,也是我们小时最爱来的地方。听老人们说,抗战时期,日本飞机曾轰炸这里。解放后成了供销社,后来破产了。那时候元宵节放烟花都在这里。今天这里是“郡城瑞居”商品楼的一部分。
从景华兴往西,路南是酒厂。这个酒厂解放前就有了叫裕升庆,七十年代迁到曹堡西,再往西路北是县文化馆,最早这里是三官庙,从小就记得这里有很多能人,那些写字的、画画的、拉胡胡的、弹琴的真了不起,文化馆大门两边各有四间房,西边是图书馆,东边是展览馆,院西房住人,正北是个大殿,经常举行各种展览,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英雄人物等。
东关剧场
这里每逢节假日,经常举行文艺演出,街头宣传。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抄了清凉寺,运来了许多经书和佛教用品,堆满大院西房下,我在一边看热闹,听两个大人说,这都是宝贝,真可惜了!后来不知道败到哪里去了!我参加工作后,曾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写作培训班,同时学习的还有胡宗永、李怀全、曲辰、吴建明等 ,后来这些人有的成了专业作家 ,有的当了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还有一个大官,他就是大“右派”、“反革命”刘雪苇,他是我小时见过最大的官,据说比胡、葛、解的级别都大,他穿一身蓝制服,戴一顶蓝帽子,一副眼镜,挺胖,从不与人交往,只是每天往报栏换报纸,落实政策后回北京了。听别人说老刘真了不起,是贵州省党的创始人,在延安时常和毛主席在一起,还有书信来往。有一次到北京,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县领导,他说他去看老刘了,现在人家和罗章龙正写党史呢。
从文化馆往西就到了西楼底下,(现新合作超市处),文革前西楼饭馆还在,是我县最大的回民饭馆。北面的南门(来薰门)还很完整。一进南门就进了明清时期的内城。南门比其它城门高,城墙宽。后来,几个小孩子 在南门上玩,把门楼点着了,南门楼从此消失,只剩下城墙。南门往东延着城墙就到了顺城街,城墙北有粮食局和实验小学。往西第一家是豆腐房,往里是县法院和公安局,顺城墙往 北是看守所,墙外乱坟滩,后来成了烈士陵园,现在是民政局家属楼和陵园街。东墙下是一片民房,后来盖起了百货商场,现在是步行街,西南城墙下是一片庄稼地和坟场,后来建成了光明街。
古涿鹿郡
西楼底下还有一个写有“古涿鹿郡”的牌坊,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古涿鹿郡”的牌坊,酒厂二锅头的商标上的图案,也是涿鹿一景,那时回来过年的人,外地来的客人常在这里照相留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一九六七年三月拆毁。往北是鼓楼南大街,当时有县委、邮电局、武装部,供电站等单位都在这里。正北是鼓楼即(迎旭门),它是我县的标志性建筑,据说是明万历年(1583年)建的,古楼东到头是小东门及瓮城,路北边有高小,南边有粮食局,鼓楼西城墙跟是看守所,五十年代还有一家养着木轮轿车,就和现在看电视剧里白七爷、乔致庸坐的马车一样。
鼓楼
鼓楼北是大片的青砖瓦房,街中有一个司宅的贞节牌坊,后来也拆了。路西是县人民政府。以及双井巷和任宅巷。
四
牌坊往北是北门(拱极门),文化大革命前还比较完整,进了城门就是瓮城,四四方方的,高高的城墙上有很多垛口,从瓮城东门出来就算出城了。后来搞城建时拆毁,我那时在学校念书,也参加了这一罪恶活动。北关大街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水渠,挑峻于明永乐时期(1403年)。横穿北关大街,渠上有一座桥可以走大马车,过了桥就看见观音寺了,建于明万历年(1573年),我小时觉得观音寺很大,还有不少和尚,我五、六岁跟着爷爷常去看一个和尚,他和我们有点亲戚。观音寺四周全是庄稼地,西边是一条通往下花园的沙石公路。
从北关往西一直通向黄羊山,半路上有涿鹿中学,那时觉得离县城太远了。中学对面路南有一瓦盆窑,是烧制瓦盆、瓦缸的。小时候我们很好奇的去看工人们和泥,在一个突突转的玩意上捏出瓦盆、瓦缸,象现在电视上看的一样,其实就是现在说的陶艺,在我国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可惜在我县失传了。
瓦盆窑附近有座杨家桥,桥不大但人人都知道,因为城里人的坟墓大都在西 山,出殡时参加埋葬的人上山,其它人就都回城了。牛家场东有个砖厂,全是手工操作,我父亲那时在这里工作,我常 去玩,现在是轩辕北区的一部分。
北门往东是前后巷和柳巷,儿时朱家楼现液压件厂家属楼处,是涿鹿汽车站,儿时我妈在北京工作,回来时我和大人来接,走时送,我妈一上车就哭,她哭我也哭,不过一会玩上就忘了。
朱家楼往南有个马宅,大跃进时建起我县第一家机械造纸厂,六十年代初下马了,县里调我爸和一个姓杨的大爷留守,我常来玩。这里有不少和我大小一样的孩子常在厂前的大街上玩兑阎王,就是摆上五块砖,中间的是阎王,谁兑倒了就弹别人的脑袋。有时兑钱钱,就是用硬币叠在一起,站在远处拿一块四五公分的铁板,谁砸倒了钱就归谁。
作 者 简 介
薛春孝,涿鹿城关镇人,涿鹿县印刷厂原厂长,文化学者,工程师。张家口京畿民间文化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历史研究会员,先后发表出版有《记忆中的涿鹿古城》《解放前涿鹿工商业概况》《闪宅旧事》《现在教育的奠基人王氏家族》《细说桑干河》《千年古县的诉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