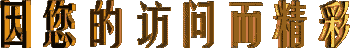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马年巨献——尹玉峰长篇硬汉小说《良马》别一番语言架构,别一番草原风情;人性、野性、眼泪、爱恨、或生或死一一铁与血的交织,在生命荒原中困苦摇曳……这是一首准格尔旗黄河第一弯山曲中流淌着的回肠荡气,即有奇幻爱情,又有铭心酸楚,更有民族民主希望和伟大生命热忱的歌。曲折的故事中一直有圣主的天驹神马,就像一面旗帜迎风飘扬……

作者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长篇硬汉小说连载十九
良 马
作者:尹玉峰
1
四奶奶的话果然应验了。那森进了衙门后,不仅得了份体面的差事,还被特许专门照料那匹失而复得的“天驹”。他在马厩里铺了最柔软的干草,每日亲自喂它上等的黑豆和苜蓿,天驹的皮毛愈发油亮,鬃毛如绸缎般在风中飘扬。
那森心思活络,借着衙门的威势,在集市上张贴朱砂写就的文告,宣称天驹乃“神马降世”,凡见者必得福运。起初,牧民们半信半疑,可没过多久,传言便如野火般蔓延——有人说,牧羊人巴图在草原上遇见天驹后,丢失的羊群竟自己回了圈;又有人说,寡妇其木格远远望见神马,她那久病不起的儿子竟一夜退烧。
渐渐地,牧民们开始自发地在敖包祭祀时供奉天驹,萨满们也将它的鬃毛系在经幡上,称其能“通灵长生天”。每逢集市,总有牧民跪在衙门外,只求远远望一眼神马,沾些福气。那森骑在马上巡视时,嘴角总噙着一丝得意的笑——他知道,这匹天驹,已经不仅仅是马,而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权柄。
夕阳西沉,马厩里只剩下四奶奶和那匹天驹。她伸手抚摸着它光滑的脊背,指尖陷入那饱满的肌肉里,触感温热而富有弹性。天驹的鼻息喷在她的手腕上,带着青草和汗水的味道,莫名让她心跳加快。
她的思绪忽然飘远,想起天驹在沙圪堵布和配马场与骒马交配的场景——那雄健的身躯、亢奋的嘶鸣、肌肉的颤动……她的掌心微微发烫,鬼使神差地,她抬手轻轻拍了一下天驹圆滚滚的屁股。
天驹甩了甩尾巴,似乎对她的举动毫无察觉,可她的脸颊却莫名烧了起来。就在这一瞬,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管家跌跌撞撞地冲进马厩,辫梢系着的白麻布在风中飘荡,像一道不祥的符咒。
“福晋!王爷……王爷在书房……咳着咳着就……没了!”
她的手指猛地僵住,天驹的体温似乎在一瞬间变得冰冷。
2
准格尔旗全境降半旗百日,哀钟昼夜不息。出殡那日,六十四名杠夫抬着金丝楠木棺,棺椁上覆盖着光绪帝特赐的明黄蟒纹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送葬队伍的最前方,八名喇嘛吹奏着三米长的铜钦,低沉的号声震得路旁的纸人纸马簌簌作响。
四奶奶一身素缟,手捧鎏金佛龛,缓步走在灵柩之后。佛龛中供奉的,是四王爷临终前剪下的辫子——按照蒙古贵族的习俗,这缕发丝将指引亡魂回归长生天。沿途跪拜的牧民们不敢抬头,只听得铜钱哗啦啦洒落的声响——那是王府特铸的“丧钱”,每一枚上都凸刻着“往生极乐”四字,既是施舍,也是彰显王府的威仪。
当灵柩行至敖包时,忽听一阵嘶鸣——九十九匹白马不知何时聚集在附近,齐声长啸。萨满高举法铃,高声道:“王爷魂归长生天,此乃吉兆!”众人纷纷伏地叩拜,唯有四奶奶低垂着眼睫,无人看得清她眼中的神色。她端坐于灵堂主位,素白孝服裹着纤细身躯,青丝绾成低髻,仅簪一支素银簪。灵前香炉青烟袅袅,檀香混着藏香的气息萦绕鼻尖,她却恍若未闻。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光绪御赐的珊瑚朝珠,珠串温润生凉,映得她指节愈发苍白。众人伏地的窸窣声里,她耳畔却回荡着昨日马蹄声——赛春格带着亲兵在府前操练,蹄铁叩击青石板的闷响,震得窗棂嗡嗡作响,分明是冲着她来的。她唇角噙着一丝冷笑,冰凉如刃,心底翻涌着不甘:王爷刚逝,这猢狲便急不可耐地示威,当她是什么?一尊泥塑的菩萨?她抬眼扫过灵堂,目光掠过那幅御笔“忠勇可嘉”的匾额,心头一刺。王爷一生,何尝不是被这朝堂的暗流裹挟?如今他魂归长生天,她却成了孤舟,飘摇在这王府的漩涡里。吉兆?呵,她只觉得寒意彻骨。赛春格的野心,像毒藤般缠绕上来,昨日他策马扬鞭的嚣张模样,又浮现在眼前——那眼神里的挑衅,分明是冲着她的权势而来。
王府正厅的自鸣钟敲了七下,钟声沉闷如雷,惊得檐角铜铃轻颤。四奶奶指尖轻抚着光绪御赐的珊瑚朝珠,朝珠是深海红珊瑚所制,光泽温润,却透着一股冷冽的贵气。她摩挲着珠串,仿佛在汲取一丝慰藉,嘴角噙着一丝冷笑,冰凉如霜。赛春格——四王爷的堂弟,昨日竟敢带着亲兵在府前操练,马蹄声震得窗棂嗡嗡作响,分明是在示威。她闭目,脑中重现那场景:赛春格身披玄色锦袍,跨坐在高头大马上,腰间佩刀寒光凛凛,亲兵们列队呐喊,声浪掀翻屋顶。那马蹄声,不是操练,是战鼓,敲在她心口。她想起王爷生前,对赛春格的纵容——那小子仗着皇族身份,横行霸道,如今王爷一死,他便迫不及待地亮爪牙。
四奶奶指尖一顿,朝珠硌得她生疼。她睁开眼,眸光如刃,扫过灵堂上供奉的王爷牌位。牌位前,香烛摇曳,映出她紧绷的侧脸。这王府,是她的战场。赛春格的示威,像一记耳光,抽得她脸颊生疼。她冷笑更甚,心底翻涌着恨意:王爷尸骨未寒,这猢狲便如此张狂,当她四奶奶是死的?她摩挲着朝珠,珠串的凉意渗入指尖,却点燃了心底的怒火。她想起昨夜密折——理藩院侍郎秘密送来,纸上残留着黄寺喇嘛加持过的藏香气味,那气味刺鼻,却藏着杀机。东协理丹丕尔凑近低声道:“老佛爷的意思……准格尔旗得有个压得住场面的人。”她当时只淡淡颔首,未置可否。如今想来,那密折的字字句句,都像毒蛇,缠绕着她的咽喉。老佛爷的“意思”,不过是幌子,真正的刀锋,是赛春格。她攥紧朝珠,指节泛白,一丝冷笑凝在唇边。这朝堂,从来不是讲理的地方。王爷的魂灵还在天上飘着,人间的争斗却已白热化。她垂眸,掩去眼底翻腾的算计:赛春格若上位,以他的性子,必定会削她的权,甚至可能逼她守寡终生。她可是光绪的姑母,金枝玉叶,怎能任人摆布?这念头一起,便如野火燎原,烧得她心口发烫。她深吸一口气,檀香的气息钻入肺腑,却压不住那股焦灼。灵堂外,风声呜咽,似在催促一场风暴。
正沉吟间,西协理捧着黄绫匣子匆匆进来,匣中赫然躺着老三爷的度牒——这位早已出家的四王爷的叔叔,如今成了她手中最稳妥的棋子。西协理是王府的老臣,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却透着一股精明。他捧着匣子,躬身行礼,声音低沉:“四奶奶,老三爷的度牒,按规矩送来了。”四奶奶抬眼,目光如电,扫过那匣子。匣子是黄绫所制,金线绣着云纹,庄重而神秘。她缓缓起身,走到西协理面前,接过匣子,指尖轻抚匣面,感受着那丝滑的触感。她打开匣子,度牒静静躺在其中,是老三爷出家时的信物,如今却成了她手中的筹码。
老三爷,四王爷的叔叔,早年因看不惯家族争权夺势,明争暗斗而出家,如今在寺庙中清修,却成了她最稳妥的棋子。她摩挲着度牒,纸张的质感粗糙,却透着一股力量。她垂眸,掩去眼底翻腾的算计。
3
老三爷盘腿坐在召庙的蒲团上,蒲团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露出里面暗黄的填充物。他身上的绛红色袈裟也褪了色,领口处还沾着几点陈年的茶渍。手中的转经筒早已停了转动,筒身刻着的六字真言被摩挲得模糊不清。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他布满皱纹的眼皮颤了颤,却固执地不肯睁开。这声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刮着他的心。三十年了,他以为自己早已斩断尘缘,可这马蹄声却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想起年轻时在王府的日子,想起那些勾心斗角的夜晚,想起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如今这马蹄声又来了,像命运的召唤,让他无法抗拒。
"师父,您就还俗吧。"小喇嘛第十次捧着崭新的锦缎官服跪在他面前,锦缎上绣着金线云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旗里不能没有主事人啊。"小喇嘛的声音带着哭腔,额头上还沾着未干的泪痕。老三爷枯瘦的手指死死攥着佛珠,青筋暴起,像老树的根须。"老衲三十年前就断了尘缘......"他喃喃道,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可这声音却像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三十年前,他被迫出家,以为这样就能远离尘世的纷扰,可如今看来,尘世却像一张网,始终笼罩着他。他想起自己出家前的誓言,想起那些在佛前许下的承诺,如今却像风中残烛,摇曳不定。
话音未落,庙门突然被撞开。一道雪白的影子旋风般冲进经堂——竟是那匹传说中的天驹!它昂首立在佛像前,银白的鬃毛在香火中泛着奇异的光泽,像月光下的瀑布。老三爷浑浊的双眼猛地睁大,手中的佛珠"啪嗒"一声散落满地,滚落在蒲团旁。"老、老天爷啊......"他干裂的嘴唇哆嗦着,竟忘了继续诵经。天驹打了个响鼻,忽然转身向外走去,每走几步就回头望他一眼,眼神里带着某种期待。老三爷的心跳突然加快,像擂鼓一般。他想起幼时听过的传说,想起那些关于天驹的神秘故事,如今这匹神马竟出现在他面前,像命运的使者,来接他重返人间。
庙里的喇嘛们都惊呆了。只见年过六旬的老三爷颤巍巍地站起来,像被勾了魂似的跟着天驹往外走。小喇嘛慌忙去拦:"师父!您的袈裟!"可老三爷充耳不闻,赤着脚就追了出去。他的脚底板踩在滚烫的沙石路上,却浑然不觉疼痛。他的目光死死黏在前方那匹通体雪白的天驹身上,恍惚间竟觉得马背上泛着一层佛光,像菩萨的化身。"这...这莫非是菩萨点化?"他干裂的嘴唇颤抖着,三十年的禅定功夫在这一刻土崩瓦解。额头的戒疤隐隐发烫,仿佛在提醒他破戒的罪过。可那双枯枝般的老腿却像有了自己的意志,一步接一步跟着神马往前挪,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
天驹雪白的鬃毛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那马儿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用湿润的鼻头轻触老三爷枯瘦的手腕。一股温热的气息喷在他手背上,带着青草与阳光的味道,像春天的气息。"你..."老三爷的指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天驹竟像通人性般,用牙齿轻轻叼住他的袖口往前拽。这一刻,他恍惚看见马眼中映出自己的倒影——那个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老喇嘛,此刻眼中竟重新燃起少年时的火光,像沉睡的火山突然喷发。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想起那些在佛前许下的誓言,如今却像被风吹散的烟雾,消散在空气中。
4
路过经幡阵时,天驹突然仰天长嘶。老三爷下意识抬手想抚摸马颈,却在触碰到油亮皮毛的瞬间如遭雷击。他分明感觉到,掌心下的肌肉正随着呼吸起伏,那是鲜活的生命力,是他在经卷中寻找半生却不得的真谛。"孽障!"他低声咒骂,却将手指更深地埋入马鬃。天驹甩了甩尾巴,一滴汗水从马颈溅到他脸上,咸涩得像是眼泪。远处传来四奶奶的呼唤,天驹突然屈起前腿,做出一个近乎跪拜的姿势。老三爷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想起幼时听过的传说:成吉思汗的白马会在真命天子面前屈膝。此刻夕阳西沉,天驹的轮廓镶着金边,宛如从长生天画卷中走出的神兽。当马唇再次触碰他掌心时,他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偷到糖的孩子,脸上皱纹舒展开来,像春日的暖阳。
"罢了..."他扯下颈间的哈达系在马辔上,哈达是洁白的,像天驹的鬃毛。"老衲就随你走这一遭。"天驹欢快地打了个响鼻,热气喷在他皱纹纵横的脸上,竟让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那个吻,温暖而湿润。路过敖包时,系着的经幡突然无风自动。老三爷浑身一颤,想起自己少年时,曾在此立誓要光耀门楣。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不愿意看到王府里的勾心斗角,青灯古佛下的无数个长夜……一滴浑浊的泪砸在沙地上,瞬间被晒得无影无踪。他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那些被他深埋的记忆,如今却像野草一样疯长。
旗府的红漆大门近在眼前,他突然看清门楣上挂着的,正是当年老王爷亲笔题写的"世袭罔替"匾额。匾额上的金漆已经斑驳,却依然透着威严。天驹在门槛前优雅地转身,琥珀色的马眼直直望进他心底。老三爷双腿一软,竟扑通跪倒在地。"长生天啊..."他嘶哑的嗓音惊飞了檐下的麻雀,"原来您早给我安排好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像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远处传来了琴声和长调短调的歌声,东协理丹丕尔、那森、少年奇子俊、兽医布和等人,抚琴放声歌唱。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像春天的溪流,冲刷着老三爷心中的阴霾。
此刻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三十年的修行,不过是在等一个体面还俗的契机。远处传来四奶奶刻意拖长的"恭迎王叔回府",他抹了把脸,在起身的瞬间,将腕上的佛珠悄悄塞进了袖袋最深处。佛珠是他的念想,是他三十年修行的见证,如今却要被他暂时收起。天驹踏着碎步跑到人群中间,鬃毛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晕,像燃烧的火焰。它突然扬起前蹄打了个响鼻,惊得丹丕尔的琴弦迸出个滑音,那森的酒碗差点脱手。少年奇子俊笑着去抓它缰绳,却被它灵巧地甩头避开,反倒用鼻子亲昵地拱了拱兽医布和腰间的奶豆腐袋子。布和突然发现天驹左前蹄沾着朱砂——正是老三爷佛袍内衬的颜色。他向拉琴的丹丕尔、那森、少年奇子俊示意着,在大家交换的眼神里,琴声已悄悄转成了《甘珠尔》的调子。西边最后一片云彩正巧掠过"世袭罔替"的匾额,将金漆斑驳的"替"字映得忽明忽暗,像命运的暗示。
四奶奶提着绣缠枝莲的袍角轻快地走来,发间银流苏随着步伐叮咚作响,像银铃在风中摇曳。她伸手抚过天驹汗涔涔的颈侧,突然踮起脚尖凑近马耳朵:"好孩子,通人性!"清亮的嗓音惊得马儿睫毛乱颤,琥珀色的眼珠里映出四奶奶的喜悦。老三爷看着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想起那些在佛前许下的誓言,如今却像被风吹散的烟雾,消散在空气中。可此刻,他却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