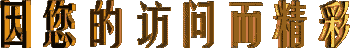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
连载十八
作者:尹玉峰(北京)
蝉鸣烫伤山坡时,赵泼儿
鬓角的汗珠里,藏着一朵
野姜花,铜锣声撞碎
正午的寂静,云臭头
笨拙地接住抛来的梨,汁液溅溢
或是梦中野姜花突然绽放的印记
1
夏日的涧水河村,蝉鸣聒噪得像是要把整个山坡掀翻。臭头蹲在赵驼子家后院的榆树下,腰间挂着赵驼子刚给系上的双联璧佩,铜锣在手里沉甸甸的。他低头看着铜锣上斑驳的铜锈,那些锈迹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痕迹。铜锣的边缘有些磨损,摸上去有些粗糙,但握在手里却格外踏实。臭头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铜锣表面,心里盘算着待会儿打锣时的节奏。
"打锣,打锣——我,锵——臭头打锣......"赵驼子佝偻着背,铜锤在锣面上敲出清脆的声响,声音在闷热的空气中回荡,"先把我放在前面,接着报个名号,再接着说具体事儿,一定要顺口。"赵驼子的声音带着沙哑,像是被砂纸磨过,每一声都透着疲惫和无奈。他佝偻着背,双手微微颤抖,铜锤在锣面上敲出的声响却异常响亮,仿佛要把积压在心底的苦闷都释放出来。
臭头盯着铜锣上斑驳的铜锈,他正走神,忽然听见细碎的脚步声,一抬头,赵泼儿就站在篱笆边上,碎花衬衫的领口湿了一片。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几缕发丝贴在脸颊上,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藏着星星。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一些野菜,绿油油的,还带着露水的清新。
"你这死丫头!你这害人精!"赵驼子转身时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一条条扭曲的蚯蚓,他抄起铜锤就朝女儿抡去,"老子打死你!"他的声音里带着愤怒和无奈,眼神中却透着一丝不舍。
臭头腾地站起来,横在两人中间。铜锤结结实实砸在他肩胛骨上,发出闷响。他疼得龇牙咧嘴,却像堵墙似的纹丝不动。赵驼子调转方向,臭头也跟着挪步,铜锤次次都落在他身上。每一次锤击,都像重锤砸在臭头的心上,但他咬紧牙关,没有退缩。他心里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赵驼子打到赵泼儿,她是那么的弱小,那么的需要保护。
"我不能让你打着赵泼儿,"臭头的声音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一丝倔强和坚定,"打我吧,出出气就顺当啦。"他的眼神中透着无畏,仿佛在告诉赵驼子,他愿意承担一切。
赵泼儿从臭头背后探出头。她看见铜锤砸在臭头古铜色的皮肤上又弹起来,肌肉绷紧时泛着油亮的光。臭头的背心被汗水浸透,贴在后背上显出结实的轮廓,像一座小山。她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她从未见过有人为了保护她而挨打,这种感觉既陌生又温暖。
"臭头,好样的,"赵泼儿突然说,声音里带着鼻音,像是被风吹过的树叶,"能找着好媳妇儿!"她的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眼睛却亮得惊人。
赵驼子的铜锤悬在半空。他眼珠子转了转,用锤柄捅了捅臭头的腰眼。臭头涨红了脸,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淌,像是被烈日烤化的冰。"那...那你就做俺媳妇儿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带着一丝期待和羞涩。
"美的你!"赵泼儿嘴上这么说,眼睛却弯成了月牙,像是两弯新月挂在天空。她看见臭头耳根红得能滴血,喉结上下滚动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2
臭头突然抢过赵驼子手里的铜锣,锵,锵,锵——"打锣,打锣——我,锵——臭头打锣,锵,锵,锵——"臭头脑门发亮,即兴编着词。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充满了热情:"锣声响,心跳快,锵,看见了赵泼儿小丫蛋儿......"他的眼神中透着欢喜,像是在诉说着一个秘密。
赵驼子嗷地一嗓子:"好!上道了!"他跺着脚催促,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继续顺口整!"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像是被阳光照过的花朵。
臭头越敲越起劲,铜锣在他手里像活了过来。每一次敲击,都像是在敲响心中的鼓点。"锵——小丫蛋儿,招人爱,锵,招人爱,小丫蛋儿......"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像是在呼唤着什么。
"锵,锵,锵——你有情,我有爱,锵——咱们俩儿一铺盖!"他的眼神中透着期待,像是在描绘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谁跟你一铺盖呀,"赵泼儿跺脚,发梢扫过臭头的胳膊,像是被风吹过的柳枝,"臭头臭脑的!"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嗔怪,但眼睛里却满是笑意。
臭头不依不饶,铜锣敲得震天响:"锵,锵,锵——只要感情在,锵——锣锅都有派......"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倔强,像是在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糟溅谁呢?"赵驼子踹了臭头一脚,却掩不住嘴角的笑。他的动作有些笨拙,但却充满了温情。臭头挨了踹也不躲,铜锣声更密了:"锵,锵,锵——只要感情在,锵——锣锅都有派,麻子放光彩,锵,哑巴也会拽,锵——臭头也不赖!"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得意,像是在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赵泼儿突然笑得直不起腰,眼泪都笑出来了。她抹着眼角说:"臭头你背我吧,就像小时候玩的猪八戒背媳妇!"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调皮,像是在回忆着童年的快乐时光。
臭头手一抖,铜锣差点掉地上。他慌里慌张地把锣塞给赵驼子,蹲下身时膝盖磕在石头上都顾不上疼。他的动作有些笨拙,但却充满了决心。赵泼儿趴上来的瞬间,他闻到她头发里野姜花的味道,混着汗水的咸涩。这种味道让他心里一颤,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
"驾!"赵泼儿拍他肩膀。臭头像匹撒欢的骡子,背着她在院子里转圈跑。他的脚步有些凌乱,但却充满了力量。赵泼儿的笑声像铃铛,发梢扫在他脖子上痒痒的。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像是被阳光照过的田野。赵驼子张着嘴站在一旁,铜锤从手里滑落都没察觉。他的眼神中透着一丝欣慰,像是看到了女儿的幸福。
"哎呀我的妈呀!"尖细的嗓音刺了进来。张寡妇挎着菜篮子站在栅栏外,她女儿张红踮着脚往院里瞅,"整这风流快活的场面,不正经啊!"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嫉妒和不满,眼神中透着一丝刻薄。
臭头感觉赵泼儿的手指突然掐进他肩膀肉里。她凑到他耳边,热气喷在耳廓上:"离开她俩远远地跑。"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焦急,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臭头撒腿就往山上冲。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像是在逃离一个危险的地方。赵泼儿在他背上颠簸着,拳头捶他肩膀:"有劲!再快点!"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像是在享受着这场奔跑。他跑过玉米地,蹚过小溪,直到两腿发软跪在山坡上。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像是被烈日烤过的空气。赵泼儿顺势滚到草地上,胸脯剧烈起伏着:"真开心啊!"她的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像是被阳光照过的花朵。
臭头躺在她身边,望着天空中的云朵。云朵像棉花糖一样,软绵绵的,飘在湛蓝的天空中。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像是被阳光照过的田野。
3
蝉鸣撕扯着山坡,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赵泼儿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觉得臭头干柴烈焰,会随时无礼。于是忙起身,蹲在远处涧水河边,用衣襟兜着刚摘的南果梨,鬓角的汗珠在光线下闪着细碎的光。臭头跟上,蹲在不远处,盯着她汗湿的鬓角,突然发现她衣领下若隐若现的淤青——像一片被风吹皱的野姜花瓣,带着淡淡的青紫。他喉咙发紧,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身子,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赵驼子给系的双联璧佩。那佩玉被太阳晒得发烫,硌着他的皮肤,却像一颗跳动的心,提醒着他此刻的悸动。
“你就老实跪在这里歇歇吧!”赵泼儿像受惊的兔子般弹起来,衣襟里的梨子差点滚落。她跑出几步又回头,看见臭头狼狈地爬起来追,却因为腿软摔了个跟头。他手忙脚乱地撑着地,膝盖蹭在石头上,渗出一点血珠。赵泼儿笑得更大声了,笑声在山谷里荡出回音,像一串银铃,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臭头瘫坐在草地上,看着赵泼儿的背影消失在果树林里。他摸到腰间赵驼子给系的双联璧佩,被太阳晒得发烫。山风吹来,带着远处铜锣的余音,像是赵驼子还在敲着那曲没打完的调子。那声音忽远忽近,像一首未唱完的歌,在空气中飘荡。臭头闭上眼,耳边却突然响起赵泼儿的笑声,清脆悦耳,像山间的溪流。
“过来呀,过来呀!”赵泼儿欢快的声音从果树林深处传来。臭头闻声追着赵泼儿钻进自家的南果梨树林,枝丫上青果子结得密密匝匝,像一群青涩的少年,挤在一起说悄悄话。赵泼儿突然从树后闪出来,手里晃着个印着英文的矿泉水瓶:“认识这字儿不?”
臭头搓着皴裂的手掌凑近,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像蚯蚓爬。”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羞涩,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那瓶子上的英文像一群陌生的蚂蚁,爬在他的视线里,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这叫矿泉水!”赵泼儿拧开盖子往他脸上弹水珠,水珠落在他的鼻尖上,凉丝丝的,“城里人喝这个,不像我们抱着水瓢咕咚咕咚。”她声音突然卡住——想起那个骗她的男人也是这样,用玻璃杯给她倒矿泉水,说这叫情调。那男人的笑容像一杯温吞的茶,暖得不真实。她的眼神黯淡了一瞬,随即又亮起来,像被风吹过的野姜花。
臭头抹着脸憨笑:“咱山泉比这甜。”他摘了个南果梨在衣襟上蹭蹭,动作笨拙得可爱,“你尝尝?”
赵泼儿接过梨子却往他领口里塞:“呆子!这品种得一俩个月后才甜!”梨子贴着臭头胸膛往下滚,他手忙脚乱去捞,衣襟被扯得歪歪扭扭。赵泼儿咯咯笑,笑声像一串风铃,在树林里回荡。笑着笑着,她突然蹲下,用树枝在地上画高楼:“知道城里楼房多高不?比五十棵老梨树摞起来还高!”
臭头数着手指头算不清,赵泼儿把树枝折成两截:“算了,跟你说也是对驴弹琴。”她瞥见臭头沾满泥的解放鞋,想起城里男人锃亮的皮鞋,突然抬脚踩他鞋面:“教你跳交谊舞!”
臭头踩着自己鞋带摔进草丛,压倒一片野山菊。赵泼儿看着他头发上粘的草籽,想起舞厅里旋转的彩灯,鼻子一酸:“笨死了!人家城里人...”话没说完就背过身去。她的肩膀微微颤抖,像一片被风吹落的野姜花瓣。
4
晌午的太阳把河滩鹅卵石晒得发烫。赵泼儿坐在臭头平时洗山杏的青石板上,晃着腿指挥:“把你那破果园最好的果子摘来!”
臭头蹚着水回来时,怀里兜着十几个青中泛黄的山杏。赵泼儿拈起一个对着太阳看:“知道城里水果店怎么摆吗?”她掏出皱巴巴的纸巾铺在石头上,把山杏摆成金字塔,“要垫雪白的纸,打暖黄的灯...”
“那多费电。”臭头刚开口就被杏核砸中额头。他捂着额头,委屈巴巴地看着赵泼儿。她却突然拽过他手腕,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表:“看好了,长针指这儿短针指这儿就是午休时间——我们山里人就知道看日头!”她画得太用力,笔油渗进臭头手腕的皱纹里,像一道细小的伤痕。
臭头盯着"手表"直乐,逗了赵泼儿一句:“能走字不?”
“土包子!”赵泼儿把剩下的山杏全倒进河里。臭头扑通跳下去捞,裤子湿到大腿根。赵泼儿在岸上跺脚:“那些在城里都是喂垃圾桶的!”可当臭头捧着捞回来的山杏上岸时,她却又挑了个最圆的在衣角擦擦,咬出个月牙印。她的动作轻柔得像一片野姜花落在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日头偏西时,臭头背着两筐南果梨跟在后头。赵泼儿突然指着他筐子喊:“停!你摆果子的手法不对!”
她夺过筐子,把梨子一个个重新排列:“要蒂朝下脐朝上,城里超市都这么摆...”手指突然颤抖起来——那个男人教她摆红酒时也这样从背后环着她。她的动作僵住了,像被定格的野姜花。臭头却跟着描,粗手指碰烂了两个梨子。赵泼儿突然抢过筐子:“算了,你个山把式一辈子学不会!”
路过山神庙时,赵泼儿扯住臭头袖子:“会把自己名字写得漂亮点不?”没等他回答,就抓着他手指在香灰里画:“赵——泼——儿——,这是我的名字,看清楚了,多浪啊!”
臭头跟着描,灰簌簌往下掉:“俺...俺,俺写'臭'字...”赵泼儿噗嗤笑了,笑着笑着用脚尖抹平香灰:“算了,反正你这辈子用不着签字。”
赵泼儿从兜里掏出一个精制的小方盒打开:“给你见识一下吧。”小方盒里面是城里卖的梨干,凝着雪白的糖霜。赵泼儿捏起一片,想起城里咖啡馆的方糖,突然把梨干塞进臭头嘴里:“甜得齁嗓子!”
山风吹乱赵泼儿的碎发,发丝间隐约可见耳朵上有个结痂的耳洞——那是她扎了三天才敢戴耳环留下的。臭头盯着看,被她转身瞪回去:“看什么看!没见过仙女啊?”
暮色中,臭头望见赵泼儿把梨干偷偷往嘴里送,腮帮子一鼓一鼓像只松鼠。他低头看手腕上晕开的"手表",觉得今天学的比赶十趟集都多,尽新鲜玩意儿。山风里,野姜花的香气若有若无,像赵泼儿的笑声,轻盈而温暖。
“赵泼儿!”臭头突然喊。
“咋了?”赵泼儿回头,眼睛亮得像铜锣。
“你...你明天还来不?”臭头挠着头,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
赵泼儿笑了,笑声像一串风铃:“来,咋不来?你这破果园,我还得教你怎么摆果子呢!”
臭头也笑了,他的笑容像山间的野姜花,朴实而灿烂。山风里,铜锣声又响了起来,像是赵驼子在敲着那曲没打完的调子,又像是野姜花在风里轻轻摇曳,诉说着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