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车轮滚滚,思绪万千
文/宋美英
车轮滚着,匀匀的,颤颤的,载着人往北去。窗外的景致,像是谁把一卷无头无尾的灰黄旧画,懒懒地、却又不停地往后抽。初时还有些疏疏落落的村庄、秃了顶的寒林、冻得发亮的麦田,渐渐地,便都融化在一片无边的、灰茫茫的平野里了。这平野是静的,静得有些肃杀,只有远处偶尔闪过一两根高压线的铁塔,像巨大的、沉默的符号,证明着这大地尚未全然睡去。可这静,却衬得我心里那份不安,越发地突突地跳着了。
我是从齐河动身的。那是个顶平常的鲁西北的村子,名字里虽带着“河”,却常年见得干涸的河床多过丰沛的水。土地是慷慨的,也是吝啬的;养活了世世代代的人,也把一些看不见的、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人的心坎上。比如,对“男丁”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执着。这执着,不独是我,怕是这黄土地上许多像我这般年纪的妇人心头,都拂不去的一层尘。女儿在电话里说:“妈,检查着,又是个姑娘。”话音是轻快的,带着北京腔儿那种脆生生的亮。可我这心,就在那一个“又”字上,猛地一沉,随即“咯噔”地一跳,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把心攥紧了,又倏地松开,留下一片空落落的慌。
思绪便不由得飘回八年前。那时女儿刚生头胎,也是个玉雪可爱的女娃娃。我赶去北京伺候月子,欢喜自然是真欢喜,可夜里躺下,听见胡同深处不知谁家传来隐约的叹息,或是瞥见亲家母那虽笑着却总像隔着一层的客气,心里便总像悬着半块石头。
车轮碾过钢轨的接缝,“咣——当,咣——当”,那声音沉闷而规律,像是亘古就有的节奏,催着人往一个既定的方向去。我想起女儿。她从小就有主意,念书肯吃苦,硬是凭着本事,从那灰黄的村子里考出去,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鸟儿,飞过了黄河,飞到了那只能在电视里看见的、有着天安门和故宫的城市。她读了研究生,找了体面的工作,又寻了那么好的归宿。她的世界,是宽阔的、明亮的,是互联网、咖啡馆、学术论坛和国际航班。她的世界,离
可我呢?我这颗被故乡的泥土浸染了大半辈子的心,为何总也熨帖不平?车轮滚滚,载着我奔向女儿的新生活,奔向一个即将诞生的、与我血脉相连的小生命,可我的魂,倒像有一半被那“咣当”声震得留在了后头,留在了齐河那方总爱论个“男女”的院落里。我替女儿悬着心。我知道这心悬得或许毫无道理,甚至有些“小人之心”,可它就是那样不由分说地悬着。我怕那些看不见的、轻飘飘的失望,会像初冬的寒雾,悄无声息地漫进女儿那扇明亮的窗,沾湿她的眉睫。我更怕的,是女儿自己。她现在说着“不在乎”,可万一……万一周遭那无形的压力,日子久了,连她自己也不曾察觉地,在内里生出些细细的裂纹呢?我见过太多开始时说着“男女一样”的脸,到最后,那笑模样是如何在岁月的风里一点点淡下去的。
窗外的天光,不知不觉暗了一层。北方冬日的白昼,总是短得有些仓皇。远方的地平线上,开始有了一簇一簇的光,先是疏落的,继而便稠密起来,连成一片浩瀚的、流动的光的海洋。那光不是家乡夜里零星的、温吞的灯火,而是璀璨的、跳跃的、带着现代节奏的星河。北京要到了。
那片光的海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切,仿佛能听见它磅礴的呼吸。车厢里起了轻微的骚动,人们开始收拾行李。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又抚上了手机屏幕,那张女儿发来的大孙女笑吟吟的照片。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没有一丝阴翳。
忽然间,我心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嘣”地一声,仿佛松了些。车轮依旧滚滚,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奔向未来的气势。我想,我或许真是多虑了。女儿的世界,有它自己的法则和光芒。我要去的,不是一个需要用老尺子去丈量的地方,而是一个需要我用全然新生的喜悦去拥抱的家。那里有一个叫我外婆的小人儿,很快,又会多一个。
至于别的,至于那些盘旋心头的、来自另一片土地的古老尘埃,就且让它们留在身后这片疾驰而过的暮色里吧。车轮滚滚,载着人向前。而前方,是家,是血脉的延续,是无论男女、都一般珍贵的、等待啼哭的新生。
我轻轻吁出一口气,那白雾在冰冷的车窗上,呵出了一小片朦胧而温暖的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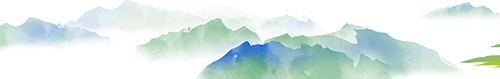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