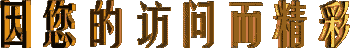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连载十四
风怜惜
作者:尹玉峰(北京)
野姜花依然在篱笆外,数着
风偷走的时辰,像数一串串
遗落的记忆,更像数着
云秀的眼泪。一滴一滴
又一滴,当最后一滴泪落入
泥土,淡雅的香气被风怜惜
1
正午的日头毒辣辣地烤着涧小河村,知了在杨树上扯着嗓子嘶鸣,那声音像是要把这炎热的空气撕裂开来,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种烦躁不安的氛围中。云祥福踩着晒得发烫的山石路来到村小学,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脚底传来阵阵灼痛,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身上的蓝布褂子早已被汗水浸透,后背洇出一片深色的汗渍,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他抬头望了望那刺眼的太阳,心里暗叹这天气真不是人过的,但一想到女儿还在学校,便咬咬牙继续往前走,脚步坚定而有力。
云祥福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滚烫的山石路上,瞬间蒸发。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对知识的渴望,可那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整日以泪洗面。作为长子,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每当夜深人静,他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失落。如今,女儿云秀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在村小学教书,忽然让他既欣慰又自豪。欣慰的是,女儿实现了自己未能完成的梦想;自豪的是,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自家出了个有学问的人。这种感觉是在此时,忽然间获得的,而平时,云秀在他眼里是憎恨的,云秀长着像她妈妈一样的俊俏脸,她妈妈早就出走了……
推开刷着绿漆的木头校门,那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也仿佛在提醒着人们,这所村小学已经陪伴了涧小河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长。云祥福的异样的目光在校园里缓缓扫过,破旧的教室、斑驳的墙壁、简陋的操场,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童年的记忆。他记得自己小时候,也是在这所小学里,用稚嫩的小手握着铅笔,在作业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字。那时的老师,是一位慈祥的老者,总是耐心地教导他们。如今,时光流转,物是人非,但教育的光芒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闪耀。云祥福惊讶自己平时路过村小学时,没有这种感觉,今天为什么瞧见什么都感觉新鲜,心里就顿起波澜呢?
云祥福看见女儿云秀正蹲在教室门口给几个孩子补课,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在她白底碎花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仿佛给她披上了一件梦幻的外衣。云秀的头发被汗水打湿,几缕发丝贴在额头上,但她依然专注地给孩子们讲解着题目,那认真的模样让云祥福心里一阵暖流涌过。他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女儿与孩子们互动,心中满是感慨。女儿的眼神里透着坚定与温柔,她耐心地解答着孩子们的问题,时而用手比划,时而用生动的例子说明。那些孩子们,有的眼神充满好奇,有的则略显羞涩,但都在认真地听着。云祥福忽然想起自己当年辍学时的无奈,如今看到女儿能够成为村里的文化人,给孩子们传授知识,他心里既欣慰又自豪,仿佛看到了自己梦想的延续。
“云秀,走,回家吃饭去。”云祥福搓着粗糙的手掌,声音像晒蔫的庄稼似的软和。这是他极少有的温柔时刻,平日里他总是板着一张脸,尤其对女儿云秀有这般和蔼的语气。云秀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那诧异中还带着一丝惊喜。有生以来也没有见过父亲这么和蔼可亲,她心里不禁想,父亲今天是怎么了?是有什么好事发生,还是单纯心情好?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那些还在认真听讲的孩子,有些为难地说:“爸,等我把这几个孩子的题讲完再走,他们马上就要考试了,不能耽误。”
云祥福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似乎明白女儿的心思,知道她放不下这些孩子,让他感到无比欣慰。他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女儿。
正在批作业的云功德校长比划着,粉笔灰从袖口簌簌落下,像是下了一场小雪。他笑着冲云秀点点头,那笑容里满是慈祥,仿佛在说父女之间就该这样亲密无间。云功德校长是涧小河村的老教师,在这里执教了几十年,见证了无数孩子的成长。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也明白云秀对孩子们的用心。看到云祥福和云秀之间的互动,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爱与责任的传承。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正是因为有像云秀这样的年轻教师,才能让知识的光芒照亮孩子们的未来。
他冲教室后排努努嘴,“云娜,你也跟着去。”云娜是云秀的妹妹,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听到校长的话,她兴奋地跳了起来,拉着云秀的手就往教室外跑。云娜心里想着,今天不知道家里会准备什么好吃的。在她小小的世界里,美食总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记得上次家里炖肉,那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让她馋得直流口水。如今,听到可以回家吃饭,她的脚步都不自觉地加快了。
2
云家小院里,臭槐树的阴凉底下摆着褪色的红漆木桌。那桌子已经有些年头了,漆皮剥落,露出里面粗糙的木纹,仿佛在诉说着它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云祥福用指甲刮掉桌沿开裂的漆皮:“这是你哥们臭头做的,用糖挂的色。”他语气里带着一丝骄傲,仿佛在炫耀自家孩子的本事。
桌上那盘红烧肉泛着油光,旁边摆着拌黄瓜、炒鸡蛋,还有一盆冒着热气的土豆炖豆角。那香味扑鼻而来,云秀和云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云秀看着这丰盛的饭菜,心里满是感动。她知道,在这个贫穷的小山村,能吃上这样一顿丰盛的饭菜是多么不容易。这一定是家里特意为她准备的,因为她今天要回家吃饭,而且父亲还这么和蔼地叫她。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常常是粗茶淡饭。如今,虽然生活依然不易,但家人之间的关爱和温暖却让她觉得无比幸福。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报答家人,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家里带来更好的生活。
木板门“吱呀”一响,臭头端着海碗从灶间钻出来,围裙上沾着柴火灰:“云秀,这是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他咧着嘴笑,那笑容憨厚而真诚。碗里的榛蘑吸饱了汤汁,土鸡肉炖得骨肉分离,香味勾得院角的芦花鸡都扑棱着翅膀凑过来。云秀看着这满满一碗的美食,心里充满了温暖。她想起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能吃上一顿肉是多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哥哥臭头亲总是把肉让给她和妹妹吃,自己却默默地吃着青菜。如今,虽然生活依然不易,但家人之间的关爱和温暖却让她觉得无比幸福。她轻轻夹起一块鸡肉,放入口中,那鲜美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让她陶醉其中。
臭头举起倒满酒的粗瓷碗,碗底“劳动光荣”的红字褪成了粉色:“爸,长命百岁。”云秀和云娜站起来,姐妹俩的塑料凉鞋在泥地上踩出浅浅的印子。她们行了个鞠躬礼,辫梢的红头绳和金发卡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长命百岁!”云祥福喉结滚动着咽下酒,皱纹里夹着的汗珠顺着紫红的脸膛滑下来:“好哇好哇。”他摸着下巴上的胡茬,目光扫过儿子结实的臂膀,又停在云秀被粉笔灰染白的指尖上,“你是吃公家饭的文化人了。”
云秀听到这句话,心里既自豪又有些不安。自豪的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不安的是,她知道父亲接下来可能会说出一些让她难以接受的话。她偷偷瞥了父亲一眼,发现父亲的眼神中似乎藏着复杂的情绪,有骄傲,也有担忧。
她轻轻握住父亲的手,柔声说道:“爸,我知道您担心我,但我选择回到家乡教书,是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些孩子。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学到知识,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而且,我也看到了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教育,我相信,我们的家乡会越来越好。”
云祥福听了女儿的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眼中闪烁着泪光。
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吃着美味的饭菜,谈论着家乡的未来。云秀的心中充满了力量,她知道,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而那野姜花的清香,仿佛也在空气中弥漫,象征着希望与美好,在这片土地上绽放。
突然,篱笆墙外传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赵驼子捧着个泛青的葫芦瓢,酒液在瓢里晃出细碎的波纹:“这是俺用后山野葡萄造的酒,祝老寿星云祥福长命百岁。”他驼背上的补丁被汗水浸成深蓝色,脚上的胶鞋还沾着菜地的泥。云祥福笑着接过瓢,酒香混着山葡萄的酸涩味在空气里漫开:“坐下坐下,一块儿喝。”赵驼子摇着蒲扇似的大手:“不了不了,你让儿女祝你的寿。”他转身时,裤腿扫过篱笆上的牵牛花,紫红的花瓣扑簌簌落了一地。云秀看着这一幕,心里不禁感慨,村里的乡亲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彼此之间却充满了温暖和关爱。赵驼子虽然生活不易,但还是愿意为云祥福送上自己酿的酒,这份情谊让云秀觉得十分珍贵。
臭头举起倒满酒的粗瓷碗,碗底“劳动光荣”的红字褪成了粉色:“爸,长命百岁。”云秀和云娜站起来,姐妹俩的塑料凉鞋在泥地上踩出浅浅的印子。她们行了个鞠躬礼,辫梢的红头绳和金发卡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长命百岁!”云祥福喉结滚动着咽下酒,皱纹里夹着的汗珠顺着紫红的脸膛滑下来:“好哇好哇。”他摸着下巴上的胡茬,目光扫过儿子结实的臂膀,又停在云秀被粉笔灰染白的指尖上,“你是吃公家饭的文化人了。”云秀听到这句话,心里既自豪又有些不安。自豪的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不安的是,她知道父亲接下来可能会说出一些让她难以接受的话。她偷偷瞥了父亲一眼,发现父亲的眼神中似乎藏着一些她读不懂的东西。
云祥福的酒意漫上来,眼皮泛着红。他盯着臭头军绿色背心上"农机站"三个褪色红字,突然说:"云秀啊,你年龄也不小了。"饭桌上顿时安静下来,连树上的知了都住了声。
"爸!"云秀的筷子"啪"地搁在碗上,瓷勺撞出清脆的响声。
云祥福从怀里摸出张按着手印的纸,被汗水浸得发皱:"臭头娶赵泼儿,你嫁赵麻杆儿。彩礼我都......"
云秀猛地站起来,板凳在泥地上刮出两道深痕。她拽起妹妹的手腕:"婚姻不是拿苞米换土豆!"云娜的塑料发卡掉在地上,被匆忙的脚步踩进土里。
3
赵驼子沿着村道往家走时,路边的向日葵耷拉着脑袋,仿佛也被这炎热的天气折磨得失去了活力。七月的阳光像熔化的金子般倾泻而下,将大地烤得滚烫。赵驼子驼背上的补丁被汗水浸成深蓝色,脚上的胶鞋还沾着菜地的泥,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他望着远处山坡上那片开凿了一半的石道,云功德校长抡铁锤的身影在热浪里微微晃动。赵驼子心里想着,这路要是修好了,村里人进出就方便多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用再走那崎岖的山路。可这工程实在艰难,云功德校长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命,真不容易。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继续往家走,心里还惦记着家里那几亩菜地,得赶紧回去浇水。
赵胖像颗炮弹似的冲过来,书包带子断了半截,在身后啪嗒啪嗒地甩。那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村道的宁静,赵驼子看着小儿子那焦急的模样,心里不禁有些疑惑,这孩子平日里上学从不这么慌张,今天是怎么了?他停下脚步,等着赵胖靠近。
“还早呢,你急三火四地干啥?”赵驼子拽住儿子汗湿的衣领,粗糙的大手带着老茧,却透着温暖。赵胖喘得像拉风箱,小脸涨得通红:“找云娜上学啊!他左脸颊肿得发亮,活像塞了个山核桃。”赵驼子看着小儿子那肿起的脸颊,心里一阵心疼,赶紧眯起昏花的老眼:“咋整的?让马蜂子蛰了?”向日葵叶子在他头顶投下交错的阴影,仿佛也在为小儿子的遭遇感到担忧。赵驼子心里琢磨着,要是真被马蜂蛰了,得赶紧找点草药敷一敷。
“哪儿啊?”赵胖扯着变声期的公鸭嗓,声音里带着委屈和愤怒,“齐老师打的!要不是云秀老师拦着......”他忽然收声,盯着爸爸青筋暴起的手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赵驼子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怒火,他觉得齐老师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呢?孩子在学校应该是受到保护和教育的,而不是被体罚。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因为一些小事被老师责罚,那种屈辱和痛苦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他只能默默忍受,心里却充满了对老师的怨恨。如今看到自己的小儿子也遭受这样的对待,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赵驼子的旱烟杆“咔”地敲在路边的石头上,那声音像是敲在了赵驼子的心上,让他感到一阵刺痛。烟锅里的火星溅到晒蔫的野草上,腾起一缕白烟。“什么?齐老师打你?”赵驼子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仿佛要质问齐老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赵胖急忙抱住爸爸的胳膊,试图安抚他的情绪:“打就打呗!”他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云秀老师的小妹云娜可厉害了,她说齐老师体罚学生违反《教师法》,把齐老师气得眼镜都歪了!”赵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得意,仿佛在为云娜的勇敢而自豪。赵驼子听了小儿子的话,心里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他想起云娜那小小的身影,却有着大大的勇气,心里不禁对这个小孙女多了几分喜爱。
赵驼子忽然笑起来,露出被烟熏黄的牙:“云娜是好丫头。”他望着远处山坡上开凿了一半的石道,云功德校长抡铁锤的身影在热浪里微微晃动。赵驼子觉得云娜确实是个有胆识、有正义感的好孩子,而她姐姐云秀老师也一定是个好老师,不然也不会拦着齐老师体罚学生。他想起云秀老师平日里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教导,心里不禁对云秀老师充满了敬意。同时,为云秀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而在心里窃喜。他觉得云秀这样的姑娘,善良、有文化,要是能嫁到赵家,那真是赵家的福气。赵驼子想象着云秀和赵麻杆儿结婚后的生活,脸上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容。
4
第二不清晨,涧水河泛着粼粼波光,河岸边的鹅卵石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与昨日的炎热形成鲜明对比。云秀蹲在河滩上,正用炭笔在林松岭的速写本上勾勒远处青山的轮廓。她专注的神情仿佛与这宁静的清晨融为一体。她一边画,一边想着昨天父亲说的那些话,心里充满了不安。父亲要她嫁给赵麻杆儿,可她根本不喜欢他,她有自己的梦想,想一心一意为村里的孩子们带来更好的教育。几十几个孩子围坐成半圆,他们静静地坐着,眼神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云秀老师的敬爱。云秀看着这些孩子,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说服父亲,不能就这样被安排婚姻。
齐老师却独自站在柳树下,手里攥着本卷了边的《诗经》,眼睛不时往这边瞟。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有对云秀教学方式的不认同,也有对孩子们喜爱云秀的无奈。他觉得云秀的教学太过自由,不像他那样严格管教,担心这样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可看到孩子们在云秀的引导下如此投入,他又有些动摇,不知道自己的教学方式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些孩子。
"云老师,山要画得陡些。"林松岭教授弯腰指点时,白衬衫袖口蹭到了云秀的发梢。云秀微微抬头,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好的,林教授。”齐老师突然咳嗽起来,手里的书页"哗啦"响,惊飞了芦苇丛里的野鸭。那野鸭扑棱着翅膀飞向天空,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齐老师看着飞走的野鸭,心里有些烦躁,觉得自己的咳嗽和野鸭的飞走打破了这宁静的氛围。
"注意山脊线的虚实变化..."林松岭话音未落,对岸的芦苇丛剧烈晃动。云功德校长深一脚浅一脚地跑来,解放鞋上沾满泥浆。齐老师一个箭步冲上前,眼镜腿上的胶布都绷开了:"校长!出什么事了?"
"云秀!你爸..."校长的话被一阵刺耳的唢呐声打断。赵麻杆儿从山坡上连滚带爬地冲下来,铜喇叭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他一把推开正要扶云秀的齐老师:"滚边儿去!云秀他爸出事了!"
云秀手里的炭笔"啪"地折断。她身子晃了晃,林松岭连忙扶住她胳膊。赵麻杆儿顿时瞪圆了眼:"城里人别动手动脚!"他粗粝的手掌一把拍开林松岭,转身就要背云秀。齐老师突然插进来:"赵麻杆儿你耍什么流氓!"两人撞在一起,唢呐和《诗经》同时掉进河里。
云秀和云娜的眼泪已经砸在鹅卵石上。姐妹俩往村里跑时,齐老师和赵麻杆儿还在后面推搡。赵麻杆儿骂骂咧咧地捞起湿漉漉的唢呐:"书呆子懂个屁!"齐老师镜片后的眼睛通红:"云秀需要的是文化人,不是你这种..."
转过打谷场,臭头和邻居王老蔫抬着门板跑来。齐老师突然噤了声,他看见云祥福灰白的脸上还沾着香灰——那是去狐仙庙的痕迹。村支书李建国小跑着攥住他垂落的手,赵麻杆儿趁机挤到云秀身边:"秀儿,我背你..."
"用不着!"齐老师拽住云秀另一只胳膊,"我认识县医院的张主任!"两人拉扯间,云秀的衣扣崩开一颗,骨碌碌滚进路边的排水沟。
赵麻杆儿喊:"你个四眼田鸡..."齐老师尖叫:你个文盲!” 。于是,两人扭打在一起,赵麻杆儿的唢呐正戳在齐老师眼镜上。
一行人抬着门板翻过山梁。齐老师捂着裂开的镜片,还在絮絮叨叨:"要是早点送县里...我有同学在..."赵麻杆儿突然回头啐了一口:"马后炮!"
救护车旁,医生说:“晩了,人已断气多时了。” 云秀扑在父亲身上痛哭。臭头捶地对云秀大喊:"都怨你!"时,齐老师突然挤上前:"云秀你别听他的!"赵麻杆儿一把揪住他衣领:"有你啥事?"两人又要动手,被村支书一烟袋锅分开:"闹丧呢?"
林松岭鞠躬时,赵驼子踹了儿子一脚:"愣着干啥?快去扶着云秀!"赵麻杆儿刚迈步,齐老师已经抢先递上手帕。赵麻杆儿气得唢呐往地上一杵,吹出个凄厉的高音。
"外乡人规矩点!"赵驼子骂林松岭时,眼睛却瞪着齐老师。齐老师扶眼镜的手直发抖:"我是本校正式教师..."话没说完就被赵麻杆儿撞了个趔趄。
村支书蹲在路边,看着远处开凿到一多半的山道:"要是有路..."云功德校长拍向路面的手掌渗出血,正好滴在齐老师掉落的《诗经》上,染红了"执子之手"四个字。
山风掠过麦田,把赵麻杆儿的唢呐声、齐老师的抽泣、还有云秀的哭声,都卷进了幽深的山谷里。
林松岭蹲下身来,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方蓝格子手帕。他刚要递给云秀,赵麻杆儿的铜唢呐就横插过来,喇叭口差点戳到林松岭的下巴。
"用不着你假好心!"赵麻杆儿扯着身上皱巴巴的确良衬衫前襟就要给云秀擦泪,汗酸味混着铜锈味扑面而来。云秀别过脸去,发梢扫过林松岭的手帕。
齐老师突然挤进来,眼镜腿上的胶布又开胶了,晃晃悠悠挂在耳朵上:"云老师,喝、喝口水..."话音未落,赵驼子一烟袋锅敲在雪碧罐上,当啷一声响。
"滚犊子!"赵驼子喷着烟油味的唾沫星子,"你们这些教书的一个比一个蔫儿坏!"他驼背上的补丁随着喘气一鼓一鼓的,像只发怒的老虾米。
林松岭的手帕还悬在半空。云功德校长突然咳嗽一声,常年开山凿石的手掌按在赵驼子肩上:"老哥,让孩子尽尽孝。"他手上的老茧刮得赵驼子一个激灵。
"尽孝?"齐老师镜片后的眼睛突然亮了,他猛地扯开的确良短袖口袋,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票据:"我、我认识县医院副院长!现在派车送云叔去省城..."
赵麻杆儿一把抢过票据,唢呐穗子甩出个圆弧:"早干啥去了?"
云秀的哭声突然拔高了。林松岭趁机把手帕塞进她掌心,却被赵麻杆儿揪住西装后摆。进口面料"刺啦"裂开道口子,露出里头"省美术学院"的绣标。
"看见没?"赵驼子烟袋锅指着绣标直哆嗦,"这些城里人,连衣裳都两层面皮!"
"都消停会儿吧。"村支书把旱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烟灰落在那本泡烂的《诗经》上,"没见丫头哭得快背过气去了?"
5
云功德突然一声吆喝:"抬——回——去——喽!"这声调像他平日带领学生喊操似的,尾音在山谷里荡出回响。臭头闷声应了句"诶",肩膀一沉就把门板扛了起来,脖颈上的青筋像盘曲的老树根。
林松岭默默站到门板右后方,把西装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城里人少见的小麦色手臂——这些天跟着云校长开山晒的。村支书李建国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抓起门板前杠:"走!"
赵麻杆儿的唢呐突然又响了,吹的是《纤夫的爱》。赵驼子抡起烟袋锅要打儿子:"你个缺心眼的!"铜烟锅撞在唢呐上,"当"的一声,惊飞了路边槐树上的老鸹。
齐老师挤到门板左侧,眼镜腿不知什么时候用麻绳绑住了,活像戴了副枷锁。他伸手要帮忙抬,被门板晃了个趔趄。"起开!"臭头一膀子把他顶开,"别添乱!"齐老师踉跄着踩进泥坑,崭新的回力鞋顿时糊满粪肥。
"慢着点!"云功德突然喊。门板经过歪脖子柳树时,云祥福的胳膊垂了下来——那手上还缠着开山用的粗线手套,拇指处磨破了,露出结着血痂的皮肉。云秀扑上去把父亲的手贴回胸口,眼泪砸在手套破洞上,洇出深色的圆斑。
赵麻杆儿突然窜到林松岭身边,唢呐嘴往他腰眼一顶:"你算老几?凭啥挨着云秀的爸爸?"林松岭身子一歪,门板顿时倾斜。云功德暴喝:"麻杆儿!"声如炸雷,惊得赵麻杆儿手里的唢呐"咣当"落地。
"都消停!"李建国支书额头上的青筋直跳,"老云哥活着时候最要脸面,你们这是存心让他走不安生!"
路边水沟里,齐老师正捞他的眼镜。赵驼子突然蹲下来,烟袋锅指着沟里的青蛙:"瞧见没?就跟这癞蛤蟆似的,净想吃天鹅肉。"话分明是说给林松岭听的,眼睛却瞟着齐老师。
门板"吱呀"一声过了小石桥。桥下漂着齐老师那本《诗经》,"关关雎鸠"那页正好糊在石墩上。
"停!"云秀突然尖叫。原来赵麻杆儿偷偷往门板上别了朵野芍药,红得扎眼。她一把扯下花揉烂……
臭头抬着门板,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汗珠子顺着脖颈往下淌。赵驼子眯着眼,心里盘算着:云秀这丫头现在眼里只有那个城里来的林松岭,换亲的事怕是黄了。可臭头……臭头老实,要是能娶了自家闺女赵泼儿,好歹也算攀上了云家。
"泼儿那丫头……"赵驼子心里一沉,想起闺女日渐鼓起的肚子,如果不赶紧抛盘,可就丢人现眼了,赵驼子把牙根咬得咯吱响。
"呸!"赵驼子往桥下啐了一口,烟袋锅重重敲在石墩上,"城里人没一个好东西!"
齐老师正弯腰在沟里摸眼镜,听见这话,手一抖,眼镜又滑进泥水里。他抬头,正对上赵驼子阴恻恻的眼神,吓得一哆嗦,赶紧低头继续摸索。
赵麻杆儿捡起摔歪了的唢呐,凑到臭头身边,压低声音:"臭头哥,我妹泼儿……你还要不?"
臭头脚步一顿,门板猛地晃了一下。云功德皱眉:"稳当点!"
臭头闷声"嗯"了一下,没接话。"麻杆儿!"赵驼子突然暴喝一声,"胡咧咧啥呢!"
臭头低着头,脖颈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半晌,他才闷闷地说:"泼儿……是个好姑娘。"
赵驼子眼睛一亮,烟袋锅也不磕了,凑过来:"臭头啊,化悲痛为力量,你爸的后事,赵叔来办!”臭头没吭声,只是肩膀绷得更紧了。
云秀走在最前面,听见身后的嘀咕,回头看了一眼。她瞧见赵驼子那张皱巴巴的老脸上堆着笑,哥哥臭头却像扛着一座山似的,脚步越来越沉。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