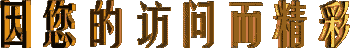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连载十二
两扇门
作者:尹玉峰(北京)
烟灰落进卦象,野姜花
数着霜;哪曾想,霜刃
劈开了两扇门
唢呐衔着黄昏
把春天吹成锁;而山风绕过
门槛,悄悄的偷走一瓣倔强
1
六月的东北山乡涧水河村,傍晚的风里还带着白天的燥热。云祥福蹲在自家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中忽明忽暗。他眯着眼睛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心里盘算着今天去邻村找大妹的事。山风掠过他布满皱纹的脸,带来一丝凉意,却无法平息他内心的焦躁。这些天来,他夜不能寐,脑海中反复盘旋着云秀的未来和赵驼子提出的换亲提议。作为一家之主,他肩负着沉重的责任,既要维持家庭生计,又要为儿女筹谋前程。每想到这些,他胸口便如压巨石,喘不过气来。
"大妹这个死脑筋,"云祥福吐出一口浓烟,烟圈在空气中扭曲变形,"狐仙娘娘都显灵了,她偏不信。"
他想起大妹那张皱得像核桃皮似的脸,听到他要让云秀嫁给赵麻杆儿时那副表情。"哥,你这是乱点鸳鸯谱!"大妹当时就拍着炕沿喊起来,"云秀是大学生,赵麻杆儿连初中都没念完,就会吹个破唢呐,这不是糟践孩子吗?"
云祥福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掐灭烟头,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院子里,臭头正撅着屁股劈柴,汗珠子顺着他的光头往下淌,在夕阳下闪闪发亮。臭头是他唯一的儿子,虽然心智有些迟钝,但勤快老实,从不抱怨。云祥福看着儿子,心中五味杂陈。臭头娶了媳妇,新婚不久,就跟人跑路了,这成了云祥福心里的一块心病。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坐在炕头,便会想起这件事,自责自己没能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想到赵泼儿那水灵灵的模样和丰满的身段,云祥福心里一阵发热——这丫头虽然嘴巴厉害点,但能生养,最重要的是赵驼子家愿意换亲。换亲若能成功,不仅能解决臭头的婚姻问题,还能为云秀找个归宿,一举两得。
厨房里飘出饺子的香气。云祥福掀开锅盖,白胖胖的饺子在滚水里翻腾,像一群欢快的小鱼。他捞了一碗,又盛了碗高粱米水饭,摆上茄子拌土豆、大拉皮和小葱蘸大酱,招呼臭头过来吃饭。这些简单的食物,是云祥福所能给予的最好款待。他望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尽管生活艰难,但一家人能围坐在一起吃饭,便是最大的幸福。
"臭头,别劈了,洗洗手吃饭。"云祥福喊道,声音里带着少有的温和。
臭头抬起头,憨厚地笑了笑:"爸,我再劈两根,明天赵泼儿来咱家,得多烧点水。"
云祥福嘴角抽动了一下,露出一个近乎慈祥的表情。臭头娶了媳妇,新婚不久,就跟人跑路了,在云祥福心里是块心病。想到赵泼儿那水灵灵的模样和丰满的身段,云祥福心里一阵发热——这丫头虽然嘴巴厉害点,但能生养,最重要的是赵驼子家愿意换亲。云祥福深知,在这个偏远山村,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联盟。赵驼子家的提议,给了他一丝希望,仿佛黑暗中的微光。
爷俩刚坐下,院门"吱呀"一声开了。赵泼儿穿着一件城里流行的碎花连衣裙,扭着腰走了进来,裙摆下露出半截白生生的小腿。她的到来,让云祥福心中既期待又紧张。期待的是,赵驼子家的换亲提议或许能成;紧张的是,赵泼儿性格直率,不知会带来什么消息。
"吃啥呢?这么香!"赵泼儿的声音又尖又亮,像只刚下完蛋的母鸡。
臭头一脑袋热汗转过头,嘿嘿一笑:"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这是鲅鱼馅儿的饺子,香啊!还有高粱米水饭,茄子拌土豆、大拉皮、小葱蘸大酱!"
云祥福舒心地望着迎面而来的赵泼儿,又满意地瞅了臭头一眼,笑微微地说:"泼儿,吃点吧!"
赵泼儿用手煽了煽鼻子,夸张地皱起眉头:"这酱咋臭乎乎的,难怪一家大酱一个味,臭头下的酱吧?"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臭头下意识地在酱碗里闻了又闻,嘴里嘟囔着:"不臭啊..."
云祥福和蔼地说:"泼儿,过来凑合吃一口吧。"
赵泼儿摆摆手:"云伯伯,我来是找你说点事儿。"
云祥福放下筷子:"好哇好哇。"
赵泼儿瞅瞅臭头,臭头正憨笑着呆呆地望着她。她撇撇嘴:"笑什么,我要说的不见得是好事儿啊!"
云祥福眯起眼睛,在赵泼儿的话音里听出了什么,连忙招呼她进屋。臭头想跟进去,被赵泼儿一个眼神钉在了原地。云祥福的心跳加速,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他强装镇定,但手却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2
屋子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光。赵泼儿熟门熟路地坐在炕沿上,两条腿不安分地晃荡着。云祥福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目光如炬,试图从她的表情中读出真相。
“云伯伯,云秀和云娜呢?"
谁知道啦,可能又去村小学了,唉,别管她们。”
"那可是你的女儿呀?怎么漠不关心的样子?"
"怎么不关心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容易吗?"云祥福顿时感到很辛酸。他想起自己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艰辛岁月,从云秀出生到上大学,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供她读书,耗尽了他的积蓄和精力,但从未后悔。云秀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未来的希望。
"云伯伯,"赵泼儿忽然压低声音,"我哥让我来问问,那事儿您考虑得咋样了?"
云祥福搓了搓手:"泼儿啊,我今儿去问了狐仙娘娘,卦象上说这事儿能成。就是云秀那丫头..."
赵泼儿突然咯咯笑起来,笑声像一串玻璃珠子掉在地上:"云伯伯,您还不知道吧?您家云秀在省城可出名了!"
云祥福一愣:"啥意思?"
赵泼儿凑近了些,身上廉价的香水味熏得云祥福直皱眉:"我听人说,云秀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光着屁股让人画呢!整个美院没有不知道她的!"
云祥福的脸"唰"地白了,手里的烟袋锅"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来,又跌坐回椅子上,胸口剧烈起伏着。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击中了他最脆弱的地方。云秀是他倾注心血培养的女儿,如今却传出这样的丑闻,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和愤怒。
"你...你说啥?"
赵泼儿装作惊讶的样子:"哎呀,云伯伯您不知道啊?我还以为..."她故意捂住嘴,"对不起,我不该多嘴的。"
云祥福的双手开始发抖,眼前浮现出云秀她妈年轻时的样子——那个总是偷偷给凿石开道的云功德送饭的女人,后来离家出走了,一去不回返,让他心里很不愉快。现在她的女儿,竟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云祥福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云秀小时候的乖巧懂事,她考上大学时的喜悦,以及自己省吃俭用供她读书的情景。这一切,仿佛在一瞬间被摧毁。
"泼儿,"云祥福的声音嘶哑得可怕,"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赵泼儿眼珠一转:"哎呀,村里差不多都知道了。我哥说,要不是看在两家要结亲的份上,他才不会..."
话没说完,云祥福已经冲出了屋子。院子里,臭头还傻乎乎地坐在饭桌前,见父亲出来,忙站起身:"爸,咋..."
"滚开!"云祥福一把推开儿子,踉踉跄跄地走到院中央,突然仰天大吼:"作孽啊!我云家造了什么孽啊!"
臭头吓傻了,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赵泼儿笑嘻嘻地从屋里走出来,经过臭头身边时,故意用肩膀蹭了他一下:"别跟着我,小心又掉陷阱里。"说完,她扭着腰肢快步走出院子,向山谷方向跑去,裙摆划出一道轻快的弧线,仿佛一只急于逃离的蝴蝶。
3
云祥福的吼声在山谷间回荡,惊起几只归巢的鸟雀。他瘫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双手死死攥住衣襟,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些关于云秀的流言像毒蛇般缠绕着他的心脏——光着身子让人画?这比当年云秀她妈私奔更让他感到耻辱。他想起自己辛苦供她上大学,盼着她能光宗耀祖,却没想到换来这样的丑闻。云祥福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深爱着女儿,希望她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传统的观念和村里的舆论让他感到无法承受。他觉得自己一生的努力和牺牲,都被云秀的行为所辜负。
"爸,您没事吧?"臭头怯生生地靠近,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饺子。
"滚!"云祥福猛地甩开儿子,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们云家都是废物!"他抓起地上的烟袋锅,狠狠砸向院墙,火星四溅。臭头缩着脖子退到柴堆旁,不敢再吭声。云祥福的愤怒不仅针对云秀,也针对自己。他感到自己作为父亲的失败,未能教育好子女,未能维护家族荣誉。这种自责和愤怒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崩溃。
厨房里,饺子在冷水中渐渐泡胀,高粱米水饭凝成硬块。云祥福站起身,踉跄着走向村口的老槐树。树下的石桌旁,几个老人正摇着蒲扇乘凉,见他脸色铁青,纷纷噤声。云祥福的步伐沉重,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需要找人倾诉,需要寻求理解和支持,哪怕只是暂时的安慰。
"祥福叔,咋了?"村邻张德贵递过一杯凉茶。
云祥福接过茶碗,手抖得茶水洒了一身:"老张,您知道云秀在省城干的那些事吗?"
张德贵皱起眉头:"啥事?"
"她...她让人画光身子!"云祥福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云家祖坟冒青烟供她上大学,她就这么报答?"
老人们面面相觑。张德贵捻着胡子沉吟片刻:"这事得问清楚。城里人搞艺术,兴许是画人体模特?"
"模特?"云祥福瞪大眼睛,"那和光屁股有啥区别?"
远处传来赵泼儿尖细的笑声,她正和几个姑娘在河边洗衣服。云祥福的视线死死钉在她身上,仿佛她就是传播谣言的源头。他突然想起赵驼子昨天的话:"祥福哥,换亲的事得抓紧,云秀名声坏了,我家泼儿可不能吃亏。"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剑,刺入云祥福的心头。他意识到,换亲的提议或许不再可行,云秀的丑闻已经影响了整个计划。云祥福感到自己陷入了绝境,前路一片黑暗。
夜幕完全降临,山风卷起地上的落叶。云祥福转身往家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经过臭头时,瞥见儿子正偷偷捡起地上的饺子往嘴里塞,眼泪突然夺眶而出——这个傻儿子,连媳妇都留不住,现在女儿又出了这种事,云家真要绝后了吗?云祥福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他觉得自己一生的努力和牺牲,都化为泡影。家族的未来,似乎已经岌岌可危。
院门"吱呀"一声自动关上,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云祥福摸黑走进里屋,从炕席下摸出皱巴巴的汇款单——那是云秀每月寄来的生活费。他盯着单子上"美术学院"四个字,突然抓起剪刀,将汇款单撕得粉碎。这一举动,象征着他与云秀之间联系的断裂,也代表了他对女儿行为的彻底否定。云祥福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局面,也不知道云家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窗外,野姜花的香气混着赵泼儿留下的廉价香水味,在闷热的夏夜里发酵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苦涩。
4
臭头立在院子里怔了又怔,晩风裹挟着枯叶掠过他的脸颊,像无数细小的爪子挠着皮肤。他本就有些迟钝的大脑此刻更是乱成一团麻,父亲那突如其来的暴怒和绝望的哭嚎,如同晴天霹雳,将他本就摇摇欲坠的世界震得七零八落。他呆呆地望着那扇透着微弱灯光的窗户,那灯光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寂,仿佛是被整个世界遗弃的角落。屋子里传来的压抑哭声,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进他心口最柔软的地方,让他一阵阵揪心。他慌忙跑进屋,脚步踉跄,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家里出大事了,到底咋的了?
进屋后,他看见父亲正捶胸顿足,老泪纵横。云祥福那平日里还算挺拔的身躯此刻佝偻着,像一棵被狂风摧残的老树。他的双手疯狂地捶打着胸口,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和耻辱都捶打出来,每一次捶击都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泪水顺着他那沟壑纵横的脸颊肆意流淌,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绝望的光芒。臭头急得直搓手,他本就不太灵光的脑子此刻更是转不过弯来,只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原地打转,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咋的了,咋的了?爹,你咋的了?”
云祥福抬起泪眼,那眼神里满是绝望,如同一潭死水,看不到一丝生机。声音里也满是绝望:“云秀在省城念书的时候光着屁股让人画……叫我的老脸往哪搁啊?都说入伏头天爽,伏伏爽,可我的心咋这么不爽呢?”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残忍地割着臭头的心。他虽脑子不太灵光,但也明白这不是小事。父亲那因愤怒和痛苦而扭曲的脸,让他想起小时候被父亲打骂时的恐惧。他笨拙地拍着父亲的后背,动作生硬而无力,就像在安抚一只受伤却依然凶猛的老兽:“爸,别急,等秀儿回来问问……”
“问个屁!”云祥福突然暴怒,那暴怒如同火山喷发,瞬间将他本就脆弱的理智彻底摧毁。他一把掀翻了炕桌,桌上的碗筷、杂物“哗啦”一声散落一地,在寂静的屋子里发出刺耳的声响。那声音仿佛在嘲笑他的无能,又像是在宣告一场家庭灾难的降临。“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跟她妈一个德行!我非把她嫁给赵麻杆儿不可,看她还怎么丢人现眼!”赵麻杆儿是村里有名的无赖,游手好闲,还爱占小便宜,父亲要把妹妹嫁给这样的人,这简直就像要把一朵娇艳的花扔进臭水沟。臭头被父亲的怒吼吓得缩了缩脖子,那怒吼如同雷霆,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但听到要把妹妹嫁给赵麻杆儿,他还是忍不住小声说:“可是秀儿不喜欢麻杆儿……”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就像风中摇曳的一根细草,随时可能被吹断。
“轮不到她喜欢不喜欢!”云祥福红着眼睛吼道,那吼声如同野兽的咆哮,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我养她这么大,她就这么报答我?让她嫁谁就嫁谁!”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对女儿的失望和愤怒,仿佛云秀的每一个行为都在挑战他的权威,都在践踏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夜色渐浓,山村的夜晚格外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打破宁静。那狗吠声像是从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传来,更衬托出这间屋子的压抑和沉闷。云祥福坐在黑暗的屋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那烟雾如同一条条灰色的毒蛇,缠绕着他的思绪,将他拉回到十年前的那个下午。
他去供销社买肥皂,刚走到村口老槐树下,就看见妻子拎着个竹编食盒往山上走,脚步轻快得像个小姑娘。那轻快的脚步如同一串欢快的音符,在寂静的山村小路上跳跃。云祥福的心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烦躁,就像有一群蚂蚁在心头爬行。鬼使神差地,他没出声,悄悄跟了上去。山路蜿蜒,如同一条曲折的蛇,在山间缓缓爬行。妻子在一处新开的石阶前停下。那里站着个赤膊汉子,古铜色的背上泛着油光,肌肉随着凿石的动作起伏——是村小学校长云功德。云祥福躲在树后,拳头攥得发疼,那疼痛从掌心蔓延到全身,仿佛要将他的身体撕裂。“云弟弟,吃饭吧。”妻子的声音温柔得陌生,就像一阵轻柔的春风,吹拂过他的心田,却让他感到一阵刺痛。那温柔里有什么东西烧得他心口发烫——是崇拜,是怜惜,是他这个丈夫从未得到过的温柔。那温柔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割开了他心中那层薄薄的骄傲,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卑微和无能。
当天晚上,云祥福把烟袋锅往炕沿上重重一磕:“今天给云功德送饭去了?”那“磕”的一声,如同一声惊雷,在寂静的屋子里炸响。妻子正在纳鞋底的手一抖,针尖扎进指腹,渗出一粒血珠:“你……你怎么知道?”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慌,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全村都知道了!”云祥福突然暴起,那暴怒如同火山喷发,瞬间将他淹没。烟袋锅带着风声砸在妻子额头上,“贱人!我云祥福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去勾引云功德!”他的话语充满了侮辱和指责,仿佛妻子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妻子捂着额头,血从指缝间渗出,滴在炕席上:“我没有……云弟弟给全村修路,大家轮流送饭……”她的声音微弱而颤抖,就像风中摇曳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云弟弟?叫得真亲热!”云祥福一把掀翻炕桌,针线筐滚落一地,“明天开始不许出门,再让我看见你往山上跑,打断你的腿!”他的威胁如同冰冷的刀锋,直刺妻子的心脏。
十五岁的臭头被惊醒,那惊醒如同一场噩梦的开始。十三岁的云秀和二岁的云娜揉着眼睛看见母亲满脸是血,吓得小脸煞白。那满面的鲜血如同一朵妖艳而恐怖的花,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云祥福一把拎起女儿云秀:“看什么看!长大也是个不要脸的货!”他的话语充满了对女儿的诅咒和侮辱,仿佛女儿的未来已经被他提前判定了死刑。那夜之后,云祥福的脾气越来越暴。他禁止妻子出门,看见妻子沉默的脸,就觉得她在心里笑话自己。那沉默的脸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的无能和不自信,让他感到无比愤怒和羞愧。“笑啊!怎么不笑了?”云祥福常掐着妻子的下巴逼问,那逼问如同一种酷刑,让妻子感到窒息。“在云功德面前不是笑得很开心吗?”他的话语充满了嫉妒和怨恨,仿佛妻子对云功德的一丝笑容都是对他的背叛。
妻子渐渐变得像具行尸走肉,只有送云秀去村小学时,才会在云功德新修的石阶上停留片刻。这些石阶已经连到半山腰,每块石头都打磨得平整光滑。那平整光滑的石阶如同一道希望的桥梁,连接着山里与山外的世界,也连接着妻子内心深处那一点点尚未熄灭的温暖。深秋的某个清晨,云祥福打脾输了整夜的钱。回家时看见灶台冷清,妻子不在,连孩子的书包都没准备。那冷清的灶台如同一座坟墓,埋葬着家庭的温暖和希望。他抄起擀面杖冲到山上,果然看见妻子站在云功德身边,两人正对着新凿的石壁比划什么。那场景如同一幅刺眼的画面,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破鞋!”云祥福的擀面杖狠狠砸在云功德肩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那撞击声如同一声丧钟,宣告着家庭和谐的终结。令他意外的是,一向健壮的云功德没有还手,反而护住他妻子:“祥福哥,你误会了,嫂子是在帮我看新路的图纸……”那护住的动作如同一道屏障,试图阻挡云祥福的怒火,却只是让怒火更加猛烈。“图纸?她个文盲看什么图纸!”云祥福抡起擀面杖又要打,却被闻声赶来的村民拦住。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像毒虫钻进云祥福耳朵:“自己赌钱不管家,还有脸打人……”那窃窃私语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他的自尊。“功德多好的人,天天起早贪黑……”那赞美的话语让他感到无比嫉妒和愤怒。“祥福家的真可怜……”那怜悯的话语让他感到无比羞愧和恼火。
最刺痛他的是妻子的眼神——那种看脏东西似的厌恶。那厌恶的眼神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割开了他心中最后一丝尊严。当天夜里,云祥福把妻子绑在院里的枣树上,用柳条抽得她后背没一块好肉。那抽打的动作如同一种疯狂的惩罚,试图让妻子屈服,却只是让家庭更加破碎。臭头扑上来咬他手腕,被他甩出去老远。那扑咬的动作是臭头对母亲本能的保护,却被父亲轻易地击碎。云秀哭喊着“别打妈妈”,那哭喊声如同一首悲歌,在寂静的夜晚回荡。云娜坐在地上哇哇大哭,那哭声如同一把锤子,敲打着云祥福那已经麻木的心。云祥福把妻子关进了仓房。第二天一早,云祥福被孩子的哭声惊醒。院里枣树下只剩一截断绳,妻子常穿的蓝布衫挂在树杈上,像面投降的旗。那蓝布衫如同一面白旗,宣告着妻子在这场家庭战争中的失败和逃离。
他找遍全村,所有人都说没看见。最后是放羊的张老汉不忍心,告诉他天没亮时看见他妻子顺着山坡走远了。“她说啥没有?”云祥福揪着张老汉的衣领问。那揪衣领的动作充满了愤怒和绝望,仿佛张老汉是妻子逃离的帮凶。“就说……让你好好待孩子。”那简单的话语如同一颗种子,在云祥福心中埋下了一丝悔恨。云祥福在镇上汽车站守了三天,没等到人。回家后发现连米缸都见了底,原来妻子走前把粮食都分给了帮忙照看孩子的邻居。那空了的米缸如同一张饥饿的大嘴,吞噬着家庭的温暖和希望。最让他窝火的是,全村人都知道他老婆跑了,却没一个人告诉他。那隐瞒如同一种背叛,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后来云功德来过一次,带着一袋白面。云祥福抄起铁锹就拍,那铁锹的拍打动作充满了愤怒和敌意,仿佛云功德是妻子逃离的罪魁祸首。云功德放下粮食就跑,在院门口喊:“祥福哥,等路修通了,到时候去镇上……”那喊声如同一句承诺,却无法平息云祥福心中的怒火。
母亲被关在仓房时,云秀偷偷从门缝塞进去的玉米饼,被父亲发现后直接扔进了猪圈。那被扔进猪圈的玉米饼如同她的希望,被父亲无情地践踏。
“哥……”云秀突然抓住臭头的袖口,眼泪砸在补丁摞补丁的布面上,“你劝劝爹……”那眼泪如同晶莹的珍珠,滚落在布面上,滚落在臭头的心上。
臭头的手在发抖。他想起云功德悄悄塞给他两个烤红薯,说“你爸赌钱输了,别饿着肚子”。当时他躲在柴垛后啃红薯,烫得直吸气,却不敢让父亲看见。那烤红薯的温暖如同一丝微光,在寒冷的冬天给予他一丝慰藉。
5
回忆中,云祥福的瞳孔猛地收缩。妻子离家时的断绳、蓝布衫、那句“好好待孩子”的嘱托,突然像潮水般涌来。那潮水般的回忆如同一场风暴,席卷着他的内心。那时他踉跄着扑向炕柜,从最底层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云秀画的素描,画的是母亲在灶台前揉面的背影,右下角写着“给爸看,这是妈妈”。那素描如同一幅珍贵的画卷,承载着云秀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期待。
“你妈……”云祥福的吼声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呜咽。那呜咽如同一首悲歌,唱响着他心中的悔恨和痛苦。他抓起画纸就要撕,却看见云秀母亲衣襟上别着朵褪色的布花,那是云秀七岁时用碎布头缝的。那褪色的布花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而温暖的光芒。
回忆到这里,云祥福被烟呛得剧烈咳嗽。他抹了把脸,发现掌心湿漉漉的。窗外,月亮已经爬上山头,照得院子里一片惨白。
"都是报应..."他喃喃自语,突然狠狠掐灭烟头,"云秀这个赔钱货,必须尽快嫁出去!"
仓房里传来窸窣声,是臭头在偷偷藏明天要给赵泼儿的煮鸡蛋。云祥福眯起眼睛——这次,他绝不会让任何人破坏他的计划。
与此同时,赵泼儿已经跑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赵麻杆儿正倚着树干等她,手里把玩着那把铜唢呐。
"咋样?"赵麻杆儿急切地问。
赵泼儿得意地扬起下巴:"放心吧哥,我添油加醋一说,老云头差点没气死过去!这下他不把云秀嫁给你都不行了!"
赵麻杆儿瘦长的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好妹子,等哥娶了云秀,一定好好谢你!"
"得了吧,"赵泼儿撇撇嘴,"我就是看不惯云秀那副清高样。大学生了不起啊?还不是得回来嫁人!"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阴狠,"再说了,臭头那个傻子配得上我吗?要不是为了..."
赵麻杆儿赶紧捂住妹妹的嘴:"小点声!这事儿成了,咱家就有后了,咱爸也高兴。"
夜风吹过槐树,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窃窃私语着什么秘密。远处,云家的灯火依然亮着,像一团不肯熄灭的怒火。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