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引 子
地里的
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穿透了这个山沟沟:过空了!透水了!
人们顺着喊声往八亩地煤窑涌去,见井口上人头攒动,四个人绞的大辘轳不停地转动着。刚上来一钩,搭钩工用抓钩搭上一把就捋了过来,油筐里的人连滚带爬地窜上了井沿边,嘶声裂气喊道:“快放钩快放呀,底下还有人嗹!”这大筐吱溜就又放了下去,但听“嘭”地一声,筐子就搁在井筒半中腰了,围在井口边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
就听井筒中发出没人声的呼喊:“起钩起钩,还有活人嗹!”吓得辘轳工们慌忙绞动把油筐拽上来,就看到两个湿漉漉泥猴般的汉子叉着双腿擎着油筐的稳绳不待到井口就伸张手臂,恨不能一步就迈到井边上,只听一老者厉声喝道:“稳住,稳住!辘轳停了再伸爪子,恁不要命了。”大伙儿这才沉住气,待停稳了,人被採住拖拉了上来。
前一钩上来的那三个矿工在人慌马乱中早跑得没影了,这俩行子一爬上来也想跑,被众人圈住好歹算是摁住了一个,另一个玩命地挣开他窜了。待再捹着辘轳把手往井里瞅,那黑乎乎的井水已漫到人能看得见了。楞了一大会儿,确见水面不再往上泛泡泡了,大伙儿才把摁住的这伙计架到井口一侧的卧棚里,问了井下透水的情形。
这人儿还在张着大嘴喘气呢。有人忙把一杯热茶递到嘴边上,咽下这口他抹抹嘴,定心了一下,又哇地一声嚎叫着满地打滚,还想跑,几个人扑上都压不住啊。
只待嚎够了又让他垫上了点吃的,肚子里有了食,这才惺醒了过来。
他逶着身子,塌眯着眼唠道:“俺下井时都还好好的。我当筐头,这来回才拉了三趟,正在炭窝里装着炭呢,就听见右侧壁子上吱吱地水老鼠叫。镢头说:坏了,要过空!得赶急跑!我一把拽起电石灯含在嘴上,转弯身子就往外爬。镢头连灯都未及拿,就紧跟我脚后头往外窜,没跑上几步,轰地一声那水就斜溜着冲了出来,呲着护煤柱脚上的炭块蹦得满洞子是。嗨!这老天有眼哪,俺俩若迎着面呲上,尸骨怕都找不着了。
俺俩一路连跑带喊逃命加上那水呲呲地叫着,邻近炭窝里伙计也挤在俺那腚后头淌着水往外跑,当窜到井口大门上见到装满炭的油筐要起钩,急了眼也顾不上啰啰了,就猛憋了一口气把载筐攉到一侧,摘下挂钩来就拤在一边的空筐上,招呼着跟前的俩伙计和俺那镢头跳进筐中,俺扩着嗓子喊了号,仨人就升上井嗹。这水势来得忒快嗹,眼看着井口大门就淹没了,没别法俺只好抓着稳绳跐着井壁往上爬,拽着拽着看到油筐又放下来搁在水面上,我就一边抓着稳绳另一手使劲把住筐边跐着井壁硬翻到筐里。一开始这两根稳绳上还挂拉着五六个人呢,可翻到筐里的就俺俩人,还有一个冒了冒头晃了晃就不见了,估摸着不是呛了水就是被溜绳底下挂着的人拽下去了。水还是不住地往上泛,没见到再有露头的了。这不才喊呼还有活人呐,俺俩算是拣了这条小命!唉!忒惨忒吓人嗹,没法说呀!”
此时众人也没敢掺言的,就听老者说:年小的,你顺着稳绳往上爬时,井口大门上有多少人?
约摸着有八九个人吧。
上山的那伙人见到没?
没看见。
这老者听到这里便双手合十,扑地跪倒:黑山爷爷在上,万望保佑俺上山的这些人吧。如有生还,俺众等上大供拜谢!
陆续有下井的家属赶到了井上,有的就直着身子硬往井筒里竖,场面眼看着要失控。没办法,井口上掌作的只好命人用斧头截断井绳和稳绳撤掉辘轳架子后用木板子棚住井口,架上石块压住堆上土完活。
这是个份子井,由三家人凑钱合伙办的。一听说出了事,掌柜
那时就兴这么弄,谁摊上算谁倒霉,就是这样的社会。
一
自西河大庄往东,沿着坡地,黄崖延到龙湾峪往北这一搭东西十几里宽、南北几十里长的地面上那是野草丛生,荒无人烟的。
这埝儿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土狼貔狐,獾兔横行。那遍地的野酸枣荆棵头、黄背草葛条根等肆意生长,绵绵密密,此起彼伏又生生不息。 出没在这里的貔狐,种类各异,数量繁多。尤其是号称话貔子的火红狐狸,那是道业高、仙光灵。听说能通人语、化人形。幻化多端而善记恩仇,屡屡在地面上惹祸端、闹事体弄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奇闻异事,官府对此亦无可奈何,见怪不怪。因而明清两朝的《淄川县志》上均封称此处地面曰“仙人乡”。
闲言少叙,且说这一夜三更刚过,鲁家庄里的一户人家推开了栅门,一老俩小背着炭衣裳手提电石灯走出院外,往西一路穿过五起磨趟过西沟河攀上陡峭的黄崖头,正走着呢,就隐约看到一只体形硕大的貔狐趴在路边高处的堰头上,待见这爷仨走近,它就扬起前爪豁了点土,口中好似念念有词,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
这当爹的约摸着是听出了点意思:像是在说“不去、甭去”。
这人就想,这貔子闹的是哪一出?
因井口上点卯时辰卡得紧,也就懒得在这和貔子掰扯,就朝着它拱了拱手,带着俩孩子急匆匆地赶路了。
但见这貔子抻腰往前拱了拱,用前瓜豁起土来扬到他爷们的脊梁后背上,还是不住声不住气地吼着:甭去,甭去!眼看没人搭理它,也就一步三回头地漫进了黑暗中。
这男人走着走着也犯琢磨:今儿这貔子是咋着嗹?
他听人说过:那些修炼得道的老貔仙会学人语行人事,有时就趁天傍黑或刚噜苏明时趴狗在路旁的地头堰边上戴着个破苇苙头守候着。见上行人就搭上腔嗹:“你看我像啥?”若遇到心肠好之人,明知是个貔子,也随口答应:“你像个人!”
貔子就恣悠悠屁颠屁颠地跑了,不几日,这人脚旁边不是一只野兔子就是别的甚么东东。甭说,是貔子来报恩了。
有时也会碰到那不大着调的人儿,当貔狐问到它像啥时,这边就随口而出:“你个貔子你还装啥蒜?滚开别碍事!”这貔子便垂头丧气地开颠了,倒也无事,它再也不稀找你了。
更有甚者,这貔子乐颠颠地跑过来求吉言呢,你可倒好,非得说这貔子像根屌,它这可就恼了。囔囔道:“恁还说俺像根屌来,俺苦苦修炼这么多年容易吗?你等着,俺和你没完!”说着就用前爪撅着土给你扬了过来。如用石头块打它,它楞能把石块给反着挡回来。说不定过两天还要招惹上点小灾让你吃点亏呢!
久了,但凡遇上貔狐讨吉言时,一般都会顺着它说好话或干脆躲开它,生怕惹了貔狐招晦气。
今早这一出,这爹琢磨了一路也未理出头绪:貔狐现身都是求人借话语长功力,今回可蹊跷了,但思来想去还是弄不透是啥意思。
爷仨急呼呼地赶到井上,下窑后就到了上山的炭窝里。爹是镢头,大儿是筐头拉煤,小的身小力薄,当水伕。
这水伕活儿就是把炭窝里渗出的铺水引到一个低凹的小水窝中,用兽皮做成的水袋子把水刮满提起来送出炭窝外头的老陈空里,以使炭窝里干爽好干活。那时的小井都这样做。
这孩子正捧着盛水的袋子往陈空里走着呢,猛听下山洞里轰地一声响,还没明白是咋回事呢,就听爹从炭窝里窜了出来,朝陈空边吼了一声:“快跟爹跑!”边跑边喊:“过空了快跑快跑,往井口跑!”小儿听见爹吆喝,含着电石灯撂下水袋就往外跑。
跑着跑着爹也没见着,哥也没找着,水就可着洞子漫了上来。
还是个孩子啊!哪见过这阵式?随着水位上涨他就往高处退。退着退着水缓缓稳住了,他吓傻了,木呆呆地狗踮在那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电石灯早就灭了,漆黑漆黑地,肚子里饿得吱吱叫,渐渐地迷糊了过去。
恍惚中,就觉得一位浑身乌黑的老者飘忽而至,待到近前时,觉得他的胡子眉毛雪白长相威严,轻声说道:“孩儿啊,这井底下可就剩下你这个活的了。”
孩子忙问:“俺爹和俺哥呢?”
“已向西天朝佛去了”,老者道。
孩儿一听嚎淘大哭。哭过后老者缓缓说道:“你这小命不该绝呵,在世间还要经历一些事儿。命大呀!”
这小儿支起耳朵使劲听,又听说道:“命里你这一劫脱不过去,经这一遭或许好处多多。你命孤,兄弟爷们不沾连,独身一人闯江湖。不近女色莫婚配,晚年返乡心坦然。孩儿啊,这话你可记住了。”
孩儿伏地头如捣蒜,连连说着:“记住了,记住了!”
老者把他扶起来又道:“若得脱身,千万不可回家,切记。要一路往北奔,越远越好。”
嘱咐完后,老翁引着孩儿爬到上山顶转弯处找到了一个陈炭窝洞,往里一拐转到一个下山洞,又拐拐折折,终于摸到了另一个井筒的大门边上。
上井前老者又叮嘱了一遍,并说井下的这一切对外人一概不能外露,别再招来祸灾。
说罢,拎起孩儿用手托住口中念念有词,这孩儿就手趴着井壁上的手窝、脚蹬着那脚窝,迷迷糊糊、腾云驾雾般地攀上了井口,一头就扎在了井沿边上。
一阵凉风把孩儿吹醒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井口,往北挪。
可这肚子不争气呀,饿得前胸贴着后脊梁呢!迈不开腿挪不动步,跌跌撞撞地奔了一段,好歹见到前头有灯光。
这家的看门狗见有黑影走近,汪汪地吠了起来。
犬吠警动了主人,一妇道人家推开山门一看,吓得“噢”地一声钻进了房屋门内,说孩他爹乜门口埝好像有人影。
男人道:“有个人怕啥,看你吓得乜个熊样。”
女人说:“你快去看看忒吓人嗹,上下一身黑也不知是人是鬼,可把俺吓煞了!”
男人出门一看也傻了:这傢伙伫在门前,透着寒气吊着膀子低着头,咋回事儿呢?
这孩儿见家里的男人出来了,两腿一屈便跪了下去,吓得男人“哟”地一声后退了两步,狗也吠得更厉害了。
男人定了定神,咋呼道:“你是人是鬼?是人就连喊三声。”
这边就使出吃奶的劲儿,从牙关里发出:“俺是人!是人。俺是人呀!”
嚎完一头就攮在地上,瘫了。
男人忙不迭地上屋里拿出油灯,掌着火苗子,凑近一瞅:这可不就是个孩子嘛!上前一步戗起了孩子,回头喊道:“孩他娘,帮我掌着灯!”就把孩子弄进屋里头,放到了杌子上。
女人心细,看到泥乎乎的衣裳,忙叫男人帮着她把脏衣服给孩子脱下来,也顾不得洗洗就换上自家儿子的衣服,可巧也合适。迭忙着往锅里撒了一把米,煮些米汤给孩子灌灌先暖和暖和肚子,又弄了点温热水把头脸和手脚用布巾擦了擦,一套活儿下来,米汤也就熬好了,把米粒滗出来往锅里窝上两个鸡蛋,调制成蛋花米汤,凉了凉让孩子喝了下去。
这孩子有些眯瞪,女人家就拾掇好了她儿子的床铺,让他先睡下了。
这一觉就睡了一个对时(一天一夜)呢!
醒来后孩儿睁着眼望望天瞅瞅地,就是不说话。
这家大婶给孩子端过饭来,说“孩子哎,先吃饭。”
孩儿看了看饭,又望了望婶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越哭声越大,拉也拉不住,一家人只好让他哭个够。
待气喘匀和了,大婶才问他:“孩哎,你这是打哪里来的?”
孩儿待要说,猛想起老者话,就打住了。
看孩儿不待说,便又端上饭,说:“咱不说嗹,先吃饭。”
一阵狼吞虎咽后,孩反倒沉不住气了,小声说:“婶,俺是从恁那门口下堰地里井上爬出来的。”
这老婆吓得喊来丈夫:“这孩儿说是从堰下头那枯井里上来的,你问他吧。”吓得忙躲到一边去了。
“你真是从下堰那井里上来的?”男人问。
孩儿点了点头。
这汉子跑了出去,狗也跟着在后头。直到井沿边上看到扒手的印子和井筒边蹬下的泥皮,这才回头告诉老婆是真的。接着就问道:”你在八亩地下的井?”孩子点了点头。
男子沉思到:八亩地过空可有一会儿了,还能有活人?还能从这枯井里钻上来?真是出了神仙啦。
他又看了看孩子,还是一副不像要说的样子,就不再问了。转声又问:“孩儿啊,咱不提这事了,你家住在哪里?”孩儿摇了摇头也不说,意思也不想让别人知晓。
这家人心里有数了,就再也就不问了。
孩子忒弱了,这女人就调对着让孩子吃好。今天割块肉,明日买点鱼,鸡蛋那是家里鸡下的,不几天的功夫,孩子的小腮儿就奓煞了起来。
期间男人悄没声地踅摸到八亩地井上,只见井口已被蓬成个大土堆堆,辘轳架也拆了,一片凄凉景象。
往回走时,这男人动了心思。步量着这井口到家旁边枯井的距离小千把步呢。他是咋着上来的?那时候人迷信,也不敢多想和多问。
这一日早晨,孩儿吃完饭后就给婶子跪下了,这婶儿就叫儿子帮着把他拖拉了起来。孩子道:“婶子啊,您和叔加上俺兄弟是俺的恩人哪!我给您磕头。”说罢“嘭、嘭、嘭”一连三个磕得地皮咚咚响。
然后说:“我该走了,我得走。”婶儿问他:“孩儿,你去哪?”
孩儿道:“我得从这往北走,一直走,越北越好,走到头。”
这婶儿看这小子神神道道,眼色迷儿不瞪,吓得也不敢再问了,忙叫自己的儿子:“把恁爹找来。”
孩子去了。
婶子迭忙着翻箱倒柜地把儿子的衣物找出来,又煮上了些鸡蛋,把家里仅剩的麦面搲出来烙成饼子,预备着这小厮在路上吃。
当家的人回来了,他默默地又打量了一下这孩儿,摸了摸孩儿的脸蛋,又拍打了下孩子的臂膀。说道:“就知道留不住你呀,有些话你也不好说,走吧。”说着从兜里摸出一把零钱来,说道:“家里不富裕,出去借了点,不多。你拿着,用得着的时候省下受窘。”又把他儿叫过来:“和你哥爬长岭送到猪食槽后就记着往回返。那埝儿前七后八,到龙口庄八里,离咱庄七里。你一个孩子家爹不放心。可记住:分头时谁也不兴送谁,各走各的。”又对这孩说:“孩子啊,今日咱走到龙口庄可就要住下宿了,我听大福子说了,你要往北走,咱不能一直走,遇上合适地儿,待上几天歇歇脚,打听打听再慢慢走,记住了啊。”
孩子听着直点头,这时婶子已把吃的用的拾掇好,交到俩孩手中,孩子又跪下磕了头后说:叔婶的恩情俺今辈子忘不了。说完就和这家的孩子沿着小路往北而去。
长岭道上猪食槽边,俩孩不舍地相互抱了抱,这孩儿说:“大福弟你赶快往回走,晚了叔和婶惦记着呢。”只见这大福子从怀兜中掏出两个琉璃蛋蛋,说:“哥哎,路上躁得慌时,打个蛋儿解解闷,收下。”俩人拉了拉手各自别过。
孩儿一路风餐露宿,往北行走。
遇到富庶地儿,给人家扛点小活,挣点路资,贫瘠地儿就讨点吃的,一股牛地往北边赶。
一日来到了山海关前,远处瞭瞭出关乜埝儿,查得很紧,还琢磨不出啥法儿呢。
忽地小眼一亮:见到一个小子随着一队驮子走了过来,心中立时有了谱气。
驮队排队等着出关。熊孩儿就和乜个小子混熟了。但见这孩从兜里摸出一个琉璃蛋,拤在手上蹦地就弹了出去,乜孩儿看得眼珠儿都发蓝,想玩呢。
孩儿说:“若让俺随着你的驮队出关,我就让你玩个够——送给你。”
乜孩子忽地一把夺过,转身告诉了身边大人,回过头来便说:“行,但不兴反悔。”“谁反谁是狗!”——俩孩儿同时说道。
过关了,眼见这驮队进门洞多大半了,这小厮猛地从怀里摸出一把锥子朝跟前骡子的大腿根上就扎了进去,骡子受惊一阵狂奔,把整个驮队冲得人仰马翻,乱套了。俩熊孩趁着乱在驮队中左右腾挪,不一会儿就从北门洞口钻了出来,像没事人似地在等人呢。
队伍等齐了往北走,到了铁岭一带,驮队到家了,这孩还邀小伙伴到家里玩住了几天,就又往北走,一直走到满洲里漠河边上的一个镇上问了问,可走到国边边上了,再走就是国外了。
正好有个山东人在此开饭店,就此流落在店里给人打杂了。
二
这地儿可算个繁华所在。
处在中苏通关隘口,关东黑土地和原始森林的交汇处,矿产丰富,资源充盈。镇面上三大马路排开,商贾如鲫,店铺林立,五行八作一应俱全:赌场烟馆比邻而居,明妓暗娼夹杂其中;西医中药明争暗斗,警匪一家相得益彰;说大鼓书的站摊儿,砸牛骨头的串门头;澡堂子,当铺子,推车挑担贩苦力;成队骆驼沿街行,叫卖声声入耳中。
掌柜可稀罕这远道而来的小老乡,管吃管住,工钱合适。还能跟师傅学做生意啥的,倒也过得逍遥自在,一晃这大半年的时光就过去了。
合当造化,一日店里进来个穿皮大氅的老客,面相清奇,双目深邃,持一柄端头白羽丛立的紫藤杖,腰间钩挂着金光闪闪的小铜铃。店家看到贵客登临,忙不迭地延入包间,呼这小厮跟前照应。
落坐后,这店小二算得是口甘如饴,手脚麻利,眼神转圆,礼数周致。把客人照拂得洑洑流流,舒坦满意。临行时这老客把掌柜的叫过来,以手掩口,伏耳言语。不多会儿就告辞,当日无话。
次日清早,别的伙计都在备料顺菜,掌柜的把这孩儿叫至帐房,屏退闲人,缓缓说道:“孩子啊,你到店里半年有余,有心学艺,长劲可不小哩,人情世故应付得麻溜得体,你叔我挺满意。昨天你伺候的客人乃一奇士,是萨满的“大先生”,黑白两道、阴阳世事、捉妖拿邪、堪舆占卜、法术灵验无一不精,名震关东大半个地面。昨日云游至此,他瞅着你有灵根,可造化,有意收你为徒。这人可邪门,有多少人上赶着求他学艺,他不屑一顾,飘然一身,真世外仙人。不知是你俩有奇缘,还是对了眼,临走时让我告诉你:愿随他,是缘法;若不愿飘零于世,是有缘无份。为叔看这事儿可不是强求的买卖,你若愿跟他受漂泊之苦,他就来带你遁入萨满之门,不愿就当这话没说,他也不再登这个门。一切都是你的造化,说完一挑门帘就走了出去。”
孩子作了难。
一者:爷仨遭了难,自己被黑山爷爷救出了性命;二者是叔和婶子恩重如山;三是现掌柜对已不薄,这都是恩情啊。内心恍惚,主意不定,但转念想到黑山爷爷说的上井后不回头,一直往北走,或许有奇缘之事。心想莫不是就这奇缘吗?人海茫茫,为何他一眼就相中了我呢?唉,随命闯吧,或许就这命哩。
他找到掌柜,悄声说道:“叔叔大恩大德孩儿没齿不忘。说实话真不愿离开咱这店,离开您。但这先生说有缘,我认了。俺从山东千里迢迢流落到这里,他老人家人海茫茫云游到此就相中了俺,加上这一连串的经历,在这埝儿对上了号。我认命,愿随缘。”
掌柜的即差人告知这仙家,萨满先生赶到店里,谢过掌柜,一把拉住这孩儿,道:“今上半年就测到有缘者自山东地面到这里圆缘。我遍访关东,寻寻觅觅,昨日在这里一见到你,就断定乃我传授衣钵之人。掌柜的也是缘份,他能忍痛割爱也合当造化。徒儿啊,干咱这行可命苦啊!有几苦呢?学艺苦;忌口苦;孤身苦;行无定所苦;捉妖拿邪苦;风风光光外面好,孤苦零丁内心苦。这些苦,孩儿你能受得了吗?”
只见这孩儿俯身一拜扑通跪下:“掌柜叔叔待俺不薄,这恩永世不忘,师父寻到我渡化我,想必明瞭我的身世。我虽年小,命忒苦,是从死里走出来的人,啥苦都能咽下去。您若不嫌弃,俺就追随于您,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啊!”说到这,师父一把拉起爱徒:“我没找错人,这是上天的感应啊!”
说罢,师徒朝掌柜拱手作别,道谢出门。
在一个大宅院里住下来,师父首先为徒儿起名,得知孩儿是苏姓后,口中念念有词:“姓苏,自山东来,山东者,鲁也。是流落到关外的宾客呢,就叫鲁宾吧。”
自此,师徒在此谈经论道,也教些江湖应酬之术、中医入门理念等等。
时光如梭,转眼间就大雪纷飞,天地间银装素裹,尽显关外景色。
一日师父召呼徒儿道:这段时间算是入门,真要修炼得到人迹罕至之地、苦寒僻静之所才成,走,咱今日就进山修炼。
马拉爬犁把这爷俩一直拉到原始森林边缘的地儿,下车看,早有一座半地下大卧棚子。推门一瞧:各种生活物什一应齐全。外面朔风呼啸,里面虽不是温暖如春,但也觉得清爽明目,心静神怡。这孩子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呢。
关东地的冬尾巴长呵!
整整一冬,方圆几十里内,就这爷俩。师父那是十八般武艺恨不能倾囊而授,徒儿学得那是磁磁实实。
雪融了,天暖了,地面上拱出了绿茸茸的新草芽。
这爷们猫完了冬也该出关了。
自此,地面上再不是孤零零一人施艺,而是师徒俩形影不离了。
名气大,法术高,经历广,心胸阔,不几年的功夫,徒儿的眼力和心劲儿已与师父不分伯仲,江湖上也立起了苏鲁宾的仙名。
某日,鲁宾师父把他叫到跟前,深情说道:“你跟着为师学了这些年,手上的活儿学得也差不离了。徒儿啊,自家的前程要自己奔,你得出去闯荡闯荡了。一是能见识见识江湖险恶,二是对自己的本事增长也有益处,呆在师父跟前咋着也放不开手脚。总不能跟我一辈子,为师也好落得个做人的口碑啊。”
鲁宾一听,立马跪在师父面前,不说话,师父拉也白搭。
师父无奈,说:“你起来吧,有话好好说嘛。”
他这才站起来,说道:“师父,您无子,我无家。我内心已把您当生身父亲待的。流落在外,是师父收留了我,教我学艺,诂我做人,咱不单是师徒关系,是知心换命情同父子啊。咱爷俩在一起,你教我,我敬您,有个说话的对儿多好啊。至于身外之物,多少是多?有多用?有用吗?您拉巴我,我养您终老,您若不答应,徒儿在这儿可就长跪不起了。”
说完,又给跪下了。
师父佯做生气的模样:“起来吧,为师答应你还不成吗?”
师徒俩相拥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师父老了。
鲁宾周到地侍候师父,应酬着江湖上的事务,他的孝道,一时传为美谈,远近闻名。
师父呢,也在最后的岁月里把那压箱底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徒弟。
师父还是驾鹤西去了。
鲁宾按萨满教的仪规隆重地安葬了自己的恩师,痛定思痛,这五七和百日都过了,还沉浸在对师父的怀念之中,不能自拔。
大户人家找到门上,请鲁宾萨满大师做法,他低沉地回绝了。
来人道:“人逝不能复生,尽孝过当即为迂腐。再说你师父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你这无精打采的样儿。为了你师父的名声也得振作起来,总不能让人说你师父看错了人?继承了师父的衣钵而不弘道,是师父所期待的吗?”
一席话,惊醒了梦中人。
于是江湖上鲁宾“苏萨滿”的名声又传开了。
这一日,鲁宾应约到某军垦农场作法祈子。
农场主管生产的宋副场长,年过四旬膝下无子,望着同事战友们儿女成群的热闹劲儿,盼子心切。头脑一热,也顾不得这纪律那制度了,暗地里悄悄请大名鼎鼎的苏大萨满法师,作法求子。
这法儿正在行着呢,就有好事者溜进场部向一把手苏大场长打小报告了。
农场是副师级单位,千把儿人呢。此事可不小,迷信影响坏,邪风不可长。
场长心急火燎地赶到场部宿舍,进门就吼:“谁在这里搞迷信?”在场众人都默不作声,问急了,有人用手指点了点屋内。场长是个爆仗脾气,上去照门就踢了两脚,咋呼道:“开门,开门!”
求子这事,须是萨满师和这家女人单独进屋关门闭窗,密不透风。至于她俩在屋里搞啥喽子,外人不晓得,就因玄妙,才吸引人。只有那求子的急瞎了眼,家里的男人才能舍得皮脸豁上自己的女人和另一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堂入室秘施法术,真乃无奈、无语,没法儿呀!
宋副场长从人堆中踅摸过来,黑着脸一捋就把场长拽到一边说:“这些吃饱了撑得没事的熊行子,是他娘的饱汉不知俺饿汉子饥呀,我姓宋的无屌谓,可经不住你那嫂子成天白日的闹啊,哭哇。恁以为我乐意自家的老婆在里头和男人不知作啥堌堆吗?丢人!丢不起啊。”
苏场长急问道:“赵处长呢?这保卫处长当得可好!闹剧都闹到场部宿舍了。”
宋又拉了拉场长道:“这活儿是他揽的哩。”场长听后也愣了,又一想:也对。他俩是章丘邻村的老乡,怨不得。
门吱的一声就开了,那女人红扑扑地腆着脸儿一猫身子就闪进女人堆里去了,鲁宾款着步迈了出来,朗声笑道:“福星降临,鸿昌大运!借您老吉言,双子报门。”说完还朝场长拱了拱手。
场长立时明白了,副场长求子,保卫处长牵线,这活儿都做完了,自己这再干预,这坏人当得忒不值了。
于是瞪了这厮一眼,就登到了门口的高处。
鲁宾一看这架式不对呀,见好就收把。靴底下抹油一溜了之。
场长发话了:“咱在这里没外人吧?宋场长两口子为人大伙儿心里都有数,他今日弄了这一出,就算是咱老家那边天旱祈雨吧。我这里代他两口子谢谢大家了。事都办完了,散吧,散了吧!”
大伙儿一轰而散。
可别说:逶过年来到了三月,这家老娘妹还真给他宋家生了俩大胖小子,一家人这个恣啊!
场长一阵心血来潮,指示保卫处长,待老宋俩儿满月时,个别约请一下这萨满师。也顺带给老宋两口道道喜,压压惊。要没去年那一出,说不定这俩儿子还在瓜哇国哪。
满月已过,场长、老宋和保卫处长做东,专门请了鲁宾一桌。
席间,说起了宋副场长和赵处长是山东章丘的老乡,勾起了鲁宾的思乡之情。说道:“宋场长哎,咱也还是老乡来。”宋场长问:“您府上?”鲁宾说:“咱隔着不远呐,俺家是淄川的。”
苏大场长一听来了劲头:“你是淄川哪里的?”“我是淄川东南鲁家庄里的。”鲁宾答道。
你猜俺家在哪里?鲁宾说:“您恁大的领导,我现在看您心里还打着鼓来,可不敢猜您是哪里的。”
“俺家就在那黄崖头上。”苏大场长道。鲁宾道:“知道嗹,咱还是邻庄呢。”
感情一下子就没法儿弄了,这酒众人喝了个小辫儿朝天,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说到深处,两人还是拐着弯的亲戚呢。若论本家辈份,场长是鲁宾的爷爷辈。
这老乡和爷们可算是认下了。
三
转眼间就到了七十年代。
苏场长随着年龄增大,恋乡之情愈发强烈。当他从战友口中打听到一知己战友现任省某厅厅长,就动了调回山东的心思。他要先回趟山东摸一下情况探探路。
临行前招呼几个知己老乡见见面,家乡之情溢于言表,鲁宾说道:“小爷爷您这一回去,也勾起了我的返乡心思,也不知俺娘怎样了。”大家这才关注起鲁宾的家事。
鲁宾就把家住哪里、爹娘状况,又把遇到貔狐,井下如何透水,眼看着父亲和哥哥被淹以及奇遇黑山爷爷的事儿说了一遭,众人听了,莫不称奇。
苏场长沉吟了大半天说道:“我这次回山东协商调动之事牵扯部门很多,手续是个麻烦事。想要把你办回山东这事我倒觉得好办,但办事要有凭据呀,没凭据一不好找人,二是有些事说不清楚。”
鲁宾从怀里摸出个琉璃蛋蛋,递给苏场长:“这是当年在长岭猪食槽边分手时我那大福子兄弟送我的,到家后您去朴家庄东头放羊的那家见到俺那恩人拿出这球一问就是。让我婶找出我那炭衣裳,再上鲁家庄一访便知。唉,俺那苦命的老娘不知还在不在人世呢。”说着又哭了起来。
众人相劝,苏场长说:“你说的这些能证明你个人的身份和经历,但要办手续须到庄里和公社询问,这猛一说咱也弄不清楚,到家再说吧。就是我的事儿不办,也要帮着办好你的事。”
个数月后,场长回来了。
还真是,场长调山东手续繁杂,除了他个人外还牵扯到家属和几个孩子的手续,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办完的,反倒是鲁宾的事办得出奇地顺当,从朴地拿炭衣裳去鲁家庄一问,这事无人不知,找到他母亲时,老人家捧着衣裳就哭晕了过去。
一问才得知:透水后,村里人以为这爷仨都淹在了井里,他娘就像塌了天样无依无靠,那时兴嫁出的闺女不能回娘家住,没办法族家商议由族长作主把娘和本家一个小叔子撮合在一块。他叔和他娘又给鲁宾添了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妺。这一家人都盼着鲁宾返家来呢。
村里书记是“作”字辈,场长是“继”字辈,加上鲁宾这“成”字辈,继作成守兴,正好是爷仨。书记去了趟公社手续就办妥了。
东北这边手续也好办,让场里派人帮着办就行。
鲁宾听到这话,孩儿般跳了起来,在场人也为之高兴。
鲁宾要迁回山东了。
把这边的什物该送的送了,能卖的卖了,场长早就安排场里做了几个一米八长、四寸厚的红松板子钉起来的木箱子,装上东西办好托运手续先走着。
临行前几天,轮着家吃饭,走的这天一家人把鲁宾送到火车站,依依不舍,倾情相送。
终于到家了。
先去朴地庄拜见了叔和婶子,和大福兄弟有说不完的话,鲁宾拿出财物谢了,婶子要留下他在朴地住,鲁宾是说啥都不肯。
回到鲁家庄,苏家是大姓,阖家迎接远行的游子。鲁宾见到母亲就跪下了,在场人无不泪目,叹惜不己。
书记见到了远来的侄儿,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在哪安家时,鲁宾说朴地庄,鲁家庄哪里都不能去,怕老娘天天见儿子想起一家子难过,想另找地方图个清静,生计不用考虑,自己大半辈子有些积攒够用就行,落叶归根遂了一生大愿足矣。
书记也考虑到了这一层,说村后山五八年公社时建了一个小水库,解决人畜用水和灌溉菜园地用,清静倒是清静就是离家远些。你若去住连带守护,耽误不了挣工分还能安家,过几日我领你去看看中不中意。
鲁宾听了后两眼发光,连说行。拉着书记就去看,到了水坝上,一看连连说太好了,就住这里。
草作安顿,便央书记叔作主,置好物什,一家人到朴地庄同着叔和婶子等人,在八亩地井那大土堆前摆上了两桌大供,一桌是给爹、哥和众难友的,另一桌是供给黑山爷爷的。
供完后烧纸,那两堆相距甚远的黄表纸点着后,不知咋地这火苗就呼地搅合到了一起,打着旋儿卷上天际,在场人都骇地不知所措,连忙俯地跪倒,口中呼号阿弥陀佛!
小年数过去了,这水坝在鲁宾辛勤照拂下,摆扯得那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人人见了都流连忘返呢。
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苏场长一家到来,这儿就热闹大发了。
场长成了省某监狱副政委,虽在职级上吃了点亏,收入上好在是减了不是很多,咬咬牙也就认了。
小奶奶家表姐的儿媳年近四十怀里未见动静:跑遍了各大医院皆无果而终,这不就窜掇着去山后水库找鲁宾作法求子,鲁宾回来后就未再出山。推辞不过,只好再施法术还真是给怀上了。
这一捣咕可不得了了,方圆村庄都知水库上有神仙,一时间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南坪村有个放羊老汉,总是到水库上饮羊。一来二去,两人话说投机了,饭都在一起吃。这天老汉在家无意中把苏神仙能作法祈子的事儿向老婆子露了露,那婆子的小表妹正好也是多年未有生养,就央羊倌领着她和表妹去了,作法后给钱鲁宾那是死活不要,还留下三人在水库上吃了顿饭。老婆子想,这么大的恩情无以为报,就想叫羊倌把鲁宾的替换衣物和床上被褥啥的捎回来洗洗,羊倌嫌沉不干。老婆说;反正水库上有的是水,就带上搓板和洗粉,在那儿整整洗了三天,晒干叠好后才算完。在洗衣过程中听鲁宾讲关内关外遇到的稀奇事儿,这婆子听得是五迷三道,如醉如痴!看鲁宾孤身一人就想给他说门亲事,鲁宾说明这辈子的因由,她长叹了一口气:“兄弟哎,你这命可真苦!”
南坪有集,逢五排十,老婆子嘱咐丈夫:你去和咱那兄弟说,叫他来赶赶集,我在集上等着他,中午你替他看好水库,让他在咱家吃顿热乎饭回去把你替回来。
羊倌去说,人家鲁宾不来,待了下集老婆子就亲自出马,硬是把鲁宾拖到集上来了。自此每隔几集,这个羊倌就去看着水库,鲁宾就下山赶集,时间一长,人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羊倌大哥去世后,鲁宾就不来赶集了。这婆子开了个家庭会,婆子说:“你叔命苦,没找上媳妇过日子,他可不是找不上啊,是命里不能找啊,要找早就找上了。你爹没了,人家也不敢上门了,为娘的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我去说动他不合适,恁看这事咋办?”
大儿二儿表示:“俺俩把叔请来,该咋地还咋地,和咱家的情份不能断了。”
于是这哥俩去水库上好说歹说,连拖带拽地就又把这叔拉回原道了。
时间过得真快,婆婆老了,鲁宾亦老矣。
在此前,朴地庄的大福弟弟、自己家的两兄弟都曾去水库说动鲁宾回家养老,鲁宾依然是谁家也不去。
冬天来了。
这一夜雪下得可真大呀,天刚噜苏明,老太太被一阵吠声惊醒了。推门一看是水库上的护家犬,见它泪汪汪匍匐在地声声咽呜,心里头一紧楞怔住了,口中喃喃絮叨:俺乜兄弟这是走了?唉,也好,走了好啊。身子一铺瘫就抢在了门框上。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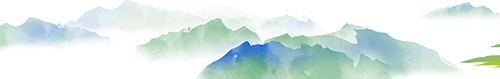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