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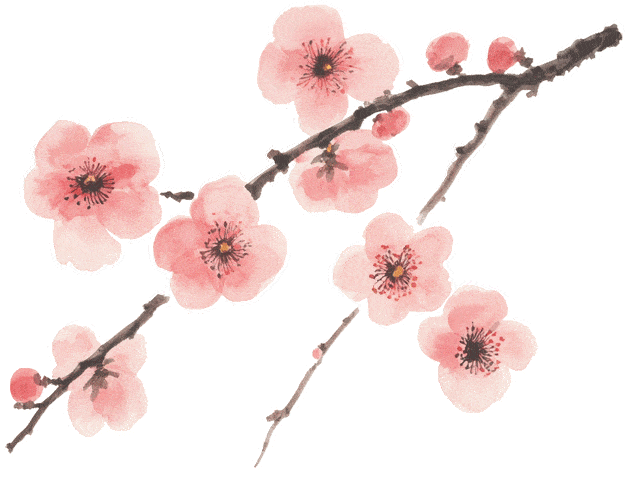
樊卫东(河北)
夜深人静,窗外月痕淡淡,岳父赵铁圪的身影,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生于 1941 年,逝于 2006 年,匆匆六十六载春秋,一生时运不齐,命运多舛,却如太行山石一般,磊落忠厚,默默扛起了世间的风雨。
岳父本是武安市管陶乡长亭苏家的孩子。太岳父赵长河、太岳母膝下无子,经人说合,他自幼便被过继到西豆庄村赵家,担起了顶门立户的责任。
母亲生前曾对我说过一段往事:“你岳父小时候常跟着他娘回姥姥家,我俩总在一块儿玩。那年你有个舅舅刚出生没几天,我拉着铁圪到家里耍。没过多久,你舅舅就没了。大人们都说,是铁圪‘引进’了 —— 乡里的老规矩,月子里的产妇房间不能进生人,说是会冲了娃娃的命。” 这桩儿时的旧事,想来竟成了岳父懵懂岁月里,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印记。
太岳父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模样周正,手脚勤快,家境也算殷实。岳父的童年,因此有过一段安稳的时光。可天不遂人愿,太岳母早早撒手人寰,丢下一双儿女,没娘的孩子,就像断了根的草,日子的凄苦,想都不敢想。
中年丧妻的太岳父,既当爹又当妈,终究顾此失彼。后来几经周折,他从邻村沙河娶了后妻老鱼奶奶,这个破碎的家,才算又有了几分烟火气。
岳父成年后,先在符山铁矿谋了份差事,没干几年便参了军,成了一名陆兵。军营的淬炼,让他身上多了几分英气。几年后退伍,恰逢国家三线建设的热潮,他二话不说,远赴新疆天山军垦农场,戍边垦殖。
岳父成家后,岳母也跟着去了新疆,在军垦农场安了家。我曾见过他那年轻时的照片:头戴棉军帽,身披军装,眉眼俊朗,英气逼人,那模样,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岳母当年的工作证,如今还好好珍藏着。听岳母说,她在农场还种过罂粟,那时军管极严,一粒一颗都不许私自带回家。漫漫军垦路,不知他们熬了多少个寒暑,妻子兄妹四人,竟都出生在这片遥远的戈壁滩上。
太岳父病故后,太岳母老鱼无人照料。本家的长辈们日日劝说,让岳父回乡。老鱼奶奶晚年双目失明,日子过得愈发凄苦。岳父岳母万般无奈,只得辞了农场的正式工作,拖家带口赶回西豆庄,侍奉这位继母。那时若活络些,凭着岳父曾在符山铁矿工作的履历,回去找领导说说情,重新回矿上上班,也不是没有可能。可岳父生来老实巴交,宁肯自己吃苦,也不愿给人添麻烦,竟一次都没有开过口。从那时起,他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把余生的光阴,都种进了家乡的黄土地里。
老鱼奶奶和我奶奶私交甚好,常拄着拐杖来串门。只要听见门外传来 “嗒嗒” 的拐杖声,我就会小跑着去开门,扶着她上台阶、跨门槛,送到奶奶屋里。两个老人家凑在一块儿,家长里短地唠叨半晌,我便再护送老鱼奶奶回家。这样的往返,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她常在奶奶面前夸我懂事,待我也格外亲厚,每次来,总不忘给我带些柿子面窝窝头,或是别的吃食。记得有一回,我一时疏忽,没留意脚下的水窖口,老鱼奶奶的拐杖 “咚” 地一声杵了进去,吓得我魂飞魄散,赶紧扑过去扶住她,小心翼翼地送她回了家。
大舅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岳父咬咬牙,举全家之力,在村边盖起了七间平房。红砖敷面,土坯垒墙,总算给儿子成了家。打土坯、盖屋顶的那些日子,亲戚们都来帮忙,妻子那时年纪尚小,也跟着搬砖、和泥、打土坯,早早便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大舅哥自小留在老家抚养,岳父母总觉得亏欠了他许多,平日里格外娇惯,竟渐渐养成了他好吃懒做的性子。因此,岳父晚年的春耕夏耘,多半要靠女儿女婿们搭手。
我至今记得那件事:秋收时节,庄稼拉回家后,大舅哥开着拖拉机把粮食卸在自己门口,便撒手不管了。岳父的住处离得不近,却只能一个人,一趟一趟地把庄稼扛回去。他与我家隔得近,平日里有事总爱找我帮忙,可那天,他竟没喊我一声。听妻子说起这件事时,我心里又酸又涩,自那以后,便更主动地帮着岳父春耕秋收、晒谷藏粮。后来我带着妻子外出打工,能帮衬他的日子,便少了许多。
那是一个寻常的早晨,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你快回来吧,你岳父昏迷不醒了!” 我和妻子放下电话,一路心急火燎地往家赶。一进门,就看见岳父躺在床上,人事不省,岳母守在床边,哭得撕心裂肺,一家人乱作一团,手足无措。
我疯了似的跑去叫村医 —— 那是我的二姑父。他赶来后,搭脉听诊,看了看岳父的瞳孔,半晌才红着眼对我说:“恁岳父不行了,就算叫救护车来,也是白搭……” 我哪里肯信,拉着他的手再三央求,二姑父拗不过我,只好又跟着我来到岳父床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终究还是摇了摇头,嘱咐我准备后事。
三个女婿一个儿,我们四人抬着岳父,从借住的院子里出来。一里多的路,谁都不敢歇一口气,生怕慢了一步,就留不住他。把他抬到自家炕上,才敢拔掉输液的针头。看着他的胸膛渐渐停止起伏,那一刻,满屋子的哭声,震碎了窗外的天。
家乡有句老话:“一个小子仨女婿,好比一杆秤。” 那几天,愁雨连绵,我们哭天喊地,送岳父走完了最后一程。几年后,大舅哥也因病离世,只留下年迈的岳母,孤零零地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受尽了人间的凄风苦雨。
又是一个深夜,忆起岳父的一生,几多感慨,几多唏嘘。他这一生,没享过什么福,却把 “忠厚” 二字,刻进了骨血里。他像一粒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过继的赵家,落在军营的训练场,落在新疆的戈壁滩,最后落在家乡的黄土地里,生根,发芽,默默枯萎。可他留给我们的,那份隐忍的孝,那份踏实的诚,却如太行山上的松柏,岁岁常青,从未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