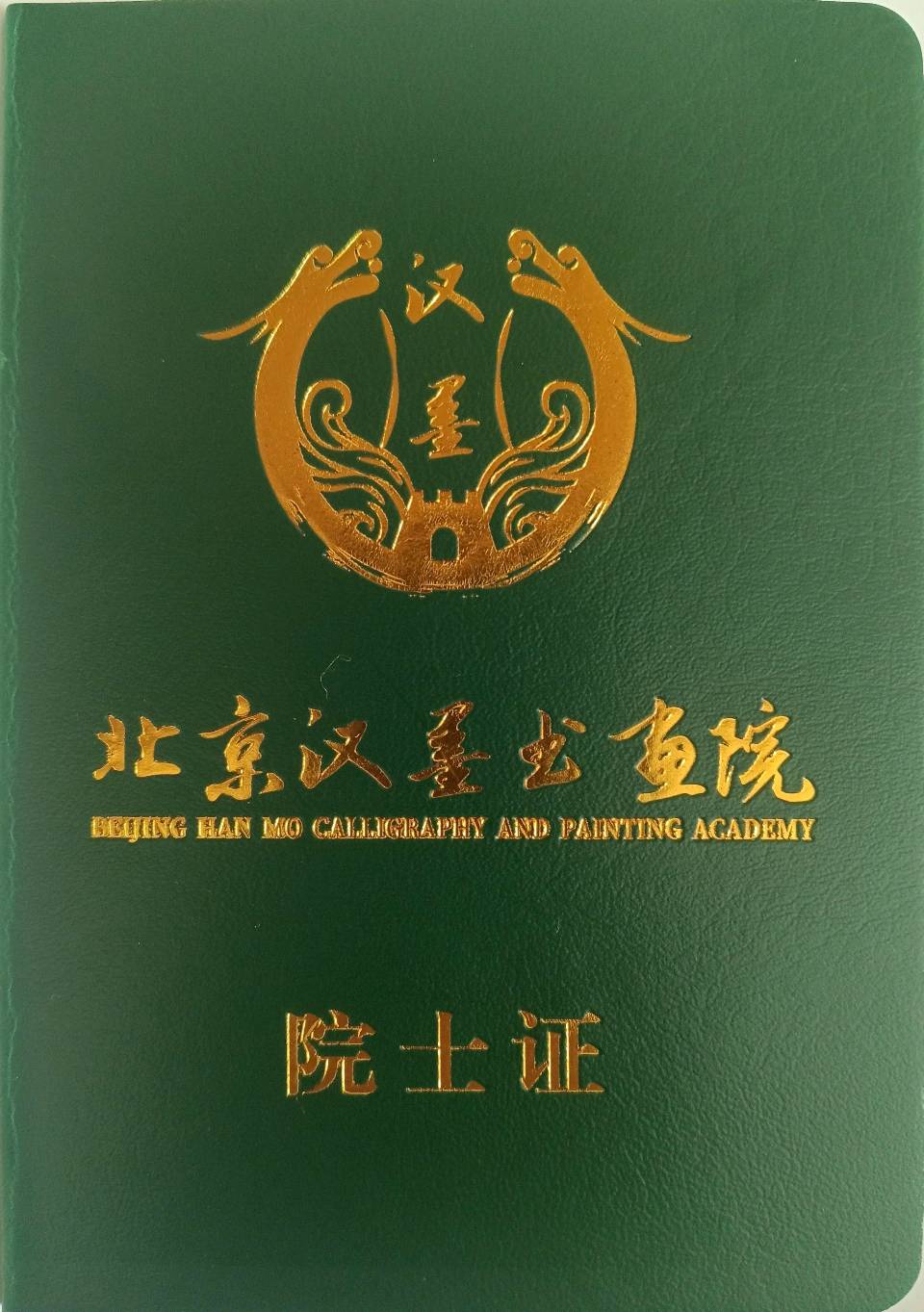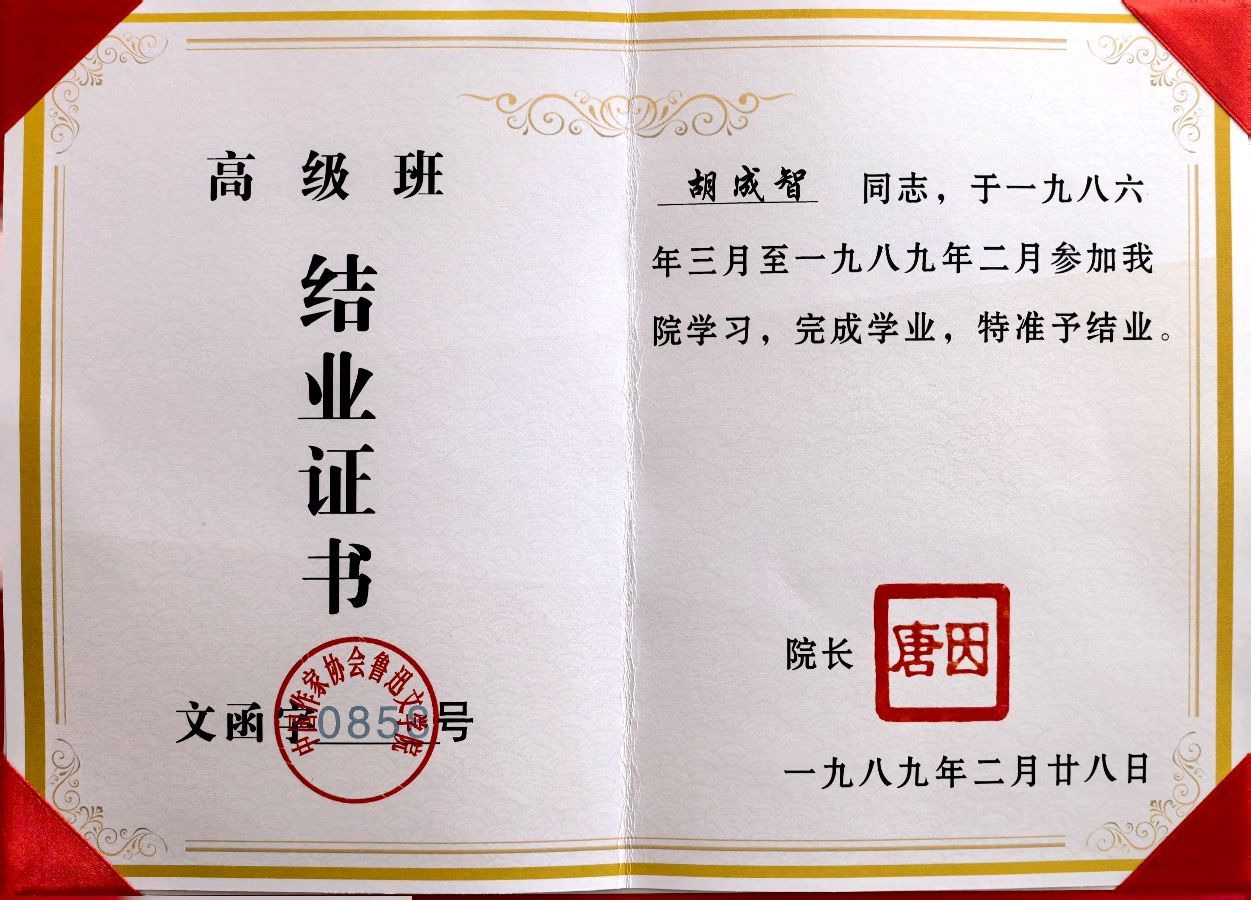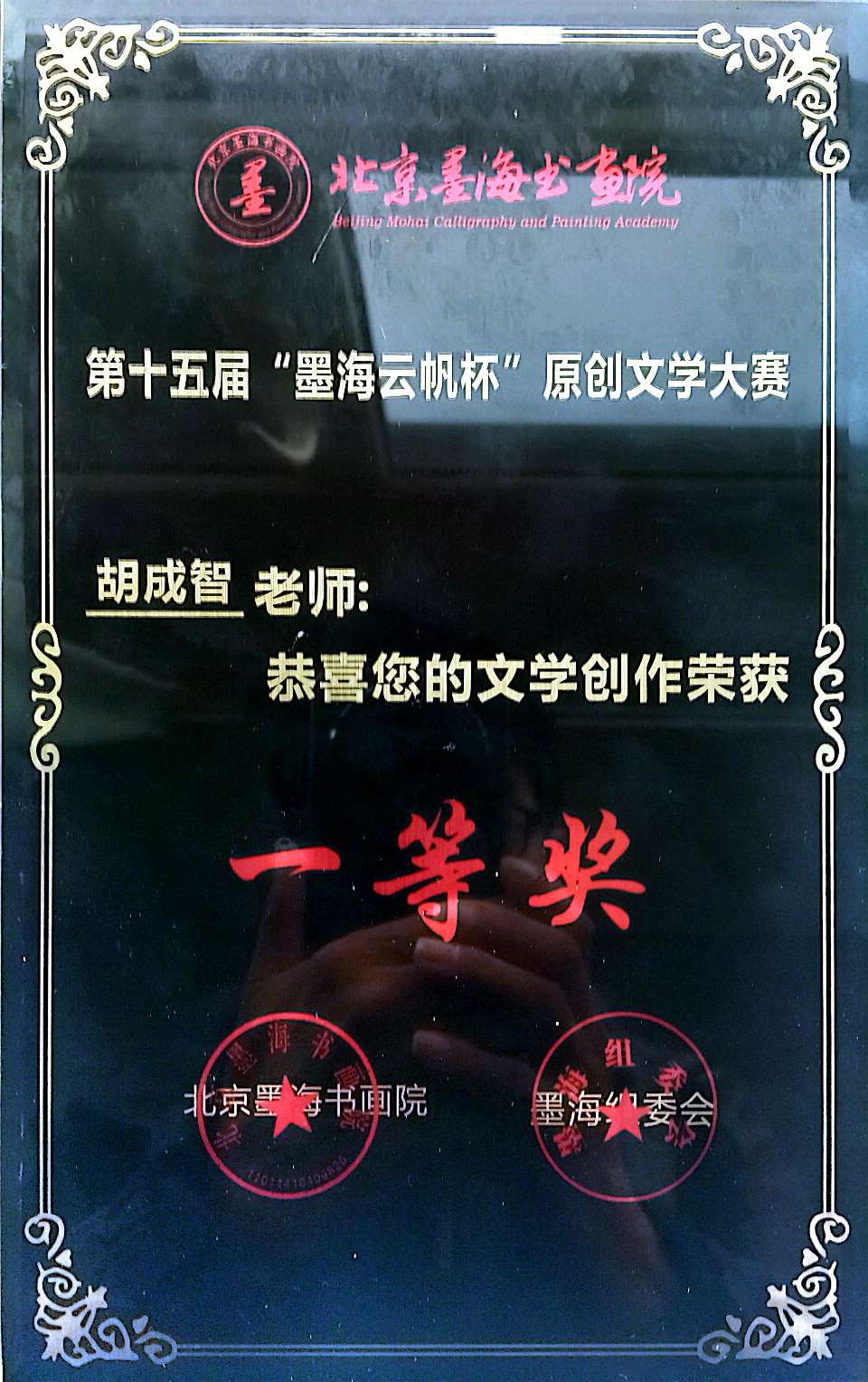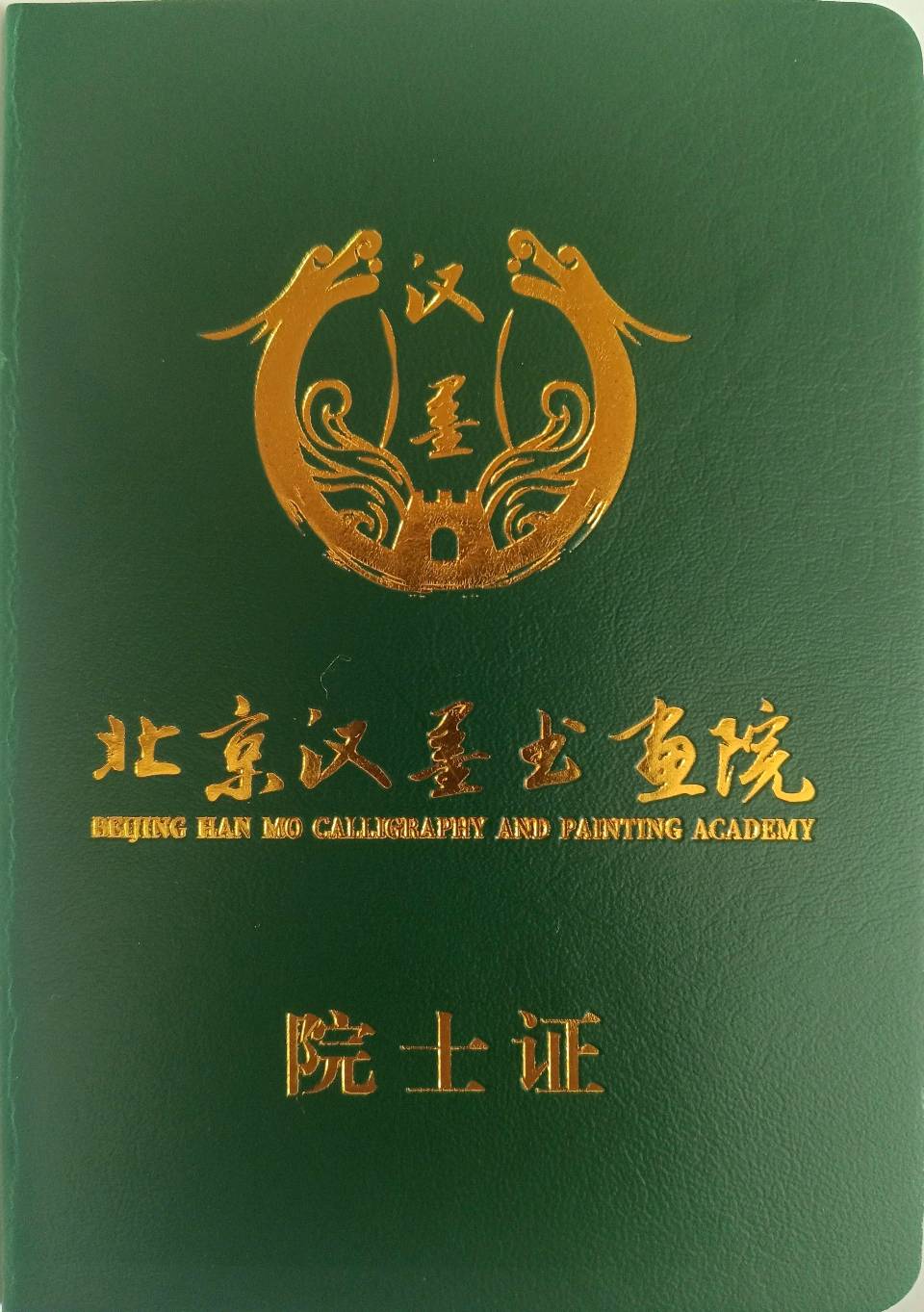第五章 密匣
雨水在沈府“文脉书阁”的兽头瓦当上汇聚成流,昼夜不息地倾泻而下,声音单调而执拗,仿佛在催促着时间的流逝。书阁内,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数十只巨大的樟木书箱已整齐码放,像一列列沉默的棺椁,等待着未知的归途。
沈文谦站在书架间的窄梯顶端,身形在昏黄的煤气灯下显得格外瘦削。他正从书架最高、最隐秘的隔层里,取出一个用深青色绸布包裹的长条形木匣。那绸布因年岁久远,颜色已晦暗不堪,但依旧能看出其上隐约的云纹。他的动作极其缓慢,带着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庄严,仿佛他捧着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沉睡的灵魂。
沈知白在梯子下仰头望着,屏住了呼吸。他认得那个匣子,那是沈家世代相传的“密匣”,非家主不得开启,非家族存亡之际不得动用。他只在幼时,见祖父在临终前,由父亲陪同,开启过一次。
沈文谦抱着木匣,一步步从梯子上下来,脚步踏在木质阶梯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将木匣轻轻放在中央一张铺着白色细棉布的长案上,那棉布是为了防止古籍受损而特意铺陈的。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用一块干净的软布,细细擦拭着匣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他的手指抚过那冰凉坚硬的木质,感受着其上粗粝的纹理和几处因常年摩挲而变得光滑的边角。
“知白,”他开口,声音因连日来的疲惫和心力的巨大消耗而异常沙哑,“去净手,焚一炷‘安定香’。”
沈知白依言而行,用铜盆里的清水仔细清洗了双手,然后用火镰点燃了书案一角紫檀木底座上的线香。一缕青烟袅袅升起,带着沉稳的檀香气,稍稍驱散了书阁中陈年旧纸和霉湿空气混合的味道,也试图安抚着空气中弥漫的无形躁动。
做完这一切,沈文谦才从腰间取下一枚贴身收藏的黄铜钥匙。那钥匙形制古拙,匙柄雕刻着一个小小的篆书“沈”字。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鼓足了莫大的勇气,才将钥匙插入木匣侧面的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书阁里显得格外清晰。
木匣的盖子被缓缓掀开。里面衬着明黄色的软缎,已然褪色。软缎之上,平放着一卷手稿。那手稿的纸张并非寻常的宣纸或竹纸,而是一种微微泛黄、质地紧密的皮纸,边缘已有磨损,显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展阅。
沈文谦戴上雪白的棉布手套,极其小心地将手稿取出,在长案上缓缓展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手筋骨开张、力透纸背的颜体行书。那不是印刷品,而是墨迹淋漓的手书。
“《守城录》……”沈知白凑近,低声念出开篇的标题,心中猛地一跳。他博览群书,立刻想起这是南宋陈规著述的城防兵书,但眼前这份,显然并非刊印本。
“不错,是《守城录》。”沈文谦的目光紧紧胶着在字迹上,声音低沉而肃穆,“但这不是普通的抄本。这是文信国公——文天祥,在督师抗元途中,亲手批注过的本子。”
“文天祥!”沈知白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顶门。文天祥!那位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魂!他的亲笔批注!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只见那手稿的字里行间、天地两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朱笔小楷。那些字迹时而激昂,时而沉郁,有对兵法的阐发,有对时局的剖析,更有许多直抒胸臆的悲愤与慨叹。其中一页,在论述“民心可用”之处,赫然用朱笔圈出,旁批一行小字:“守城在先守心,心散则城破,心聚则城存。” 笔力千钧,仿佛能看见那位孤忠的丞相,在摇曳的烛光下,以笔为戈,呕心沥血。
沈文谦的手指虚悬在那朱批之上,不敢触碰,仿佛怕惊扰了七百年前那不屈的精魂。“你看这里,”他指向另一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信国公论及巷战、论及粮秣水源、论及如何在我众寡悬殊之时,凭借城垣与死志,与敌周旋……这不仅是兵书,这是……这是我华夏士大夫,面对强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实录!”
他的眼眶湿润了。这几日来,所有的焦虑、无助、被挚友背弃的悲凉,在此刻,仿佛都在这卷沉甸甸的手稿中找到了回应与依托。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无数像文天祥一样,在绝境中坚守道义、以身殉国的先贤英烈。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在他胸腔中剧烈地激荡着。
“父亲,这……这真是无价之宝!必须带走!无论如何也要带走!”沈知白激动地说,声音都有些变了调。
“带走?”沈文谦喃喃道,目光却从手稿上移开,缓缓扫过周围那堆积如山的书箱,扫过这藏书十万卷的“文脉书阁”,最终投向窗外那被雨幕笼罩的、未知而危险的远方。“知白,我们能带走多少?这卷手稿固然珍贵,可那边箱子里,有苏轼的手札,有朱熹的注疏,有《永乐大典》的残本……哪一件不是先人心血,哪一件不是文明碎片?”
一股巨大的、近乎绝望的矛盾感,再次攫住了他。拥有得越多,需要抉择舍弃时,便越痛苦。这卷《守城录》批注本,此刻在他手中,重逾千斤。它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带着它,就像是携带着一个沉重的、关于坚守的誓言。
他沉默了许久,终于,极其缓慢地,将手稿重新卷好,放回木匣之中。但他没有盖上盖子。
“将它单独装一匣,”他吩咐道,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冷静,但那冷静之下,是汹涌的暗流,“用最好的油布包裹,置于最坚固的箱中。它……将与我们沈家,共存亡。”
沈知白郑重地点头,双手接过木匣,感受到那沉甸甸的分量,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历史的、精神的。
就在这时,老仆沈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书阁门口,脸上带着欲言又止的神情。
“老爷,码头上的张把头……悄悄派人递了话过来。”
沈文谦猛地转身:“怎么说?”
“他说……林家船队,三日后黎明,准时启航。”
书阁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线香燃烧时细微的“滋滋”声,和窗外永恒的雨声。
三日后。最后的期限。
沈文谦闭上眼,深吸了一口带着檀香和书卷气的空气。当他再次睁开眼时,眸子里所有的迷茫和痛苦都已褪去,只剩下一种近乎冰冷的决绝。
“知白,按照第二套方案执行。所有选定的人员、书箱,明日午夜,于后角门集合。”
“那……地窖的封藏……”
“我亲自来做。”沈文谦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有些路,既然选了,就不能回头。”
第六章 暗流
林家“蕴秀园”的忙乱,已从明面转入了地下。表面上,园子依旧维持着往日的宁静,只是下人少了许多,显得有些空荡。但在地下银库和几处隐秘的仓房里,紧张的气氛几乎要凝成实质。
林慕云坐在书房里,面前摊开着最后一批需要处理的契约和账册。他手中的紫檀狼毫笔悬在半空,一滴浓黑的墨汁,颤巍巍地凝聚在笔尖,将落未落。他的目光停留在账簿上“沈记文翰堂”那一栏的往来款项上,数字清晰,记录着两家过去几十年在笔墨纸砚生意上的合作。如今,这些数字都成了刺眼的嘲讽。
沈文谦拒绝金子的画面,又一次不受控制地闯入他的脑海。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比任何愤怒的斥责都更让他如坐针毡。他林慕云一生精明,善于衡量,却在那双眼睛面前,感觉自己像个赤裸的、唯利是图的小人。 这种认知让他烦躁不堪。
“父亲。”林焕章推门进来,他穿着一身利落的短打,额上带着汗,眼神里却闪烁着事态尽在掌握的亢奋,“最后一批货已经上船了,是那批德国产的精密仪器和西药,都放在防水隔舱里。船上的护卫也增加了人手,配了家伙。”
“嗯。”林慕云淡淡地应了一声,目光仍未从账册上移开,“人员名单最后核定好了吗?”
“好了。除了我们本家、各房亲信,还有商会里几位坚决跟我们一起走的元老家眷,以及……我们旗下工厂里几十个核心的技师和他们的家小。”林焕章顿了顿,补充道,“人数比预想的多了两成,船位有些紧张,所以我让人把原先准备装载一些家具和装饰物的舱位也腾出来了。”
“做得对。”林慕云终于放下笔,那滴墨终究没有落下,在雪白的宣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人是根本。只要人在,技术在手,就不愁没有东山再起之日。”
他话虽如此,心中却并无多少“东山再起”的豪情,反而充满了离乡背井的苍凉。他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漕运水利图》前,手指沿着那条代表他们即将撤离的航线缓缓移动。航线蜿蜒,最终指向南方一个陌生的港口。那里没有他熟悉的临州街巷,没有沈家书阁的墨香,只有未知的商机和险恶的竞争。
“沈家那边……有什么动静?”他终究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艰涩。
林焕章脸上掠过一丝不屑:“还能有什么动静?听说沈世伯带着他儿子和几个老仆,日夜不停地整理书籍,看样子是真打算把那些破书当命根子带走了。哼,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父亲,您就别再为他们费心了,路是他们自己选的。”
林慕云沉默着。他了解沈文谦,那是个外表温和、内里却极其执拗的人。他一旦认定了某件事,便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这种文人的“气节”,在太平年月是风骨,在这乱世,却是取祸之道,甚至可能累及全家。
他忽然想起一事,眉头微蹙:“码头上,还有没有别的船?我是说,除了我们林家和几家大商号的船队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小船、民船,可能被沈家雇用的?”
林焕章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思索片刻,摇了摇头:“我仔细查问过了。但凡像样点的船只,不是被征用,就是早已被各方势力预定一空。剩下些舢板、小渔船,在近岸跑跑还行,根本不可能进行长途航行,更别说装载大量货物了。沈家……他们走不了。”
最后四个字,像冰冷的钉子,敲定了沈家的命运。
林慕云的心,随着这四个字,彻底沉了下去。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也破灭了。他仿佛已经看到,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沈家老小带着他们那几箱视若性命的书籍,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或者更糟……
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再次涌上心头。他猛地转过身,不再看那幅地图。
“焕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你去准备吧。记住,撤离之事,务必机密。最后时刻,不要节外生枝。”
“是,父亲!”林焕章躬身领命,快步离去。
书房里又只剩下林慕云一人。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和连绵的雨丝。这雨,下得人心里头发霉。他想起年轻时,和沈文谦一起在雨中登山,两人衣衫尽湿,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畅谈理想。那时,他们都以为未来是一片坦途,友情能地久天长。
可如今……这莽莽苍苍的烟雨,不仅模糊了天地,也模糊了人心,将昔日的知己,隔绝在了两个再也无法相通的世界。
他缓缓从怀里掏出那对盘得油光锃亮的核桃,用力攥紧,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咯咯”的摩擦声,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在嘲笑他此刻内心的挣扎与伪善。
他知道,从今往后,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积累多少财富,临州城的这场雨,沈文谦那双平静的眼睛,都将如同梦魇一般,跟随他一生。
第七章 夜祭
夜色如墨,雨水依旧不知疲倦地敲打着沈府的一切。往日里廊下悬挂的气死风灯,今夜大多熄灭了,只有几盏在关键路口散发着昏惨惨的光晕,勉强照亮一小片湿漉漉的地面,反而更衬得整个府邸幽深莫测,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
沈文谦屏退了所有下人,独自一人,提着一盏小巧的玻璃风灯,踏着被雨水浸透的青苔小径,走向沈氏祠堂。风灯的光圈在黑暗中摇曳不定,只能照亮脚下几步远的范围,两侧的假山、树木在光影中投下幢幢鬼影,仿佛潜藏着无数沉默的注视。
祠堂位于沈府的最深处,是一座独立的、庄严肃穆的建筑。飞檐斗拱在夜雨中只剩下一个模糊而沉重的轮廓,像一头蛰伏的巨兽。他推开那扇沉重的、散发着柏木和香火混合气味的门扉,吱呀一声,在静夜中传得老远。
祠堂内,没有点灯,只有长明灯那一点如豆的火焰,在神龛前跳跃着,映照着层层牌位上镌刻的冰冷金字,忽明忽暗。那些沈家列祖列宗的名讳,在幽光下仿佛活了过来,一双双无形的眼睛,从历史的深处凝视着这个可能即将让家族蒙受大难的后人。
沈文谦将风灯放在供案旁,却没有立刻上香。他撩起长衫前襟,缓缓地、极其郑重地,在冰冷的蒲团上跪了下来。他没有磕头,只是挺直了脊梁,抬起头,目光逐一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牌位。
“列祖列宗在上,”他开口,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带着金属般的质感,却又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悲怆,“不肖子孙文谦,今夜于此,并非祈求宽宥,而是……禀明心迹。”
他的话语顿住了,似乎在积聚勇气,又像是在组织语言。长明灯的火焰跳动了一下,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时局维艰,豺狼环伺,临州城已如风中残烛。我沈家十数代心血,尽系于‘文脉’二字。书在,沈家在;书亡,沈家……魂亡。”他的声音提高了些许,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林慕云背信弃义,携资南遁,置临州万千乡梓于不顾。我沈文谦,无力回天,无法保全这一城百姓,唯有……竭尽所能,护住我沈家所守护的,华夏文明之一缕薪火。”
他仿佛能看到牌位之后,那些曾经同样在历史关头做出过抉择的先祖们,正静静地听着他的诉说。
“此行前路,凶险未卜。文谦已抱定‘城亡与亡’之志。若能侥幸,将部分珍本转移至安全之地,则沈家香火不绝,文脉得以延续,乃列祖列宗庇佑。若……若事不可为,文谦与书俱碎,亦无愧于心,无愧于沈家‘诗书传家’之祖训!”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已然哽咽,但眼神却亮得骇人,那是一种将个人生死、家族存亡都置之度外后,所产生的近乎狂热的光芒。他俯下身,额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砖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一下,两下,三下。
当他再次抬起头时,额上已是一片淤红。他站起身,从供案上取过三炷线香,就着长明灯点燃,恭敬地插入香炉之中。青烟笔直上升,在幽暗的祠堂里缭绕不散。
他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站着,像一尊雕塑,与这祠堂、与这雨夜、与那无数沉默的牌位,融为了一体。他在汲取力量,从祖先的荣光与坚守中,汲取与这座城、与这未卜命运抗争到底的勇气。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提起风灯,转身,步履坚定地走出了祠堂。当他重新融入外面的雨夜时,他的背影,仿佛比来时更加挺直,也更加孤独。
---
几乎在同一片夜色下,林家“蕴秀园”的“洗尘轩”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轩内灯火通明,精致的宫灯将每一个角落都照得亮如白昼。林慕云坐在主位,下手坐着林焕章、几位族老以及商会中心腹。桌上摆着几碟精致的点心和时令水果,但几乎无人动筷。气氛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他们正在做最后的确认。撤离的路线、船队的编组、沿途可能遇到的盘查与危险、到达目的地后的安置与生意重启计划……每一项都被反复推敲,确保万无一失。
林焕章显得成竹在胸,条理清晰地向众人汇报着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他的声音自信而有力,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锐气,仿佛不是在进行一次悲壮的逃亡,而是在开启一场伟大的远征。
几位族老和心腹不时点头,脸上露出赞许和依赖的神情。在这种时候,一个果断、有能力的继承人,无疑能给惶惑的人心带来极大的安慰。
唯有林慕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听着儿子的汇报,目光却不时飘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黄花梨木椅扶手上敲击着,节奏杂乱。
他仿佛能穿透这无尽的雨幕,看到沈府祠堂里,沈文谦那孤绝跪拜的身影。他能感受到那种与城共存亡的悲壮,更能感受到那种被挚友、被同道抛弃的苍凉。
“父亲,”林焕章汇报完毕,见父亲神色恍惚,不由得出声提醒,“您看……还有何需要补充?”
林慕云回过神来,收敛了心神,脸上恢复了一家之主的沉稳:“嗯,安排得很周详。只是……记住,明日凌晨出发之时,一切动作务必要轻,要快。不要惊动太多人。”
“父亲放心,码头那边已经打点妥当,绝不会走漏风声。”林焕章保证道。
一位族老叹了口气,语气复杂:“说起来,沈家……真是可惜了。文谦兄何等人物,竟要……”
他的话没说完,但在座的人都明白那未尽之意。一种微妙的、混合着庆幸、惋惜和一丝负罪感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林慕云的脸色微微一沉,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那苦涩的滋味一直从舌尖蔓延到心底。
“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他放下茶杯,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我林家,首先要对得起跟着我们的这几百口人。”
他的话,为这场最后的会议定下了基调,也为他内心的挣扎画上了一个强制性的句号。
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回到书房,看着这间即将被永远抛在身后的、承载了他大半生记忆的房间时,那种空虚和负疚感,再次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走到书案前,摊开一张宣纸,想写点什么,留给这座城,或者留给沈文谦。但提起笔,悬腕良久,脑海中万千思绪翻滚,却一个字也落不下去。
最终,他颓然掷笔,那支上好的狼毫笔滚落在地,溅开几点墨痕,像一声无声的叹息,也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他知道,有些裂痕,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弥合。有些路,一旦踏上,便再也无法回头。
这莽苍苍的雨夜,见证着一场无声的诀别。一边是祠堂里的孤影,誓与文明共存亡;一边是华轩中的密议,只为家族谋生存。忠义与存续,在这末世的风雨里,被撕裂成无法两全的悲歌。
第八章 断缆
第三天,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雨,竟然奇迹般地变小了,从之前的倾盆之势,转为了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笼罩着尚在沉睡中的临州城。空气里弥漫着破晓前特有的清冷和潮湿,一种不安的宁静悬浮在城市上空。
林家“蕴秀园”的后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一长溜黑影鱼贯而出。没有灯笼,没有喧哗,只有车轮碾过湿滑石板的细微声响,和人们压抑到极致的呼吸声。林慕云穿着一件深色的普通棉袍,外面罩着蓑衣,站在门边的阴影里,默默地看着家人和重要的心腹、技师及其家小,在林焕章低声而迅速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地登上一辆辆早已准备好的、卸去了所有标识的马车。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或惶恐、或茫然、或带着一丝逃离兴奋的脸孔,最后落在儿子林焕章那年轻而坚毅的侧影上。焕章做得很好,比他想象中更好,果断、周密,临危不乱。林家交到他手上,或许真的能在那陌生的南方闯出一片新天地。这让他感到一丝欣慰,但旋即又被更深的空虚所取代。
当最后一名人员登上马车,林焕章快步走到他面前,低声道:“父亲,都齐了,可以出发了。”
林慕云点了点头,最后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在黎明前的微光中只剩下一个庞大轮廓的“蕴秀园”。那飞檐斗拱,那亭台楼阁,那他曾耗费无数心血经营打造的家……从此,便只是记忆里的一个幻影了。
他毅然转身,钻入了为首的一辆马车。车帘落下,隔绝了视线。
马车队如同幽灵般,在寂静无人的街巷中穿行,朝着码头方向疾驰而去。
---
几乎在同一时刻,沈府的后角门也悄然开启。
这里的气氛,与林家的高效有序截然不同,更显出一种悲壮的凝重。十几辆粗陋的骡车、板车静静地停在雨中,车夫们都是沈家多年的佃户或可靠的老仆,个个面色沉郁。沈文谦和沈知白站在门内,看着下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最后几只包裹着厚厚油布的书箱抬上车,用绳索死死固定。
每一个书箱被抬出,沈文谦都觉得自己的心被剜去了一块。那里面,是他和儿子、老仆们不眠不休数日,从十万藏书中甄选出的最精华部分,是沈家的魂,是他宁愿付出生命也要守护的东西。而更多的、无法带走的书籍,已被秘密封存在加固后的地窖之中。那是无奈的舍弃,是每当想起便心如刀绞的遗憾。
沈府的女眷和孩子们,也都换上了粗布衣衫,默默地站在廊下等候,脸上带着惊惧与不舍。他们不知道前路如何,只知道要离开这个世代居住的家,踏上一条吉凶未卜的旅程。
“父亲,都装车完毕了。”沈知白走到沈文谦身边,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因紧张和疲惫而沙哑。
沈文谦点了点头,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沉声道:“出发。”
没有更多的言语,队伍在细雨中,悄无声息地开拔了。沈文谦走在最后,他亲手关上了那扇沉重的后角门,落锁。那“咔哒”一声,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
临州城码头。
黎明前的微光勉强穿透雨雾,勾勒出停泊在岸边那支庞大船队的轮廓。林家的船队,帆樯如林,在灰蒙蒙的水面上显得气势恢宏。先期到达的人员和物资早已登船,林慕云所在的马车队抵达后,最后一批核心人员也开始迅速而安静地登船。
林慕云站在主船的甲板上,蓑衣上的雨水汇成细流,滴落在脚边。他望着不远处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的临州城城墙,心中百感交集。这座城,给予了他财富和地位,如今,他却要弃它而去。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猛地一凝。
在码头另一侧较为偏僻的角落,隐约出现了一队人马,十几辆骡车,几十个身影,正在雨中艰难地试图将一些沉重的箱子搬上几艘看起来十分破旧的小型货船和改装过的渔船。那是……沈家的人!
他们果然来了!他们果然找到了船!尽管那些船看起来如此不堪,与林家这支装备精良的船队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林慕云的心脏骤然缩紧。他看到沈文谦那清瘦的身影,正站在岸边指挥着,即使隔着这样的距离和雨幕,他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人身上散发出的那股义无反顾的决绝。
“父亲,所有人都已登船,可以起锚了。”林焕章走到他身边报告,顺着父亲的目光,他也看到了沈家那支渺小而狼狈的队伍,嘴角不由撇了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林慕云没有理会儿子的话。他的内心在进行着最后的、天人交战的挣扎。只要他一声令下,或许可以分出一两条船,搭载上沈家和他们的书箱……但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船位已然紧张,路途凶险未知,带上沈家这个“包袱”,会极大地增加整个船队的风险,甚至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
利弊,利弊!他的一生都在权衡利弊!可此刻,他痛恨这该死的权衡!
“父亲?”林焕章见父亲久久不语,再次催促。
林慕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冰冷潮湿的空气,再睁开时,眼中已是一片冰冷的清明。
“断缆,启航。”他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块寒冰,砸在甲板上。
“断缆!启航!”林焕章立刻高声传令。
嘹亮的号子声响起,沉重的铁锚被绞起,缆绳被砍断,巨大的船帆在桅杆上缓缓升起,吃住了风。
林家船队,如同一条苏醒的巨龙,开始缓缓移动,驶离码头,驶向宽阔而迷茫的江心。
---
沈文谦站在冰冷的雨水中,看着林家那支庞大的船队,毫不留恋地、以一种近乎优雅的姿态,斩断与这座城市最后的联系,驶向远方。船队经过他们这小小的、挣扎求存的队伍旁边时,甚至没有一丝停顿,仿佛他们只是岸边无关紧要的蝼蚁。
他看到了主船甲板上,那个穿着蓑衣的熟悉身影。隔着雨雾,他看不清林慕云的表情,但他能感觉到那道投射过来的目光。那目光,或许有复杂,有歉疚,但最终,是冰冷的背离。
他没有愤怒,也没有呼喊,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冰凉的雨水顺着脸颊滑落,与那或许存在的温热液体混合在一起。
“父亲……”沈知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愤懑和绝望。
沈文谦抬起手,阻止了儿子后面的话。他的目光从远去的船队收回,落在了眼前这几艘破旧、但却承载着他们全部希望的船只上。
“上船。”他只说了两个字,声音平静得可怕。
他率先踏上了那艘最大的、看起来也最不牢靠的货船。船身在脚下微微摇晃,像这动荡的时局。
当最后一只书箱被艰难地挪上船,当沈家所有人都登上这狭窄而拥挤的船舱,船工们开始解缆、撑篙。
小小的船队,像几片无力的落叶,歪歪斜斜地,驶离了岸边,驶入了那莽莽苍苍、前途未卜的江雨之中。
身后,是渐渐远去的、沉睡的临州城。
前方,是迷雾笼罩的、命运的洪流。
两条船,两个方向,两种抉择,在这黎明时分,在这苍茫江雨之中,彻底分道扬镳。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奖。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