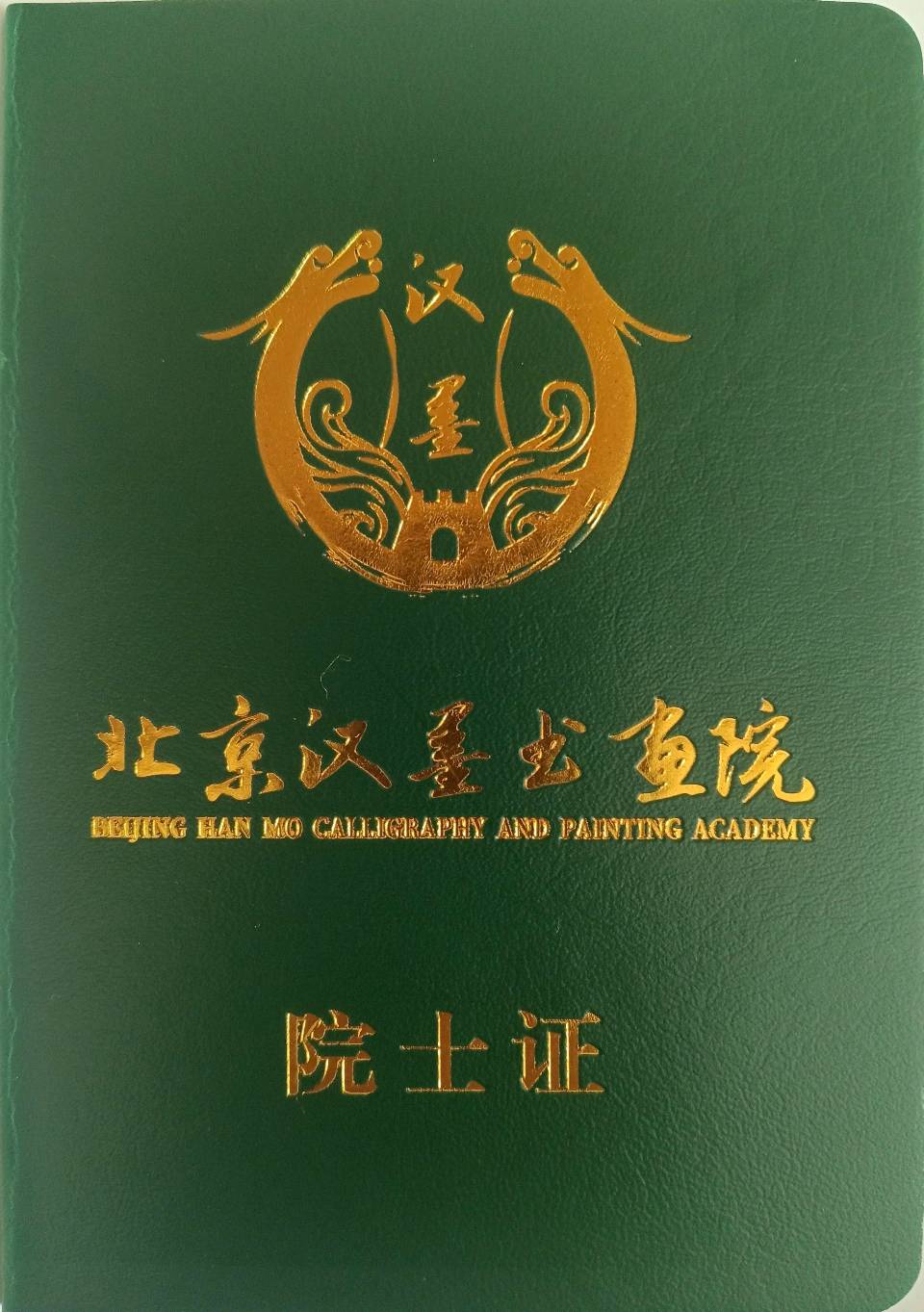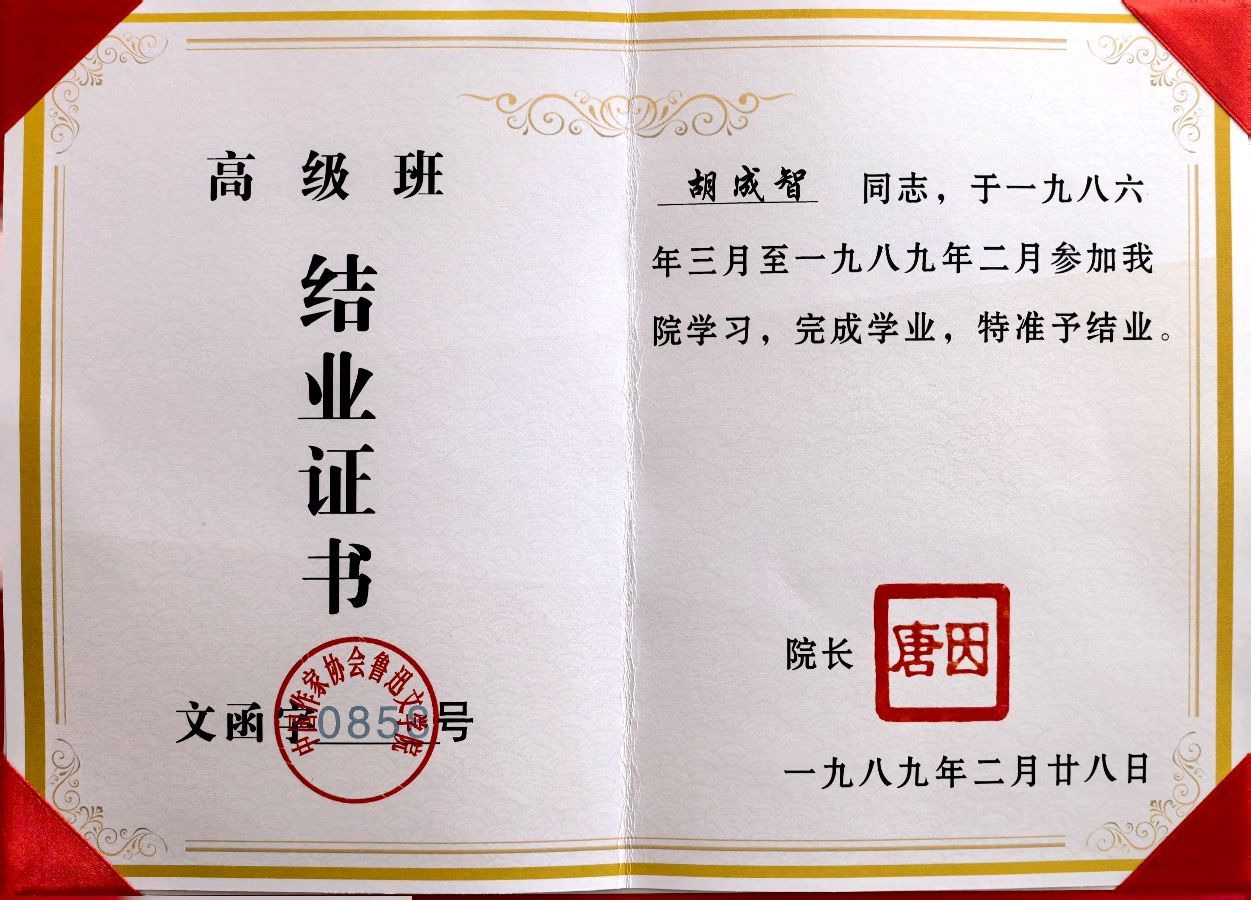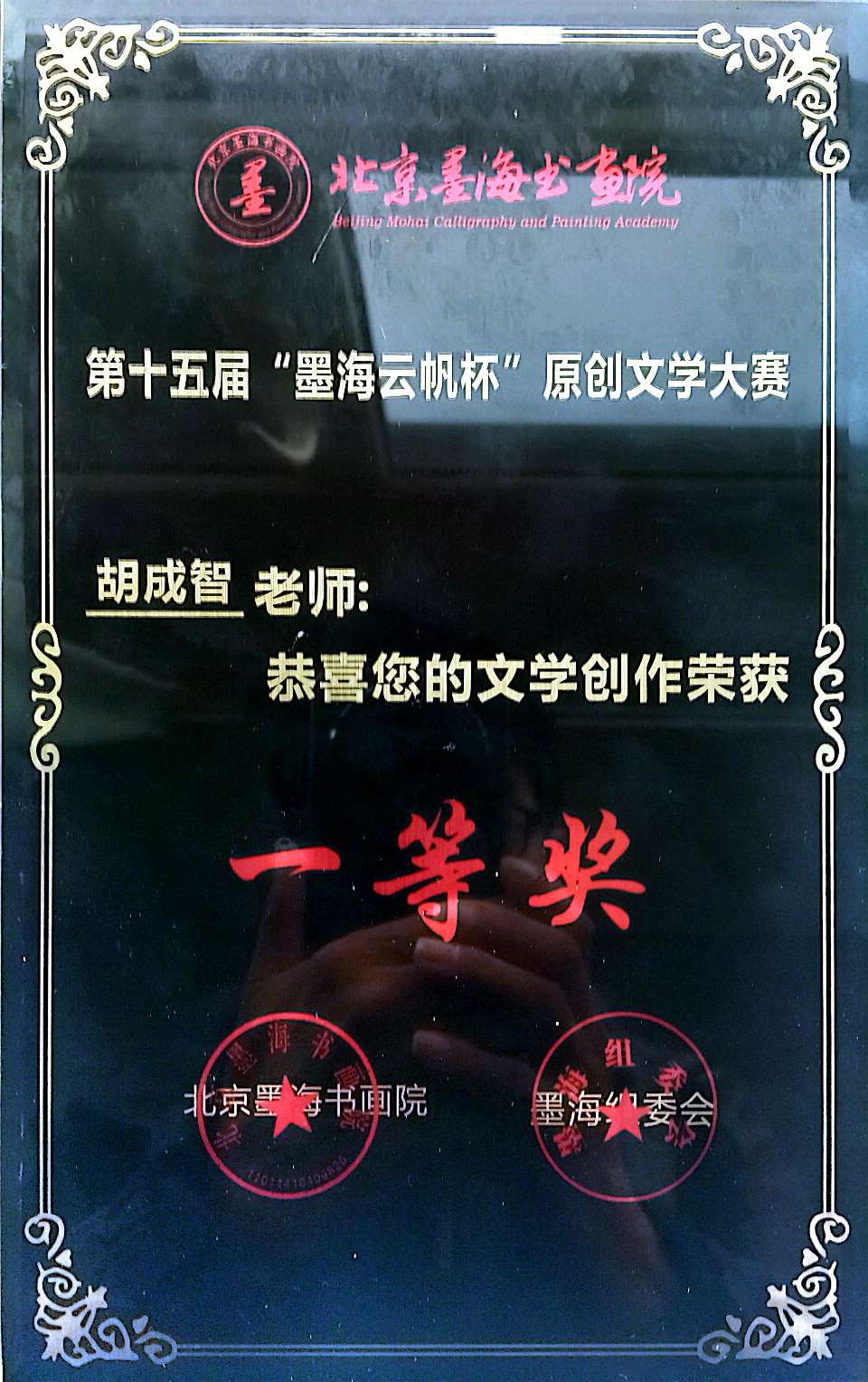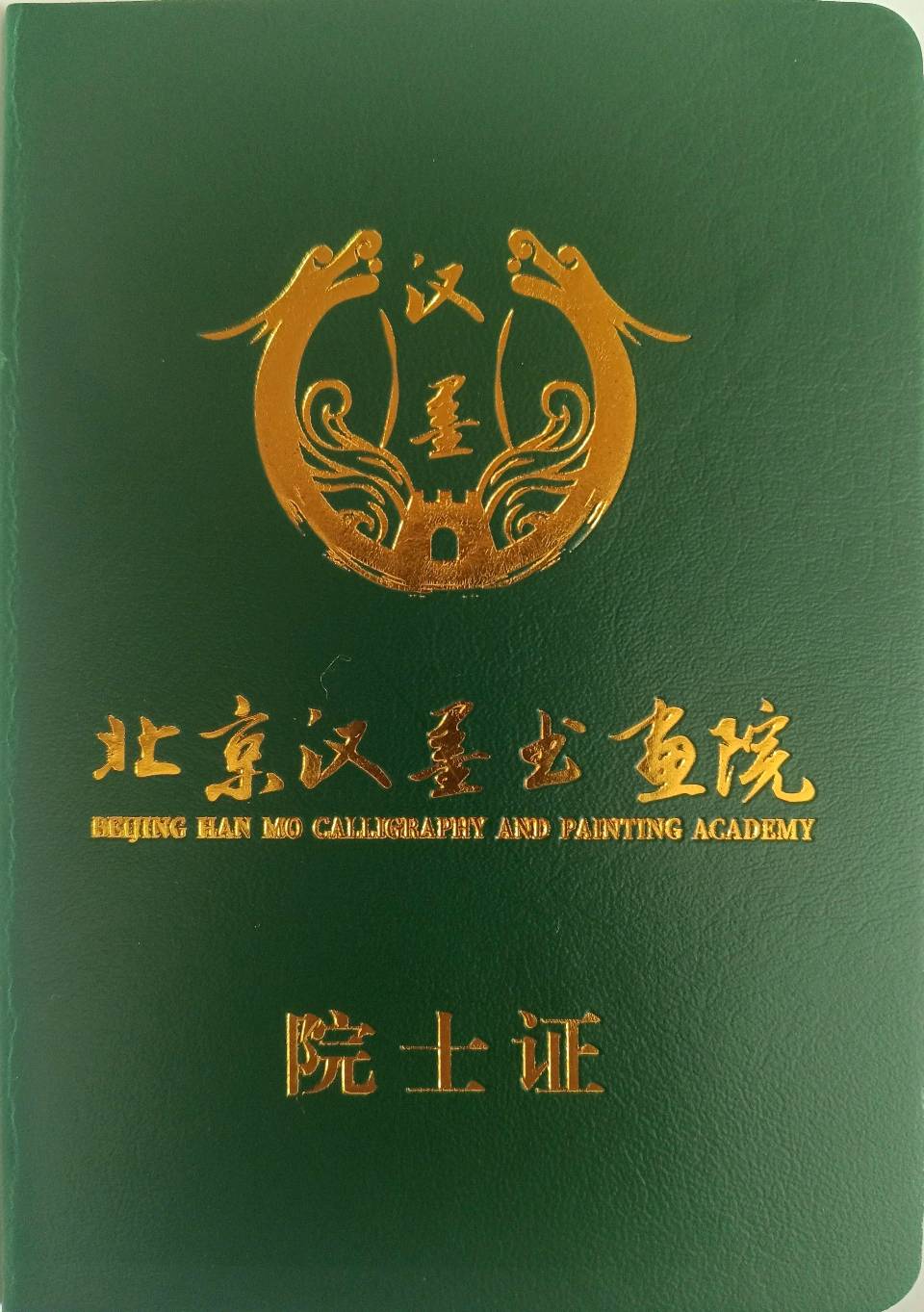第四十九章 回音
等待的弦在料峭春寒中绷紧到了第十五天,终于被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拨动了。信封依旧是那个朴素的白色,右下角印着“历史研究所”的红色宋体字,像一枚冰冷的官方印章。
苏姨拿着信快步走进书房时,芷蘅正对着一幅父亲与友人在西湖边的旧照出神。照片上的父亲穿着浅色长衫,戴着眼镜,笑容温煦,背景是潋滟的湖光和堤岸垂柳,那是另一个时空的、尚未被风雨侵蚀的宁静。听到脚步声,她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苏姨手中那封信上,瞳孔几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
“阿蘅,北京的回信。”苏姨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紧张,将信递过去。
芷蘅放下照片,接过信。指尖触碰到纸张,依旧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冰凉。她没有立刻拆开,只是用手指摩挲着信封上打印的地址,仿佛在掂量其内容的分量。窗外,细雨又开始飘洒,敲打着玻璃,发出细碎而持续的声响,像是在为这关键时刻伴奏。
她终于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信封,取出了里面的信笺。依旧是印着单位抬头的公文纸,但内容不再是打印体,而是手写的钢笔字,笔迹端正有力,带着一种审慎的克制。
“沈芷蘅女士:
惠函收悉,迟复为歉。
您主动提出整理沈允之先生生平材料,对此我们深表感谢。这充分体现了您对历史研究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沈允之先生作为与顾长明先生关系密切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其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确实对全面理解顾长明个案及其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我们非常欢迎您能从这个角度提供相关资料。”
看到这里,芷蘅的心微微沉了一下。对方敏锐地抓住了她信中的意图,并明确将其定位为“理解顾长明个案”的“参照”。他们关注的焦点,依然牢牢锁定在顾长明身上。父亲,在他们眼中,似乎始终是那个主要研究对象的附庸和背景板。
她继续往下看:
“关于材料形式,您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处理。或为书面回忆,或辅以旧物照片之说明,皆无不可。唯望内容能尽可能客观详实,尤其涉及沈允之先生与顾长明先生交往之具体细节,以及其在特定历史关头之真实想法与处境,对我所研究至关重要。”
信的最后,是赵怀明熟悉的签名,比打印的字体多了几分人间的痕迹,却依然带着官方的距离感。
没有催促,没有强制,甚至语气比上次来访时更为客气。但字里行间那种对“客观详实”、“具体细节”、“真实想法”的强调,却像一张无形而坚韧的网,悄然收紧。他们同意了她“整理材料”的提议,却也将评判“价值”的标准,明确地指向了那些她最不愿轻易示人的、与顾长明直接相关的、充满痛苦和挣扎的“细节”与“真实”。
这封回信,像一场高手过招中的绵密应手,看似接受了她的提议,实则将她拉入了一个更深的、由对方设定规则的场域。
芷蘅缓缓将信纸放下,目光再次投向窗外迷蒙的雨景。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淌,扭曲了外面的世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不是身体的,而是源于这种与一个庞大而无形的体系周旋时,那种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第五十章 织锦
既然棋局已开,便没有回头的余地。
沈芷蘅开始了她承诺的“材料整理”工作。这并非一项简单的回忆录撰写,而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文字战役。她必须像一位最谨慎的织工,在历史的经纬线上,小心翼翼地穿梭,既要呈现出父亲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完整性与尊严,又要避免触及那些可能被研究所过度解读或利用的、过于私密和疼痛的神经。
她在书房里开辟了一个专门的角落,将父亲的照片、手札、印章、那本行医杂录,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家信( carefully selected, 避开了所有提及敏感时局和人物的内容)分门别类摆放。她铺开一叠全新的稿纸,拿起那支父亲常用的、笔尖较粗的黑色钢笔——这一次,她决定用父亲的笔,来书写关于父亲的记忆。
落笔的第一个字,重若千钧。
她先从父亲的家世和早年求学经历写起,用平静而克制的笔调,描述祖父开明敦厚,父亲自幼聪颖,深受传统典籍熏陶,后又接受新式教育,立志悬壶济世。她写到父亲如何潜心医术,如何对待病人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如何在家中开设小小的义诊,帮助那些无力求医的街坊。她引用父亲杂录中的片段,展现他对医道的理解与追求:“医者,父母心。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她试图勾勒出一个仁厚、敬业、深受邻里敬重的儒医形象。
然后,她谨慎地触及父亲与顾长明的交往。她将其描述为一种纯粹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强调父亲是欣赏顾长明的聪慧与求知欲,才对他多有指点,并因他出身寒微而给予生活上的些许关照。她刻意淡化了顾长明后期那些激烈言论和活动对父亲造成的冲击与困扰,只含糊地写道:“……然时局嬗变,少年人意气风发,所思所想,与父辈渐生隔阂。先父感其才,亦忧其行,常怀惴惴。”
写到父亲晚年,是最为艰难的部分。她不能回避父亲的消沉与谨慎,但必须为其赋予合乎情理且不至于损害其根本形象的解读。她着重描写父亲对家人的深沉关爱,以及他将全部精力转向医术钻研和培养后辈(尽管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传人)的“消极”坚守。她写道:“……先父晚年,愈发沉默,常独坐书房,或翻阅医籍,或凝视旧物。外界喧嚣,似已与之无关。然其对病患之关切未尝稍减,于医术之求精更臻化境。或可谓,其将未尽之理想与热情,尽数倾注于斯,以此守护内心一方净土,亦是对纷乱时局一种无言之应对。”
她像修复一件珍贵的、却已破碎的瓷器,用最细腻的笔触,小心翼翼地填补着裂缝,试图还原其原本的温润光泽,而将有碍观瞻的、尖锐的碎裂痕迹,巧妙地隐藏在修复材料的纹理之下。
这个过程,缓慢而耗神。常常写不了几行,便要停下来长时间地思索,反复推敲用词,权衡利弊。有时,她会因为成功地找到一个既能表达事实、又不至于授人以柄的措辞而微微松一口气;有时,则会因某个无法回避的痛点而陷入长久的凝滞,笔尖悬在纸面上,久久无法落下。
织锦不易,尤其是要用语言的丝线,去织就一幅既能保护逝者尊严、又能应对外部审视的、完美无瑕的图景。
第五十一章 影武者
在沈芷蘅埋首于“织锦”工程的同时,那个名叫顾知行的身影,并未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他像一个沉默的影武者,虽未直接现身,其存在感却通过种种方式,悄然施加着影响。
首先是他留下的那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它依旧放在书桌上那堆遗物的最上面,深蓝色的布面封面,像一个幽深的、无法忽视的注脚。芷蘅在整理材料感到疲惫或困顿时,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上面。她始终没有勇气再次翻开它,去看那幅侧影画和那两个“是你?”的字。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质询,提醒着她那段无法被完全纳入她正在编织的、理性图景中的、带着青春体温与情感悸动的过往。
其次,是关于研究所动向的零星信息。一天,苏姨从菜市场回来,有些犹豫地告诉芷蘅,她听一个同样家里有亲戚在文化单位工作的邻居说起,历史研究所最近好像确实在搞一个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专题,动静不小,还从下面调阅了不少旧档案。
这个消息,让芷蘅握着笔的手停顿了许久。她意识到,顾知行和他所在的课题组,正在以一种她无法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从各个渠道搜集着与顾长明、甚至可能与沈家相关的材料。她在这里字斟句酌地编织着关于父亲的“保护性叙述”,而对方可能早已掌握了更多、更原始、甚至可能对她不利的档案证据。她的“织锦”,在对方庞大的史料挖掘面前,会不会显得苍白而可笑?
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带来了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焦虑。她感觉自己像是在一间透明的玻璃屋里劳作,自以为隐秘,殊不知屋外早有无数双眼睛在审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最后,也是最具冲击力的,是大约在回信寄出十天后的一个下午,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署名顾知行的私人信件。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字迹是他那特有的瘦硬挺拔的风格。芷蘅拆开信,里面只有薄薄一页纸,内容同样简短:
“沈女士:
冒昧致函。近日查阅旧档,偶见一份一九六五年华东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动态汇总简报(内部参考),其中提及令尊沈允之先生曾于某次非正式座谈中,就‘历史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发表看法,认为对传统医学之精华不宜全盘否定,其言恳切,留有记录。
此事或可为理解沈先生当时立场与心态提供一佐证。
另,研究所资料室存有部分当年相关报刊,若您整理材料时需要核实某些时间节点或事件背景,我可代为查阅。
顾知行
某年某月某日”
这封信,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瞬间打乱了芷蘅所有的节奏。
顾知行没有催促,没有质疑,甚至提供了一条看似有益的“佐证”和一个“帮忙”的提议。但芷蘅却从中读出了更多的东西:他在向她展示他的“武器库”——他掌握着她所不知道的、关于父亲的官方记录;他在暗示,他了解她正在进行的“材料整理”工作;他以一种看似友善的姿态,提醒着她,历史的“真相”是多维的,并非完全由她个人的回忆所定义。
这是一种温和的,却更具压迫感的提醒。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并不急于收网,只是不时地展示一下手中的猎具,让猎物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芷蘅拿着这封信,在书房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暮色四合,苏姨进来点灯。
织锦尚未完成,而影武者的刀锋,已经悄无声息地抵近了后心。
第五十二章 孤灯
顾知行的来信,像一块冰冷的巨石投入沈芷蘅的心湖,打破了她在“织锦”过程中勉强维持的、脆弱的平静。那种被窥视、被评估、甚至被某种程度“怜悯”的感觉,让她感到屈辱,也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位置的险恶。
她将顾知行的信折叠好,没有回复,也没有扔掉,只是将其塞进了那叠正在撰写的“材料”底下,像一个必须面对却不愿多看的疮疤。然后,她重新拿起笔,继续她那未完成的织锦工作。只是,笔下的文字,似乎比之前更加沉重,更加小心翼翼了。
夜色渐深,细雨不知何时又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敲打着书房朝北的窗户。苏姨早已睡下,整栋房子寂静无声,只有书房这一盏孤灯,在雨夜里散发着昏黄而执拗的光晕。
芷蘅伏在案前,稿纸上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她正在撰写关于父亲晚年心境的部分,这是整篇“材料”最核心、也最难把握的段落。她必须解释父亲的沉默与谨慎,又不能将其归因于对某个具体事件或人物的恐惧;她必须承认父亲的痛苦,又不能渲染其悔恨与无力感。
她写写停停,不时抬起头,望向窗外无边的黑暗。雨丝在玻璃上划出无数道细密的、冰冷的痕迹,像极了岁月在她心上刻下的、无法磨灭的皱纹。父亲的形象,顾长明的身影,研究所的压力,顾知行那双深邃而冷静的眼睛……所有这些,都在她的脑海中交织、碰撞。
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孤独,并非源于身边无人,而是源于一种精神上的绝对隔绝。无人可以分担这份守护往事、与庞大体系周旋的重负;无人可以真正理解她此刻在字斟句酌间所耗费的心力与所承受的煎熬。
她放下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眶。目光落在桌角那本深蓝色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上。鬼使神差地,她伸出手,第一次主动地、缓慢地翻开了它。
直接翻到那幅衬页。
铅笔素描的侧影,在昏黄的灯光下,线条显得更加柔和,也更加脆弱。旁边那两个“是你?”的字,墨色浅淡,却像拥有生命一般,直直地撞入她的心底。
这一次,她没有感到惊慌或刺痛,反而有一种奇异的、近乎麻木的平静。她伸出手指,极其轻柔地抚过那铅笔的线条,仿佛隔着数十年的时光,触摸着那个下午图书馆里,那个年轻人偶尔投来的、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明了用意的目光。
那目光里,是否有过一丝类似于她此刻所感受到的孤独?
两个孤独的灵魂,在时代的洪流中短暂交汇,却最终被冲向不同的、布满礁石的彼岸。
她轻轻合上诗集,将其放回原处。
然后,她重新拿起笔,深吸一口气,在稿纸上继续写道:
“……先父晚年,常言‘但求问心无愧,俯仰天地’。其内心或有波澜,然对外始终保持着一位传统士大夫的沉静与克制。这种沉静,非是麻木,亦非怯懦,乃是在无力改变之大环境下,对自身道德底线与专业操守的最后坚守,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之另一种姿态……”
孤灯下,笔尖沙沙作响。
一个女儿,正在用尽全部的智慧与情感,为她风干在岁月里的父亲,做最后、也是最艰难的辩护。
雨,还在下着。长夜漫漫。
---
(第三卷 尘封的标本,待续)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奖。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