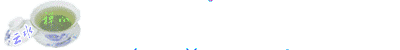苹 果 香
作者:张龙才
红嘴雁划过天际,翅膀下是绵延的芦苇荡,风一吹,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向远方。阿依波力勒紧马缰,立在坡上,望着那条蜿蜒的河流。河对面,就是记忆中的夏牧场,那片白色的毡房星星点点,像散落的珍珠。
“莎吾烈泰……”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舌尖仿佛尝到了青草的涩,又泛起了苹果的甜。这么多年,他浪迹天涯,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再到更远的南方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梦里萦绕不散的,总是这片草原的气息,和那缕抓不住的苹果香。
他是归乡的游子,也是怯懦的逃兵。故乡,在记忆里被镀上了金光,却又近乡情怯,怕它已不是旧时模样。
马蹄嘚嘚,踏过熟悉的草坡,那条饮马的小河依旧清澈见底。他仿佛又看到许多年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十八岁的少年,骑着心爱的枣红马,踏着夕阳的余晖,来到河对岸那片白色的毡房前。
那天,他是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叼羊比赛做准备,提前来勘探场地。河水凉丝丝的,漫过马腿,也驱散了他的疲惫。就在他准备牵马离开时,一阵悠扬的冬布拉琴声随风飘来,夹杂着清亮婉转的歌声。
那歌声,像天山融化的雪水,清冽地淌过心田;又像初夏的风,拂过盛开的苹果花。他循声望去,看见不远处一座洁白的毡房前,坐着一个姑娘。她穿着艾德莱斯绸的裙子,头上戴着一顶绣花小帽,帽檐上插着一根漂亮的羽毛,随着她拨动琴弦的动作,轻轻颤动着。
晚风调皮,拂动着那根羽毛,也拂动了少年阿依波力的心。他看得呆了,忘了时间,忘了周遭的一切。那姑娘偶尔抬起头,目光与他相遇,没有惊慌,只是微微一笑,嘴角漾起浅浅的梨涡,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她的歌唱。
那就是莎吾烈泰,河对岸最明亮的星星。
那个晚上,部落里恰好有聚会。人们燃起篝火,烤着羊肉,喝着马奶酒。阿依波力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而他所有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莎吾烈泰身上。她不再是独自弹唱的少女,而是人群中的焦点,她跳舞,她歌唱,她眼眸亮如星辰。
单纯的相逢,在那个平凡的晚上,变得无比瑰丽。阿依波力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碗马奶酒,只记得心跳比手鼓的节奏还要快。他不敢上前搭话,只是躲在人群的阴影里,贪婪地看着她,听着她。
夜深了,篝火渐熄,人们陆续回到自己的毡房。阿依波力却毫无睡意。他躺在分配给客人的毡房里,耳朵却竖着,捕捉着外面的一切声响。虫鸣,风声,还有……隐约似乎还能听到那美妙的歌声在回荡。他知道那是幻觉,却心甘情愿地沉溺。
他起身,悄悄走出毡房。草原的夜晚,天空是深蓝色的丝绒,月亮又大又圆,清辉遍地,将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梦幻的银纱。他鬼使神差地走到莎吾烈泰家的毡房附近,看到她毡房外的拴马桩上,挂着她那顶帽子,那根羽毛在月光下,像被镀上了一层银边,随着晚风,轻轻地,一下一下地飘啊飘。
那一刻,月亮作证,那根羽毛仿佛不是飘在风里,而是飘进了他的心里,轻轻地,痒痒地,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记。
他就那样,在毡房外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傻傻地,看着那顶帽子,等到了天亮。直到东方既白,草原上泛起乳白色的晨雾,他才惊觉自己竟坐了一夜。露水打湿了他的衣襟,心里却是一片滚烫。
那次相遇之后,阿依波力的魂就丢在了河对岸。比赛结束后,他找各种借口往返于自家的牧场和河对岸。他知道了莎吾烈泰喜欢在清晨去挤牛奶,知道了她每周会去一次六星街,用自家做的奶酪换些针线和书本。
六星街,那是伊宁城里他另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六星街里还传来巴扬琴声吗?”阿依波力驱马前行,离开河边,向着城镇的方向走去。越是靠近,记忆的闸门就越是汹涌。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六星街的奶奶家度过的。那由六条射线般的街道汇聚成的中心区域,是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充满了异域风情和鲜活的生活气息。
他总是能听到手风琴——我们叫它巴扬——的声音,从某个院落里飘出来,欢快又略带忧伤的旋律,伴随着手鼓的节奏。循着琴声,往往就能找到聚会的人们,无论认识与否,你都可以加入进去,跳一支舞,喝一杯格瓦斯。
阿力克桑德爷爷的面包房,永远散发着诱人的麦香。那个大胡子的俄罗斯老人,总是系着白色的围裙,笑容和蔼。他的列巴,外皮硬脆,内里柔软,带着啤酒花的微酸和麦芽的甜香,是阿依波力童年最顶级的美味。每当下午列巴出炉的钟声敲响,孩子们便会像听到集结号一样冲向面包房。阿依波力总会用奶奶给的零钱,买上一个热乎乎的列巴,一边烫得直吹气,一边迫不及待地掰开,和伙伴们分食。
还有南苑卤香。那家由一对四川夫妻开的小小卤味店,是舌尖上的传奇。红色的招牌,玻璃橱窗里摆着油光发亮的卤鸡、卤鸭、卤牛肉、卤豆干、卤藕片……那股混合了数十种香料的复杂卤香,能飘出半条街,霸道地钻进每一个路过行人的鼻腔,勾起最原始的馋虫。对阿依波力来说,那卤味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故事。四川夫妻会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来往的客人也有各自的故事,他和小伙伴们就趴在柜台边,一边啃着卤鸡翅,一边听着天南海北的奇闻异事。
“你让浪迹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阿依波力喃喃自语,喉头有些发紧。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构成了故乡的筋骨和血肉,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复制的味觉和听觉记忆。
他的思绪又飘向了更久远的童年。奶奶家那个湖蓝色的院落围墙,是他整个世界的边界。
“儿时的万花筒里,有野鸽在飞翔。”他想起二哥,那个比他大五岁,调皮捣蛋却又无比疼爱他的哥哥。二哥是制作弹弓叉的高手,会用粗壮的树杈和医院废弃的输液管,做成威力巨大的弹弓。他们常常爬上湖蓝色的院墙,瞄准院子里枣树上啄食的野鸽子。二哥很少真的打中,更多的是享受那种瞄准和发射的过程。阳光透过万花筒,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斑,野鸽子扑棱棱飞起,掠过湛蓝的天空。那些无所事事的下午,缓慢,悠长,充满了简单的快乐。
而那个湖蓝色的院落,更是他生命的摇篮,是母爱的象征。他的妈妈,一位温柔而坚韧的哈萨克妇女,总是在那里忙碌着。在葡萄架下为他缝补磨破的裤子,在院子里用巨大的铜壶烧水给他洗澡,在冬夜里搂着他,给他讲古老的传说和歌谣。妈妈的爱,像院墙那样坚实,包容着他的一切,给予他最初的安全感和面对世界的勇气。
“我的妈妈在那里给我的爱,叫我永生不忘啊。”阿依波力深吸一口气,仿佛还能闻到妈妈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了奶香和阳光的味道。
可是,儿时的他,并不懂得珍惜这份安稳。他向往着远方,向往着歌词里唱的“浪迹天涯”。十六岁那年,父亲因为工作的调动,要举家迁往乌鲁木齐。对于少年阿依波力来说,那不是离愁,而是兴奋,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
离开的那天,正是初夏,院子里父亲亲手栽种的苹果树开花了,粉白的花朵簇拥在枝头,香气馥郁,几乎笼罩了整个院落。妈妈红着眼眶,往他的行囊里塞着自家做的包尔萨克和奶疙瘩。二哥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说:“臭小子,到了大城市别忘了我!”
他当时满心欢喜,哪里体会得到离别的伤感。他甚至觉得,故乡太小,太一成不变,他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马车驶出湖蓝色的院落,驶过六星街,巴扬琴声、列巴的香气、南苑卤香……都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他回头,看到妈妈还站在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和那片苹果花的云雾,一起模糊在视野的尽头。
“儿时离开你,正逢花开时。”
如今,他真的浪迹了天涯,看过了世界的广阔与繁华,也尝遍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孤独。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在觥筹交错的应酬之后,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感到窒息的时候,故乡的一切,便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草原的辽阔,河谷的静谧,六星街的喧嚣,还有……院子里那棵苹果树的花香。这些意象,反复咀嚼,最终都化成了他心底的歌。他在南方的酒吧里驻唱,唱流行,唱摇滚,但每次安可曲,他总会固执地唱起自己写的关于草原、关于故乡的歌。台下的人们或许听不懂哈萨克语,但那旋律里的思念,总能引起一些共鸣。
可是,唱得越多,思乡的病就越是沉重。他终于明白,无论他走了多远,飞了多高,根系,始终牢牢地扎在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这次回来,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是回来看看,更是想寻找一些东西,弥补一些遗憾。最重要的,是关于莎吾烈泰的。
那年夏天之后,他们有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一起骑马,一起放羊,他教她弹吉他,她教他唱更古老的哈萨克民谣。在苹果树下,他第一次笨拙地牵了她的手;在月光如水的夜晚,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吻了她的额头。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秋天,他收到了乌鲁木齐一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提前为他办理了迁居和转学)。离别来得猝不及防。
他记得那天,他去找莎吾烈泰告别。还是在河边,芦苇已经枯黄。她听完他的话,沉默了许久,然后抬起头,脸上依然是初见时那样明亮的笑容,只是眼底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
“去吧,阿依波力。你应该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他手里,“这个给你,想家了,就看看。”
他打开,是一把干枯的苹果花,虽然失去了水分和色泽,但依稀还能闻到一丝残存的香气。
他走了,带着那把苹果花和满腔的离愁。起初,他们还通信,信纸上是滚烫的思念和对新生活的分享。但渐渐地,距离拉长了等待,不同的生活环境让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他的信越来越短,她的回信也越来越慢。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她最后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语:“阿依波力,不要再写信了。我阿爸给我定了亲,是隔壁牧场的一个小伙子。祝你前程似锦。”
那一刻,他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把那封信和那把早已碎成粉末的苹果花,一起锁进了箱子的最底层。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适应新生活中,试图用忙碌来忘记那份钝痛。
“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是的,往事的确远了,模糊了。莎吾烈泰具体的容貌,在记忆里已经有些朦胧,但那种心动的感觉,那个月光下的夜晚,那缕苹果的香气,却清晰地刻在了灵魂里,成为他乡愁中最柔软、也最疼痛的一部分。
这次回来,他想知道,她过得好吗?那个当年“定了亲”的小伙子,对她好吗?他还想看看,那片草原,那条河,那座叫做六星街的地方,是否依然如故?
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阿依波力终于走进了伊宁城,走进了六星街。
熟悉的街道布局,但两旁的建筑或多或少都有了变化。一些老旧的木屋被拆除了,盖起了崭新的砖房;一些传统的店铺不见了,换成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他的心微微一沉。
他循着记忆中的路线,慢慢走着。突然,一阵熟悉的巴扬琴声传来,精神为之一振!他快步走过去,发现声音是从一个院子里传出来的。院门开着,他探头望去,只见几个老人坐在葡萄架下,一个头发花白的俄罗斯族老人正闭着眼睛,陶醉地拉着手风琴,琴声依旧欢快而悠扬。
还好,有些东西还没变。
他又走向阿力克桑德面包房的位置。还好,面包房还在!虽然招牌新了一些,但那股熟悉的麦香依旧。他推门进去,铃铛“叮铃”一声。柜台后面站着的,不再是阿力克桑德爷爷,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眉眼间有老爷爷的影子。
“请问……是阿力克桑德家的列巴吗?”阿依波力用略带生疏的俄语问道。
中年男人抬起头,笑着用流利的汉语回答:“是的,我父亲的手艺,我继承了。要来一个吗?刚出炉的。”
阿依波力买了一个列巴,热乎乎的,和他记忆中的味道几乎一模一样。他捧着列巴,眼眶有些湿润。
南苑卤香的招牌也还在,卤香味依旧诱人。他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这味道永远镌刻在肺里。
他走到了奶奶家的老院子前。那片湖蓝色的院墙,经过风雨的剥蚀,颜色已经斑驳暗淡,但依然顽强地立在那里。院子里,那棵苹果树还在,比记忆中更加高大粗壮,枝叶繁茂,只是此时已过花期,看不到满树繁花了。
他站在院门外,久久凝视。这里已经住进了别的人家,他不敢贸然打扰。只是这样看着,童年的一幕幕便如潮水般涌来。妈妈的呼唤,二哥的弹弓,野鸽子的咕咕声……一切都仿佛就在昨天。
物是人非。这个词从未如此刻骨铭心。
在六星街漫无目的地走着,感受着熟悉又陌生的氛围。他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下。他记得街角有一家招待所,以前叫“草原旅社”,现在好像重新装修过,名字也改成了更具旅游特色的“丝路客栈”。
他走进去办理入住。前台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穿着时髦,正在低头玩手机。
“你好,开一个单人间。”阿依波力说道。
姑娘抬起头,看到阿依波力风尘仆仆却难掩俊朗的面容,愣了一下,随即露出职业化的微笑:“好的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办理手续的间隙,阿依波力随口问道:“请问,你知道河对岸夏牧场那边,以前住着的莎吾烈泰一家,现在还在那里吗?”
姑娘歪着头想了想,摇摇头:“不太清楚呢。夏牧场那边人家挺散的,而且很多年轻人都搬进城或者出去打工了。”她看着阿依波力失望的神情,又补充道,“不过,你可以去问问街尾‘古兰丹姆’奶茶馆的老板娘,她是我们这儿的‘百事通’,在这条街住了几十年了,附近牧场的事她多少都知道点。”
“古兰丹姆奶茶馆?”阿依波力记下了这个名字。
安顿好行李,稍作休息,阿依波力便按照前台姑娘的指引,找到了街尾的奶茶馆。那是一家看起来很有年头的小店,门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门口挂着半截绣花门帘,里面飘出浓郁的奶茶香。
他掀开门帘走进去。店里光线有些暗,但很凉爽。几张木桌旁零星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慢悠悠地喝着奶茶,低声交谈。柜台后面,一位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哈萨克妇女正在擦拭茶壶,她体型微胖,面容慈祥,眼神却十分锐利。
“阿帕(大妈),您好。请给我一碗奶茶。”阿依波力用哈萨克语说道。
老板娘抬起头,打量了他一下,笑着用哈语回应:“好的,孩子。面生得很,是外地回来的吧?”她一边熟练地倒茶,一边问道。
“是的,阿帕。我离开家很多年了。”阿依波力在柜台边的高脚凳上坐下。
“一看就是。城里回来的娃娃,气质都不一样。”老板娘把盛着滚烫奶茶的陶碗推到他面前,又配了一小碟包尔萨克(一种油炸面点),“尝尝,自己家做的。”
阿依波力喝了一口奶茶,咸香醇厚,正是记忆中的味道。他心里一暖,鼓起勇气问道:“阿帕,向您打听个人。河对岸夏牧场,以前住着一户人家,他家有个女儿叫莎吾烈泰,您知道吗?她家现在……还在那里吗?”
老板娘擦拭茶壶的手顿了一下,她抬起头,更仔细地端详着阿依波力,眼神里闪过一丝探究和了然。
“莎吾烈泰……”她慢慢重复着这个名字,像是在回忆,“哦,你说的是老巴特尔家的莎吾烈泰吧?那个唱歌像百灵鸟一样的姑娘。”
“对!对!就是她!”阿依波力激动起来,心脏砰砰直跳。
老板娘叹了口气,放下茶壶,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老巴特尔前几年生病去世了。他家的牧场……唉,儿子不成器,赌钱欠了不少债,后来就把牧场卖了,搬到县城去了。”
阿依波力的心沉了下去:“那……莎吾烈泰呢?她也搬去县城了吗?”
老板娘看着他,目光里带着一丝同情:“莎吾烈泰那孩子,命苦啊。她阿爸当年确实给她定了亲,是隔壁牧场的一个小伙子。但那小伙子后来出去跑运输,出了车祸,人没了。婚也没结成。”
阿依波力呼吸一窒。她……没有结成婚?
“那后来呢?”
“后来?她阿爸去世后,家里就更难了。她弟弟不成器,欠了债跑了,追债的天天上门。莎吾烈泰为了还债,什么活都干。放牧、挤奶、去饭店帮工……后来,听说去了更远的冬牧场给人家做牧工,具体在哪,就不太清楚了。”老板娘摇摇头,语气里满是惋惜,“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又漂亮又能干,唱歌还好听,就是命不好。”
阿依波力呆呆地坐在那里,手里的奶茶已经凉了,他却毫无知觉。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震惊、心痛、愧疚、怜惜……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让他窒息。
他想象着那个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的姑娘,是如何在生活的重压下,一步步失去了她的歌声。他想起她当年那句“祝你前程似锦”,背后隐藏了多少无奈和心酸?而他自己,却在远方,过着所谓“更广阔”的生活,甚至……几乎要将她遗忘。
“我……我该怎么找到她?”阿依波力声音沙哑地问。
老板娘想了想:“你去冬牧场那边问问看吧。沿着公路往昭苏方向走,过了特克斯河大桥,那边有几个大的冬牧场接待点。她好像是在一个叫‘白云牧场’的地方帮工,不过我也不太确定,都是好几年前的消息了。”
“白云牧场……”阿依波力牢牢记住这个名字,“谢谢您,阿帕!”
他放下茶钱,起身就要离开。
“孩子,”老板娘在他身后叫住他,语气温和了些,“如果找到她,好好跟她说说话。那孩子,心里苦。”
阿依波力重重地点了点头,掀开门帘,走进了午后的阳光里。街道依旧,但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之前是怀旧的感伤,现在则充满了紧迫感和一种想要弥补的冲动。
他回到客栈,立刻开始查询去冬牧场的路线。冬牧场距离这里还有一百多公里,班车很少,而且到了地方还需要找车进入牧场区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开车去。
他在城里租了一辆性能不错的越野车,准备了一些饮水和干粮。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他便发动汽车,驶出了伊宁城,向着遥远的冬牧场进发。
公路在两旁无尽的草原和连绵的天山雪峰之间延伸。风景壮美,但他无心欣赏。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老板娘的话,是莎吾烈泰可能面临的艰辛,是那份沉甸甸的过往。
他恨自己回来得太晚。
开了几个小时后,他过了特克斯河大桥,按照路牌和偶尔的询问,终于找到了“白云牧场”的指示牌。那是一条颠簸的土路,通向雪山脚下的一片辽阔草场。
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才看到远处山坡上散落的毡房和围栏。空气中弥漫着牲畜和草料混合的气息。他停下车,走向最近的一座毡房。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牧民正在修补马鞍。
“阿达西(朋友),请问一下,这里有一个叫莎吾烈泰的妇女吗?是从河对岸夏牧场那边过来的。”阿依波力上前询问。
老牧民抬起头,脸上布满风霜的沟壑,他眯着眼看了看阿依波力,用手里的工具指了指更远处的一个山坡:“那边,山坳里那个独立的毡房,好像住着一个叫莎吾烈泰的。她是帮库尔班家放羊的。”
阿依波力道了谢,心跳再次加速。他按照指引,把车停在路边,徒步走向那个山坳。
越靠近,脚步越是沉重。他该说什么?怎么解释这十几年的缺席?她还会愿意见他吗?会不会已经彻底忘了他,或者,根本不想再提起往事?
终于,他看到了那座孤零零的毡房。毡房看起来有些旧了,但收拾得很干净。旁边用木栅栏围了一个小小的羊圈,里面只有十几只羊。一个穿着朴素哈萨克族长裙的身影,正背对着他,在毡房前晾晒奶疙瘩(一种酸奶制品)。她的背影有些单薄,微微佝偻着,长发简单地编成辫子,能看到几缕刺眼的白发。
风吹起她的裙摆和发丝,那个画面,莫名地让阿依波力感到一阵心酸。
他停下脚步,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个名字卡在喉咙里,重若千钧。
或许是听到了脚步声,或许是感觉到了背后的注视,那个身影缓缓地转了过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是她。尽管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皮肤变得粗糙,眼角有了细密的皱纹,但那五官的轮廓,那双眼睛……阿依波力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莎吾烈泰。
她也看到了他。起初是疑惑,随即是茫然,然后,那双依旧明亮的眼睛里,逐渐浮现出震惊、难以置信,以及……一丝迅速被掩饰起来的慌乱和复杂情绪。
她手里拿着的盛奶疙瘩的簸箕,“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白色的奶疙瘩滚了一地。
两人就那样隔着十几米的距离,静静地站着,对视着。风在草尖上奔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
过了许久,莎吾烈泰才缓缓弯下腰,默默地捡拾着散落的奶疙瘩。她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平静。
阿依波力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蹲下身,帮她一起捡。
“莎吾烈泰……”他终于叫出了这个名字,声音干涩而沙哑。
她没有抬头,只是低声应了一句:“嗯。”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
捡完奶疙瘩,她站起身,把簸箕放到一边,然后才抬起头,正视着他,脸上努力挤出一个平静甚至有些疏离的笑容:“阿依波力?真的是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只是在问候一个多年未见的普通朋友。
这平静让阿依波力更加难受。他宁愿她哭,她骂,她质问。
“我……我回了六星街,打听了好久。”阿依波力看着她,目光贪婪地描绘着她如今的容貌,心里疼得厉害,“你……你过得还好吗?”
莎吾烈泰转过身,走向毡房门口的小木墩坐下,拿起旁边放着的针线活,低头缝补起来,避开了他的目光:“就这样吧。放放羊,做点奶疙瘩,日子总能过下去。”
她的回避和沉默,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在了两人之间。
阿依波力在她旁边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这个话题。他环顾四周,这片山坳很安静,只有风声和偶尔的羊叫。她的生活,看起来是如此清贫和孤独。
“我……我都听说了。”他艰难地开口,“你阿爸的事,你弟弟的事……还有,你之前……”
“都过去了。”莎吾烈泰打断他,声音依旧平静,但握着针线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没什么好说的。”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阿依波力看着她熟练地飞针走线,看着她粗糙的手指和不再年轻的面容,想起当年那个在月光下弹着冬布拉、帽子上羽毛随风飘动的少女,巨大的时空错位感和心痛几乎要将他淹没。
“对不起……”他低声说,这三个字轻飘飘的,却承载了他十几年的愧疚。
莎吾烈泰的手彻底停了下来。她抬起头,望向远方的雪山,眼眶微微泛红,但终究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她轻轻地说,“当年让你走的,是我。你去了更广阔的世界,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不,不够!”阿依波力激动起来,“我忘不了!我忘不了那条河,忘不了那个晚上,忘不了你的歌声,忘不了……苹果香!”
听到“苹果香”三个字,莎吾烈泰的身体几不可查地震动了一下。她猛地转过头,看向他,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是惊讶,是回忆,还有一丝……柔软的触动。
阿依波力从随身的背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把已经完全干枯、变成褐色的花瓣碎片,但它们被精心地保存在一个透明的袋子里。
“你看,”他的声音带着哽咽,“你当年给我的苹果花……我一直留着。虽然它们早就碎了,但每次看到,我都能想起离开时,我家院子里那棵苹果树的花香,还有……和你在一起时,闻到的味道。”
莎吾烈泰怔怔地看着那把花瓣碎片,又抬头看看阿依波力通红的眼眶和真诚的神情,一直强装的平静外壳,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缝。
她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良久,才用极轻的声音说:“你……你还留着……”
“是,我还留着。”阿依波力坚定地说,“就像我忘不了你,忘不了故乡一样。莎吾烈泰,我回来了。这次,我不走了。”
莎吾烈泰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走了。”阿依波力站起身,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平视着她的眼睛,“我在外面,唱了很多歌,赚了一些钱。但我一点也不快乐。我的根在这里,我的心……也一直有一部分,留在了这里,留在了你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很突然,也很自私。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这些年的缺席,也不求你马上接受我。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留下来,陪着你,弥补我过去的遗憾,也……也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莎吾烈泰看着他,眼泪终于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滴在她粗糙的手背上,也滴在阿依波力的心上。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仿佛要透过时光,看清他此刻的真心。
风依旧在吹,草浪翻滚。远处传来牧人悠长的吆喝声。
过了很久,莎吾烈泰才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你……你还是那么傻。”
这句话,和当年那个晚上,她发现他在石头坐了一夜后说的话,一模一样。
阿依波力的眼眶也湿了,他用力点头:“是,我还是那么傻。傻傻地等过天亮,傻傻地等了你这么多年。”
莎吾烈泰看着他,终于,嘴角慢慢牵起一个真实的、带着泪花的笑容,虽然浅淡,却如同冲破乌云的阳光。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站起身,走进毡房,拿出了一个东西——一把旧的冬布拉。
她坐在木墩上,调了调弦,然后,手指轻轻拨动。
熟悉的旋律流淌出来,正是阿依波力在无数个夜晚魂牵梦绕的那首歌。她的歌声不再像少女时期那般清亮无暇,带上了岁月的沙哑和沉淀,却更加动人,仿佛在诉说着这些年的风霜雨雪,和那份深藏在心底、从未真正熄灭的柔情。
阿依波力坐在草地上,静静地听着。他看着她在歌声中微微晃动的身影,看着远处巍峨的雪山和辽阔的草原,闻着空气中混合了青草、泥土和奶制品的气息……
他忽然觉得,心中那个空缺了多年的地方,正在被一点点填满。
“草原,河谷,月季花香,都是我的歌……”他低声和着她的旋律。
如今,他回来了。往事或许远了,模糊了,但那份刻在生命深处的记忆与情感,如同这永不消散的苹果香,穿越了时间和距离,终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故事,似乎可以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但阿依波力和莎吾烈泰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重新开始,需要更多的勇气和磨合。故乡,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乌托邦,它有自己的发展和问题。但这缕由歌声牵引、跨越时空的苹果香,已经为他们的未来,指明了一条回归与弥合的道路。
而这,也正是所有浪迹天涯的孩子,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归宿。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