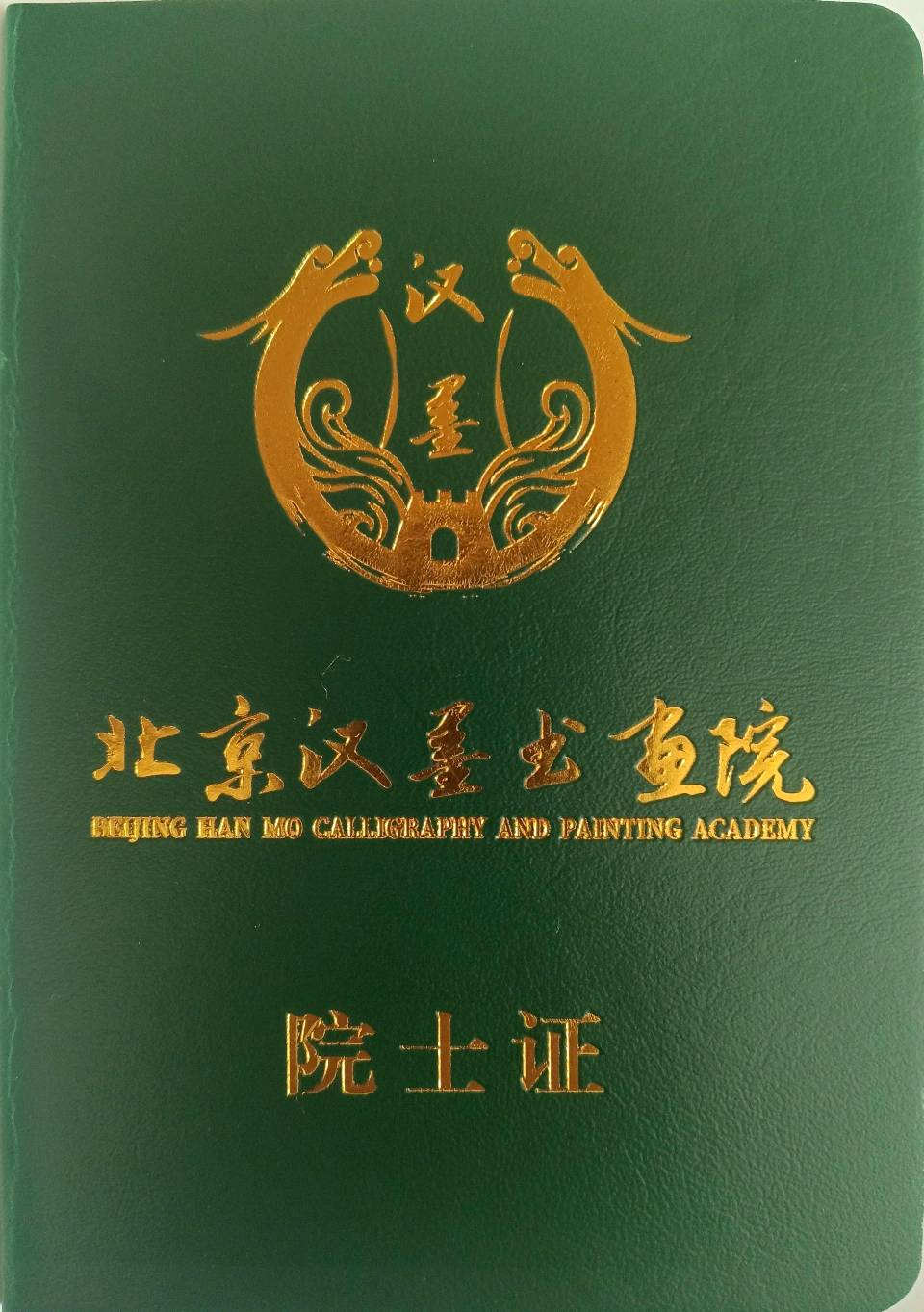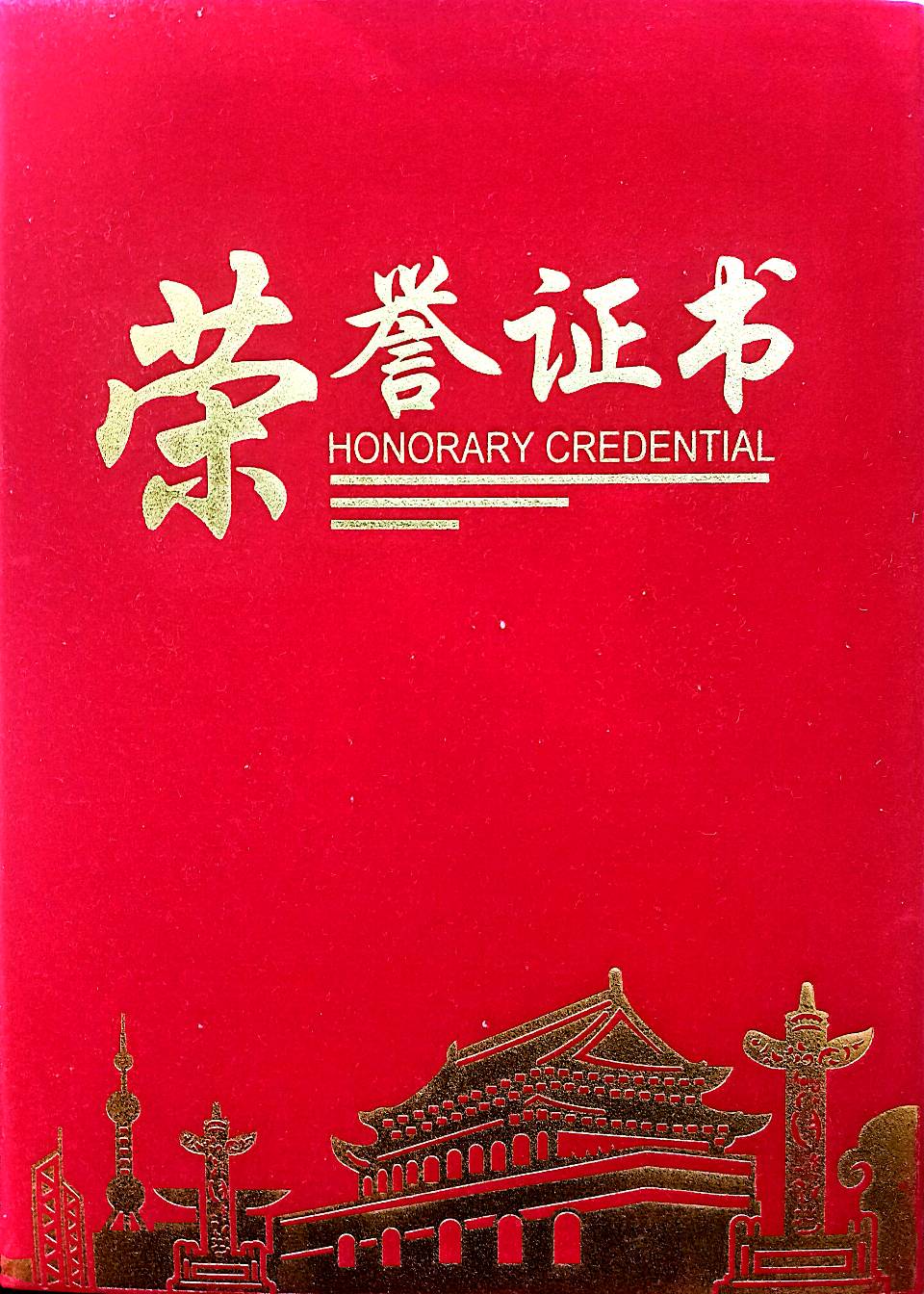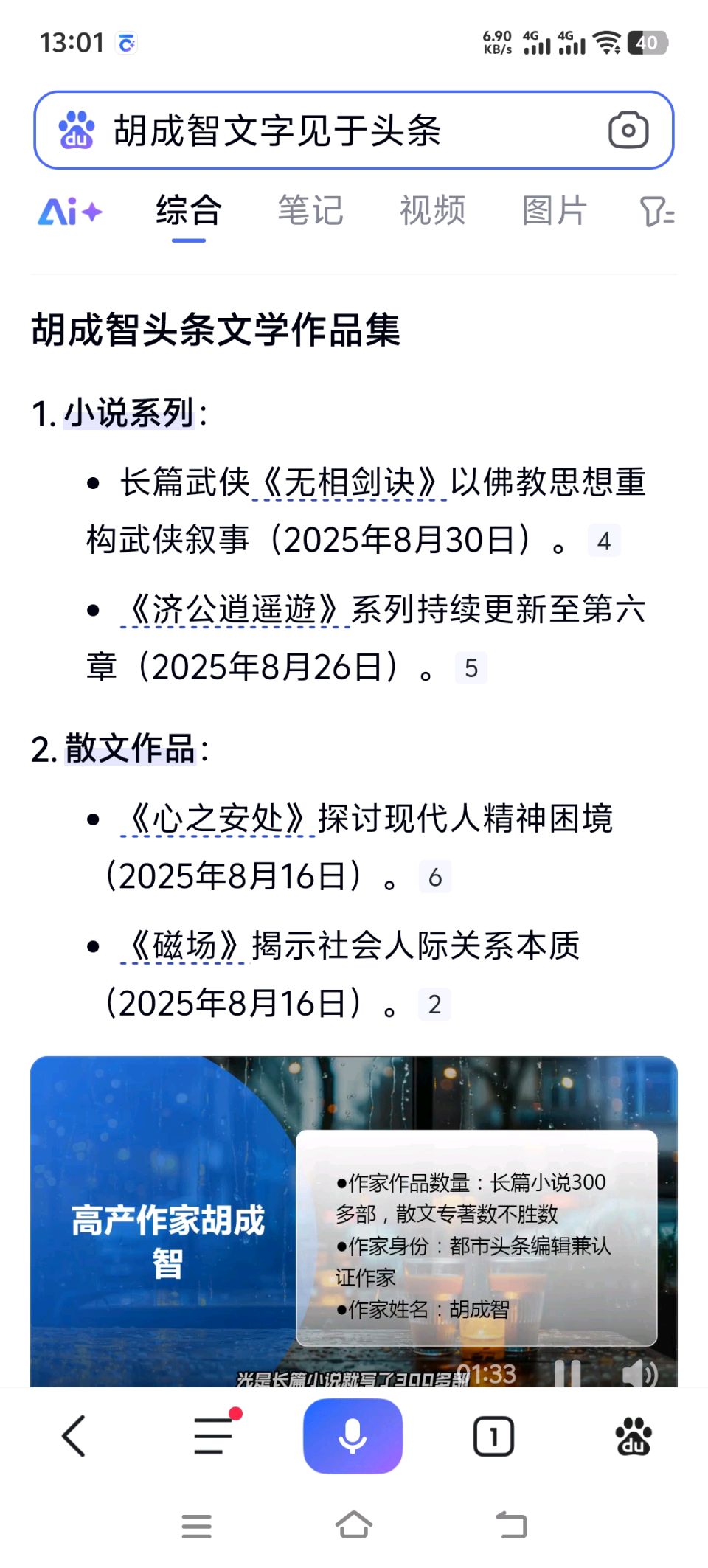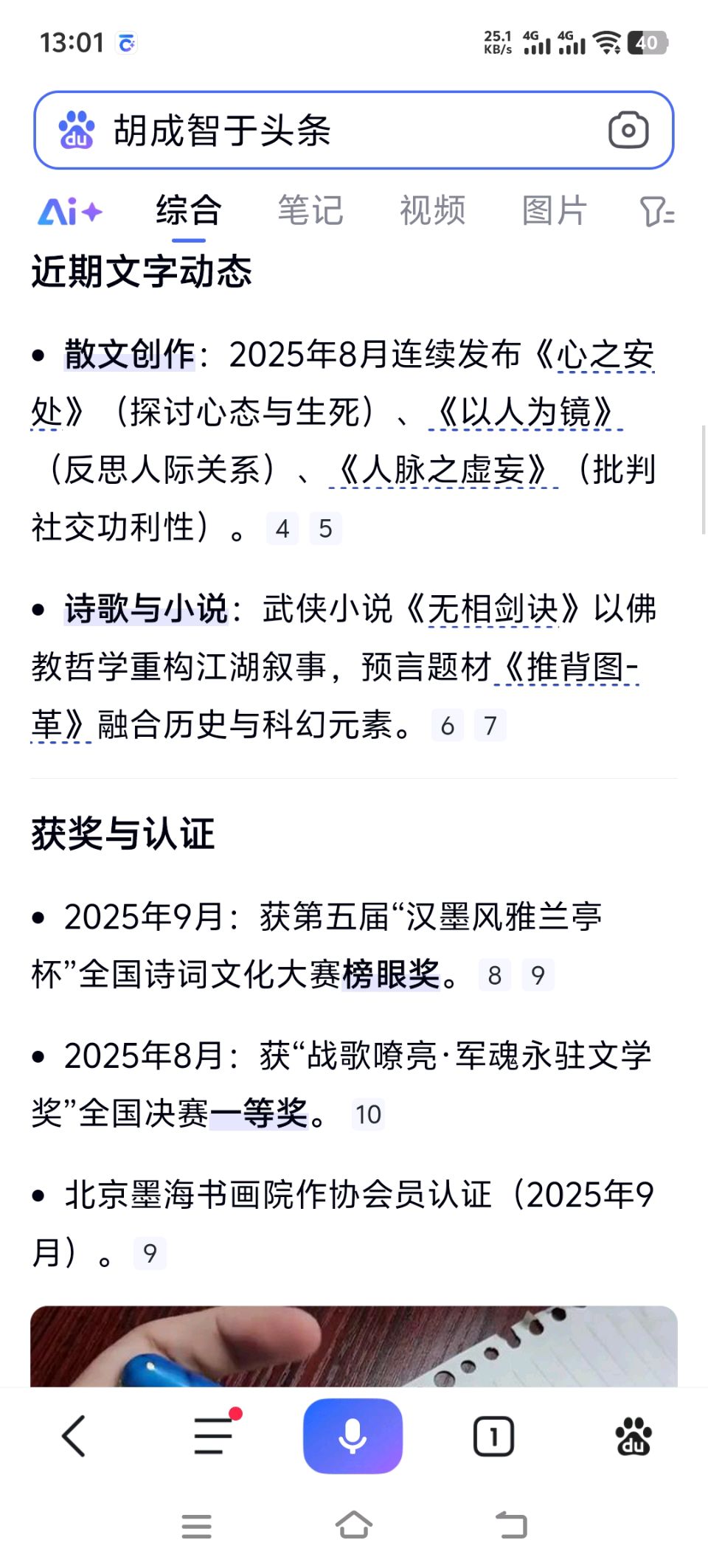---
《青春渡口》
第二卷 《离岸》
第六十五章 無校服的日子
父親那番關於“星圖與軌跡”的囈語,像一枚堅硬的種子,在陳燼余冰封的心田深處紮下了根,雖然尚未發芽,卻帶來了某種難以言喻的、內在的穩定感。然而,現實的困境,並不會因精神的片刻啟迪而有絲毫緩解。最直接、最尖銳的問題,如同冰冷的刀鋒,橫亙在他面前——沒有了校服,他該如何踏入省立一中那扇代表著秩序與身份的大門?
第二天清晨,他依舊在天光未亮時醒來。陋室裡,父親難得地沉睡著,呼吸聲雖然粗重,卻不再是那種撕裂般的哮鳴。母親也還在睡夢中,臉上帶著連日操勞的疲憊。陳燼余輕手輕腳地起身,沒有點燈,在黑暗中摸索著,穿上了那身他最舊、打滿補丁、顏色洗得發白幾乎難以辨認原本樣式的粗布衣褲。布料粗糙,摩擦著皮膚,與之前那身挺括的藏青色校服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他站在水缸前,藉著從門縫透進的微光,看著水面上那個模糊的、穿著寒酸得像個小學徒似的倒影,一種強烈的格格不入感和羞恥感,再次湧上心頭。他幾乎能想像到,當他這樣走進教室時,會引來怎樣驚詫、好奇、甚至鄙夷的目光。
但他別無選擇。
他背上那個母親用舊布拼湊的書包,深吸了一口凜冽的晨氣,推開門,踏入了省城黎明前最深的寒意之中。
通往學校的路,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每一步,他都感覺有無數無形的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那些目光來自早起的路人,來自同樣趕往學校、卻穿著整齊校服的陌生同學。他下意識地低下頭,縮起肩膀,試圖減少自己的存在感,像一隻誤入鶴群的灰撲撲的麻雀,只想盡快逃離這令人窒息的審視。
果然,當他走到省立一中那氣派的鐵藝大門口時,負責值守的校工攔住了他。那是一個面色嚴肅的中年人,用一種混合著疑惑和不容置疑的權威目光,上下打量著他這身與校園氛圍格格不入的打扮。
“你是哪個班的?校服呢?”校工的聲音帶著例行公事的冷硬。
陳燼余的臉瞬間燒了起來,心跳如擂鼓。他張了张嘴,喉嚨乾澀,一時竟不知該如何解釋。難道要說為了給父親抓藥而典當了嗎?這理由在現實面前顯得如此蒼白而可笑。
“我……我是新錄取的……陳燼余……”他艱難地報出自己的名字,聲音低得幾乎只有自己才能聽見,“校服……暫時……暫時……”
就在他語無倫次、幾乎要陷入絕望之際,一個平靜而溫和的聲音從旁邊響起:
“他是我班上的學生,陳燼余。校服的事情,我已知曉,稍後會補辦手續。”
陳燼余猛地抬頭,只見國文教員程先生不知何時站在了旁邊。程先生穿著一身半舊的青色長衫,面容清癯,眼神溫潤而帶著一種洞察人心的力量。他對著校工微微點了點頭,校工見是先生出面,便不再多問,側身讓開了道路。
“謝謝……謝謝程先生。”陳燼余如同溺水之人抓到了浮木,連忙躬身道謝,聲音依舊帶著顫抖。
程先生看著他,目光在他那身破舊的衣服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裡沒有鄙夷,沒有好奇,只有一種深沉的、近乎悲憫的理解。他什麼也沒多問,只是輕輕拍了拍陳燼余的肩膀,溫聲道:“進去吧,快打鐘了。”
陳燼余低著頭,幾乎是小跑著穿過了校門。他能感覺到身後那些來自其他同學的、更加密集和複雜的目光,像無數細小的針,扎在他的背上。
走進教室的那一刻,原本喧鬧的空間瞬間安靜了一下。所有目光,或明或暗,都聚焦在了他這身突兀的打扮上。驚訝、疑惑、竊竊私語……各種情緒在空氣中無聲地交織、發酵。陳燼余感覺自己像一個被剝光了衣服、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小丑,臉頰燙得驚人,他幾乎是逃也似的衝到了自己那個最靠角落的位置,將頭深深地埋了下去。
這一整天,他都處於一種極度敏感和緊繃的狀態。他不敢與任何人對視,不敢參與任何交談,甚至下課去廁所,都要等到人最少的時候。那身破舊的衣服,像一層有形無形的隔膜,將他與周圍的世界徹底隔絕開來。他感覺自己彷彿被剝奪了某種身份認同,重新變回了那個來自梧城縣底層的、一無所有的少年,甚至比那時更加不堪,因為他曾經短暫地擁有過,又失去了。
無校服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它不僅僅是身體上的寒冷(省城的冬日,沒有厚實的校服保暖,只穿著單薄舊衫的他確實凍得瑟瑟發抖),更是精神上的酷刑,是尊嚴被反覆摩擦和拷問的過程。
他只能緊緊攥著口袋裡那張冰冷的當票,和父親那句關於“軌跡”的話,作為支撐自己,不在這無形的壓力下徹底崩潰的、最後的力量源泉。
第六十六章 程先生的硯台
無校服的日子,如同在荊棘叢中赤足行走,每一步都帶來尖銳的刺痛和難以癒合的傷口。陳燼余在省立一中的校園裡,徹底成了一個“隱形人”。他將自己縮在教室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課間從不離開座位,走路時永遠低著頭,目光只敢落在自己腳前三尺之地,彷彿這樣就能將那身代表著貧窮與恥辱的舊衣衫,連同他自己,一併從這個光鮮亮麗的世界裡抹去。
然而,有些目光是無法躲避的,比如來自講台上的。
國文教員程先生,是少數幾個沒有因為他衣著的改變而流露出異樣神情的師長之一。他依舊如常地講課,聲音溫潤平和,引經據典,將枯燥的文言文講解得深入淺出,充滿了思想的魅力。他的目光依舊會掃過全班,偶爾也會在陳燼余的方向停留,但那目光裡沒有探究,沒有憐憫,只有一種平等的、對知識傳遞對象的關注。
這讓陳燼余在極度的自卑與緊繃中,獲得了一絲難得的喘息之機。只有在程先生的課堂上,他才能暫時忘記自身的窘境,將心神投入到那些跨越千年的文字與思想之中。
這天下午,是程先生的國文課。講授的內容是韓愈的《師說》。程先生並未急於解析文字,而是從“師道”與“尊嚴”的關係談起,談及古之學者為求學問,可不畏艱險、不避貧賤,所求者,乃天地之理,人間之道,而非一身之錦衣華服。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程先生吟誦著古文,聲音不高,卻清晰地迴盪在安靜的教室裡,“衣冠楚楚者,未必胸有丘壑;簞食瓢飲者,或懷瑾握瑜。諸君當知,求學問者,首重其志,次修其心,外物之華,不足恃也。”
他的話語,如同涓涓細流,潤物無聲,卻又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陳燼余低著頭,聽著這些話,心中卻如同被投下了石子的湖面,蕩漾開層層漣漪。他感覺程先生這些話,彷彿不只是對全班同學的教誨,更是對他一個人處境的、最溫和卻也最有力的聲援與開解。
下課鈴聲響起,同學們紛紛收拾書本離開。陳燼余照例等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默默起身,準備離開。
“陳燼余,”程先生卻在講台上叫住了他,聲音依舊平和,“你留一下。”
陳燼余的心猛地一跳,有些忐忑地停下腳步,轉過身,垂手站在教室門口。
程先生沒有立刻說話,他只是低頭,慢條斯理地收拾著講台上的教案和文具。然後,他拿起一方看起來頗為古舊、邊緣已經磨得十分圓潤的端硯,走到陳燼余面前。
那方硯台石質細膩,色澤沉穩,雖然陳舊,卻透著一種歷經歲月沉澱的溫潤光澤。
程先生將硯台遞到陳燼余面前,語氣平淡如常:“我這裡有一方舊硯,閒置已久,蒙塵可惜。見你習字勤勉,筆力日進,便轉贈於你吧。望你善加利用,莫負了這點石中精魂。”
陳燼余徹底愣住了。他看著那方一看便知價值不菲、絕非“閒置蒙塵”之物的古硯,又抬頭看看程先生那雙溫潤而帶著不容拒絕意味的眼睛,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反應。
這不是施捨。程先生的語氣、神態,沒有一絲一毫施捨的意味。這更像是一種師長對勤勉後輩的認可與期許,一種基於對“才”與“志”的欣賞,而產生的、純粹的贈與。
“先生,這……這太貴重了……學生不能……”陳燼余囁嚅著,不敢伸手去接。
程先生微微一笑,那笑容裡帶著洞察一切的瞭然:“硯台之用,在於磨墨載文,不在其值幾何。寶劍贈英雄,紅粉贈佳人,這方舊硯,於你手中,或許方能物盡其用,不負其作為文房清供的使命。”他頓了頓,目光變得有些深邃,低聲道,“身外之物,一時之困,切勿縈懷。守得住心中一點清明燭火,方是長久之道。”
說完,他不由分說地,將那方沉甸甸的端硯,塞到了陳燼余的手中。
冰涼而潤澤的觸感從掌心傳來,那重量,不僅是石頭本身的重量,更是程先生那份沉甸甸的信任與期望。
陳燼余雙手捧著那方硯台,指尖微微顫抖,喉頭哽咽,千言萬語堵在胸口,最終只化作深深的一躬,和一句帶著顫音的:“多謝……先生教誨!”
程先生擺了擺手,拿起自己的教案,轉身飄然離開了教室。
空蕩蕩的教室裡,只剩下陳燼余一人,雙手緊緊捧著那方古硯,如同捧著一盞在寒夜裡驟然點亮的、溫暖而明亮的燈。
這盞燈,驅散了無校服帶來的陰影,也照亮了父親所謂“星圖”中,那條屬於“志”與“學”的、或許可以憑藉自身努力去觸摸的軌跡。
第六十七章 圖書館的燈火
程先生贈硯的舉動,像一道溫暖而強勁的洋流,注入了陳燼余幾乎被冰封的心海,不僅帶來了溫度,更攪動了深層的水域,帶來了營養與生機。那方沉甸甸的舊硯,被他用母親給的、最乾淨的一塊舊布,層層包裹,珍而重之地放在書包的最底層。它不再僅僅是一方硯台,而成了一種精神的象徵,一個無聲的誓言——他必須對得起這份超越物質的贈與,對得起程先生那“守得住心中一點清明燭火”的期許。
無校服的羞恥感依然存在,周圍異樣的目光也並未完全消失,但陳燼余的心態,卻發生了微妙的、決定性的變化。他不再一味地躲藏和自卑,而是開始嘗試著,將所有的精力與注意力,更加純粹地聚焦於學業本身。既然外在的“殼”已經被迫剝離,那麼,他就只能用內在的“核”——知識與思想——來為自己重新鑄造一副鎧甲。
圖書館,自然成了他這番“鑄甲”工程最重要的工坊。他幾乎將所有不屬於課堂和西藥房的時間,都耗費在了那裡。沈先生角落裡的炭爐早已撤去,但那方天地依舊是他感覺最自在、最安全的所在。
他不再僅僅滿足於完成課業和應付考試。在沈先生看似隨意、實則用心的指點下,他的閱讀範圍開始向更廣、更深的領域拓展。他開始系統地閱讀中國古代史,不僅看正史,也找來一些野史筆記,試圖從多個角度去理解那些教科書上乾巴巴的結論;他開始接觸一些西方哲學的入門譯著,儘管那些拗口的名詞和迥異的思維方式讓他頭疼不已,但他強迫自己啃下去,因為他隱約感覺到,那裡面有一個與他所受傳統教育完全不同的、廣闊而新奇的世界;他甚至開始嘗試閱讀一些淺近的英文原版故事書,憑藉著字典和一股狠勁,一個詞一個詞地摳,雖然進展緩慢得令人絕望,但每讀懂一個句子,都帶來一種微不足道卻真實的成就感。
沈先生依舊是那個沉默的守護者。他很少主動與陳燼余交談,但陳燼余需要的書籍,總會“恰好”出現在他常坐的位置附近,或者沈先生會在整理書架時,“順便”將某本相關的著作放在顯眼的位置。偶爾,當陳燼余在閱讀中遇到實在無法理解的難題,鼓起勇氣前去請教時,沈先生也只是點到為止地提示一兩句,絕不越俎代庖,總是留下足夠的空間讓他自己去思考和探索。
這種無聲的、建立在對知識共同尊重基礎上的互動,成了陳燼余精神成長中最寶貴的養分。他開始體會到,學問之道,並非僅僅是記誦和應試,更是一種思維的訓練,一種視野的開拓,一種與古今中外智者靈魂對話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忘記了衣著的寒酸,忘記了囊中的羞澀,甚至暫時忘記了父親那持續的咳嗽聲和家庭的沉重壓力。
他的世界,在圖書館的燈火下,被無限地擴大了。
與此同時,他也在默默地為贖回校服而努力。西藥房的夜班依舊雷打不動,那是他目前唯一穩定的收入來源。他計算著日子,計算著每一次結算的工錢,小心翼翼地積攢著,雖然距離那筆贖金還很遙遠,但至少,希望已經有了具體的數字和可見的路徑。
這天夜裡,他在圖書館閉館前的最後一刻,才合上手中那本厚厚的《全球通史》譯本。抬起頭,揉了揉因為長時間閱讀而乾澀發脹的眼睛,發現偌大的閱覽區裡,只剩下他一個人。沈先生正站在不遠處,準備熄滅最後幾盞燈。
“沈先生,我這就走。”陳燼余連忙站起身,開始收拾書包。
沈先生點了點頭,沒有催促。當陳燼余背好書包,走到門口時,沈先生忽然開口,聲音在空曠的圖書館裡顯得格外清晰:
“書,是隨身的淨土。心,是自己的明燈。”
陳燼余腳步一頓,回頭望去。沈先生已經轉身,開始熄滅最後一盞燈,身影融入漸濃的黑暗裡,只有那平靜的話語,如同籤言,烙印在陳燼余的心上。
走出圖書館,省城的夜空依舊是那片熟悉的、被燈火映成暗紅色的混沌。寒風撲面而來,他下意識地裹緊了單薄的舊衣。
但這一次,他沒有感到往日的瑟縮與寒意。
因為他知道,無論外面的世界多麼寒冷、多麼艱難,他的內心,已經被圖書館的燈火,被程先生的硯台,被沈先生的箴言,也被他自己點燃的、那簇名為“求知”的火焰,照亮了一角。
這光亮雖然微弱,卻足以讓他在黑暗中,看清腳下的路,也看清自己那顆不甘沉淪、奮力向上的心。
第六十八章 軌跡的選擇
父親的病情,在苦澀藥汁的持續作用下,如同被勉強壓住的爐火,時而看似平穩,時而又會竄起幾縷令人心驚的、帶著哮鳴的火苗。那三劑藥很快見底,而典當校服換來的錢也已耗盡。母親周氏的臉上,剛剛鬆動了幾日的愁雲,再次濃重得化不開。她開始更加瘋狂地接活,那雙手的紅腫開裂處,甚至開始滲出淡淡的血水,在冰冷的河水和鹼性皂角的雙重刺激下,疼痛鑽心。
陳燼余將這一切看在眼裡,那方程先生贈予的端硯帶來的溫暖與激勵,在冷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與一種更深沉的焦慮並存。他知道,必須盡快賺到更多的錢,不僅是為了贖回校服,更是為了父親後續的藥費,為了這個家能夠繼續在省城這片冰冷的土壤上,勉強紮根下去。
西藥房的夜班收入是固定的,抄書的活計也並非時時都有。他必須開闢新的“財路”。
這天課間,他無意中聽到幾個同學在抱怨即將到來的期末考試,尤其是數學和英文,讓他們頭疼不已。其中一個家境似乎頗為優渥、名叫趙瑞安的同學,甚至半開玩笑地說道:“要是有人能幫我把這些難纏的公式和單詞都搞定,我寧願出錢請個‘槍手’!”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陳燼余的心猛地動了一下。
“槍手”……替人做功課,換取報酬?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讓他感到一陣強烈的不適和抵觸。這無疑是舞弊,是對學術誠信的玷污,也完全背離了程先生贈硯時對他的期許。他幾乎能想像到,如果程先生或沈先生知曉,會對他流露出怎樣失望的眼神。
可是……現實呢?父親的藥不能斷,校服必須贖回,房租和米糧像兩隻飢餓的野獸,時刻張著血盆大口。尊嚴、誠信,在赤裸裸的生存面前,似乎都成了奢侈而蒼白的字眼。
兩種念頭在他腦海中激烈地搏殺著,如同天使與魔鬼的拉鋸。一邊是來自底線和師長教誨的召喚,一邊是來自家庭困境和親情壓力的驅使。
他想起父親關於“星圖”與“軌跡”的話。父親並未指明哪條軌跡是正確的,只是告誡他“莫要迷了路”。那麼,哪條路才是不會迷失的路?是堅守所謂的“清高”,眼看著家庭在泥沼中沉淪?還是暫時放下那些虛無的原則,換取實實在在的、救命的資源?
放學後,他沒有立刻去圖書館,而是獨自一人,在省城寒冷的街道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天色漸暗,華燈初上,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又縮短,變幻不定,如同他此刻紛亂的心緒。
他走過燈紅酒綠的商業區,那裡充斥著物質的誘惑與繁華的虛幻;他走過骯髒破敗的貧民窟,那裡瀰漫著掙扎的艱辛與生存的頑強。他看到西裝革履的紳士從汽車上走下,也看到衣衫襤褸的乞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他忽然意識到,這個世界本就充滿了各種各樣、或明或暗的規則與生存之道。絕對的潔白,或許只存在於理想之中。在現實的灰色地帶裡,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著生存的縫隙。
那麼,他的縫隙在哪裡?
替人做功課,無疑是一條捷徑,一條能夠快速獲取相對豐厚報酬的“軌跡”。但走上這條路,就意味著他將背離自己內心認可的某些東西,意味著他可能就此滑向一個自己都無法預料的方向。
可是,如果拒絕這條路,他又該如何去籌措那筆急需的款項?難道要靠母親那雙已經不堪重負的手嗎?還是要靠他自己那點微薄的、按部就班的收入?
不知不覺間,他竟走到了那家當鋪的附近。看著那扇熟悉的、如同怪獸巨口般的大門,他典當校服時的屈辱感再次清晰地浮現。那種將自身最珍視的東西抵押出去的無力與痛苦,他絕不想再經歷第二次!
一種近乎破釜沉舟的決絕,在這一刻壓倒了一切猶豫。
他不能讓母親倒下,不能讓父親無藥可醫,也不能讓自己永遠失去那身代表著希望與尊嚴的校服。
他猛地轉過身,不再猶豫,大步朝著學校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找到那個趙瑞安,去談一筆他極不情願、卻又不得不做的“交易”。
他知道,這個選擇,或許會玷污他靈魂的某一部分。
但他別無選擇。
這是他為自己、為家庭,在命運的星圖中,被迫選擇的一條,充滿荊棘與陰影的軌跡。
他只能期望,在未來的某一天,當他擁有足夠的力量時,能夠有機會,將這片污點,從自己的人生中,徹底洗刷乾淨。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奖。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