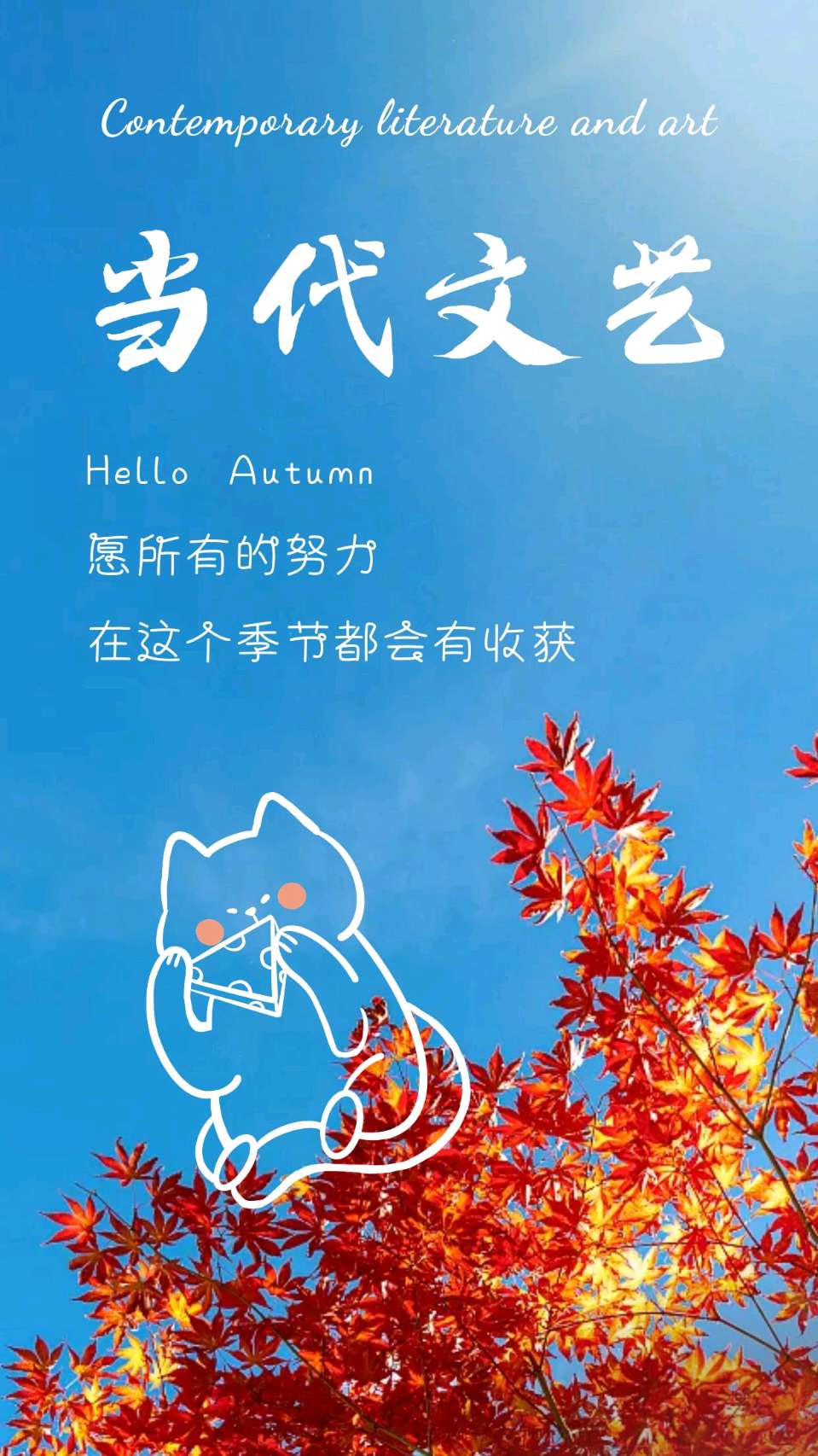传 斌
作者:一愚
珠江的风,和辰安的电话,一下子把我召到了广州的“小蛮腰”。“小蛮腰”是广州塔的呢称。孙子在这里上小学。临行前,有人说,你这一去,接上手,就很难抽出身。果不其然。与孙子粘得热乎。原先还怕他嫌弃爷爷有体味,没想到他一心要跟爷爷睡。每天晚上,做完作业,洗完澡,就抱着枕头,被子,赖到我床上。“爷爷,我今天还是跟您睡。”睡就睡吧,我例行讲两个小故事,都是我和他爸爸小时候捡蝉蜕,逮蜈蚣,捉土鳖虫之类的一些小经历。我感觉这是最好的催眠曲。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有时还能在梦中听到他的笑声。我索性中断了与老家的联系,心无旁骛地当起了“招孙办”主任。反正拖地,买菜,陪辰安上学,与过去晨跑,练剑,打太极拳,也没有什么差别。相反,心里还要快活得多。
有得就有失。国庆节期间,我给也在武汉带孙子的妹妹打了一次电话。她告诉我说,传斌去逝了,已经快一个月了。我责怪她没及时把这消息告知我。她说,她也是后来才得到消息。还说,送传斌那天,有同学专门给我打过电话。传斌今年也给我发过多次短信和微信。我都没有回复。我感到震惊。立马查阅了手机记录,一点没错。同学打来的电话,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陌生电话我一般不接。传斌发给我的短信和微信,多是对学长的节日问候,我比他高一个年级,他一直这样称呼我。几十年一样,哪怕是后来晋升了将军衔,也没有改过口。他一直顺风顺水,健健康康。有可能是我以为来日方长,一时没有回复。也有可能是被临时打断,后面又没有回翻。想不到,就留下了阴阳两隔的遗憾。
我还是不相信传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他去年刚刚到点,享受正军职待遇退休。他说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这样就是祖坟冒烟了。要惜福。因此,他把银钱看得很淡,经常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生活在老家农村的乡亲和同学。我们有些同学,条件很差都还顽强地活着。例如李忠诚,老婆走了,独子是弱智,自己又中风卧床。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难道这是老天在造化弄人?需要解脱的,让你活着受罪。可以享福的,让你消失无常。我连续打了两个同学的电话确认,答案都是一样的。他们还告诉我,传斌去年秋天检查出肝硬化,本来可以到北京住院治疗,但他不愿意麻烦部队,选择了回老家疗养。他一直低调,在老家也从不增添地方政府的负担。去年一年,我都在仙桃。退休之后,一直深居简出,与外界基本没有来往,只有“诗和远方”一扇窗户没有关闭。但用的又是笔名。自然没有知晓他在仙桃养病。去年冬季和今年春节,他给我发过几则微信,我也回过几则微信,互动热络。但他没有丝毫透露身体不适的消息。倒是在信中反复提醒我,要勤作些检查。他知道,我小时候,曾得过胸膜炎。我以为他还在河南郑州,或者山东济南。没想到,他是与我同城,在和病魔抗争。他是有条件住三0一医院的。
虽然,我不是故意疏忽传斌。但客观上疏忽了他。由于我的疏忽,我们不但失去了一段相互陪伴的日子,而且还失去了最后的一次告别。
确认传斌已经走了之后的一段日子,我都沉浸在了内疚和思念之中。我经常在吃了晚饭之后,把孙子交到已经下班了的儿子,一人摸到珠江上的海心桥独坐。海心桥是一座新修的跨江观光桥。南岸是广州塔,北岸是东塔和西塔。都高耸入云,分别名列全国第一高塔,和第四,第八高楼。夜幕降临,华灯骤亮。塔上,桥上,江上,火树银花。如织的游人,沉醉珠江的夜景。我坐在海心桥中段的一处廊墩上,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已经不可能再有互动的微信和短信。珠江的风,溢满了我对他的思念。
其实我和传斌的朝夕相处,只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时我和传斌同在一所农村初中读书。学校只有两个年级,两个年级又各只分了两个班,座落在离襄河不远的金河村。我在二(1)班,他在一(1)班。教我们班数学的胡引焕老师,同时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直接推荐我出任校学生会(时称红卫兵大队部)学宣部长,并把一块校团支部和学生会联合举办的黑板报交给我组稿,一个月更新一次。这对我是莫大的信任和鼓励。我和传斌的友谊,就是在这个平台上结下的。
记得学校的食堂设在校园的西南角,再往南是一口池塘。池塘边有几棵大柳树。大多数同学在学校吃午饭,碗是学校统一购置的砂砵。饭毕,在池塘洗净后放还。吃着吃着,砂砵就少了。在连续几次补买砂砵之后,终于觉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借抽水机抽干池塘,一百多个砂砵都完好无损,潜在池底。显然,是有些同学,懒得洗碗,或者觉得好玩,把碗丢到了水里。黑板报上要有一篇评论。传斌找我第一次投稿,个子不是很高,微胖,衣服皱巴巴的,但文章写得很好。我眼睛一亮,连夜排版,在头条位置刊出。是请张定江,还是付正文同学抄录的,我记不清了。但那篇评论的笔锋还有印像:同学们随手丢掉的不是简单的砂砵,是莘莘学子的儒雅之气,是劳动人民的节俭本色,是学校主人的责任意识。几十年了,还记得个大概。就是认为好,至于好在哪里也说不清。以后我们就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传斌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编辑部的台柱子,好像还有二(2)班的张国泉同学。
湖北省的初中,由两年制向三年制过渡,是从我读初中的那一届开始的。先延长半年,把秋季学期毕业,改为春秋学期毕业。因此,我与传斌就延长了半年的同学之谊。有一点是令我格外感激的。传斌人小心细,对我保护有加。应该不止一次,他悄悄地对我说,有些政治敏感,言辞激烈的文章,就让他来署名。因为当时论阶级,我家的成份不太好。这是我的硬伤。有同学这样保护我,我怎么能不感动呢?这种感动,只有经历了那种压抑的人,才能觉得无比珍贵。
越是临近毕业,他越看出我有些忧伤。与校园那几棵高大栁树相对,也有几棵高大的柳树,南侧,相距三百米左右。树上没有鸟巢,挂着一口铁钟。司钟的人,艺名“一朵云”,天沔花鼓戏程派唱腔创始人。相传,他的弟子演出,曾多次受到过国家领导人接见。此时,被发配回家乡改造。乡亲们念其人老体弱,照顾他司钟,钟声是村民按时出工和收工的讯号。他早上敲三十六响,中午敲七十二响,晚上敲一百零八响。据说都与《水浒传》有关。传斌每天中午陪我听七十二响钟声。钟声悠扬激越,没有丝毫落魄之感。我是想读书,想做七十二贤人,而又不得不面对读高中彻底无望,初中毕业即失学的现实。传斌知道我心里难受,就默默地陪在我身边。他把疏导宽慰的希望,都融进了那七十二响悠扬激越的钟声。
后来我们就各奔东西。若干年后,我成了一名地方基层的公务员,他成了一名解放军某部的司令员。
我比他长三岁,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比我迟五年。自然而然,我就要比他早八年退休。在我退休的头一年,他多次电话邀我去郑州。我说,现在的规矩多,就不给你添麻烦了。他坚持说,我自费尽地主之谊,还能有什么问题?记得那次郑州之行,他破例请了两天假,陪我看了洛阳牡丹,龙门石窟,和嵩山少林寺。他还要陪我去看黄河三门峡。我说留点念想下次来吧!没想到竟然就没有了下次。那次相见,竟成了诀别。记得我们还约定,等他退休了,我们一起去看望胡引焕老师。胡老师还在青山三中宿舍,等着我们的到来,他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没有享受一年他应该享受的退休待遇。
珠江的风,又一次吹散了我的头发,让一些染黑了的头发,又露出了新长的白发。我终于下定决心,从此刻开始,删除我们之间短信和微信的聊天记录。这世界本来就是年青人的,把美好的未来留给儿子和孙子,我们就坦然一点地去吧。是时,海心桥的两侧栏杆开始有露珠凝结,江面上的五彩游轮逐渐归港,不知何处飞来的几只鹭鸟凌空向北飞去。
我知道,天地万物都是过客。但我对传斌的思念,就像珠江之水,不能止息。
树欲静,而风不止。
乙巳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广州
【作者简介】
鲍厚成,笔名一愚。湖北仙桃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武汉散文学会会员。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