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行于文字间,遇见失语的星光
——读张述《失语者的村庄》有感
付朝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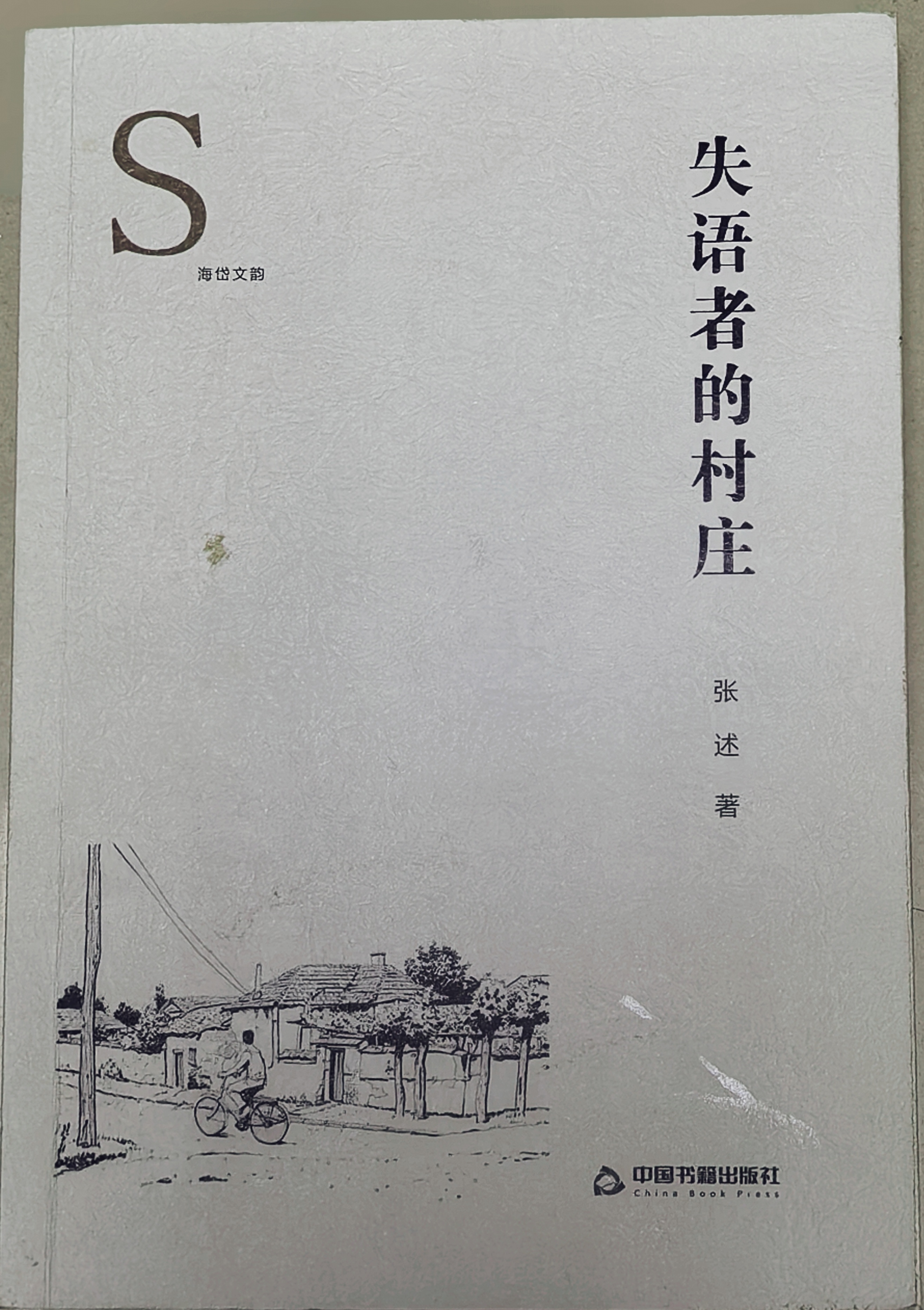
张述老师的《失语者的村庄》被我翻阅很多遍了,一篇感悟始终没有写出来,或许是对书本作者的了解还不深刻,再读张述老师《失语者的村庄》时,像在秋夜的灯影下,听一段关于文字与心灵的私语。写作者多有一颗柔软的心,面对粗粝的世界,竟像蜗牛般,以文字为触须探索,以沉默为外壳守护——这话一入眼,便轻轻撞进了每个曾在喧嚣里渴望寂静的人心里。
现实中的张述老师是备受欢迎的教学名师,语言表达自然利落,可在文学世界里,他偏以“失语者”自居。这份反差,像春日里开在石缝中的花,不张扬,却藏着动人的执拗。想来,许多对文字怀有执念的人,大抵都有这样的“两面性”:在人群中或许能从容谈吐,可当面对内心那片纯粹的文学天地时,反而愿意褪去所有“话术”,只剩一颗赤诚的心,在沉默里与自己对话。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史铁生在地坛的寂静里捕捉灵感,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独处中书写哲思,张述的“失语”,原是与这些灵魂相通的默契——沉默不是空白,而是文字生长的土壤。
《失语者的村庄》是张述老师三十年“蜗行”的结晶。这“蜗行”二字,读来格外有分量。三十年,足够一座小城换了模样,足够一代人从青涩走到沉稳,而张述却用这漫长时光,一点点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村庄”。当书中同名篇目在中国作家网刊载时,“失语者的声音何其响亮”——原来,那些在沉默里积攒的力量,终会通过文字,化作穿透喧嚣的回响。这让我想起自己偶尔提笔的时刻:或许只是深夜里写下几行零散的句子,或许是对着一张旧照片记录细碎的回忆,当时只觉是无人问津的“自语”,可多年后再读,竟发现那些文字早已成了照亮过往的微光。张述的三十年,何尝不是无数热爱文字者的缩影?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写、慢慢走,像蜗牛背着壳,看似缓慢,却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心上。
这座文学“村庄”里,藏着太多动人的风景。“旅途散记”记录人生行踪,“点状人生”反思现实处境,“时光近浅”回眸青春往事——三部分内容,像三条蜿蜒的小路,最终都通向作者对文学梦的执着。序言里说,张述为了文学之梦,“守护着一片沙漠中的绿洲,守护着无数喧嚣中的那份失语般的孤独与寂静”。这“守护”二字,让我想起老家邻居李爷爷院角的那棵老槐树,李爷爷守了它几十年,任凭外界盖起高楼,依旧年年为它修剪枝丫。文学梦于张述,大抵也如这老槐树于爷爷,是喧嚣世界里不愿放弃的纯粹,是疲惫生活里不肯熄灭的火种。
更动人的,是“村庄”里的文字之美。那些文字“简洁朴素中蕴含秀美,细腻温婉中亦不乏张力”,背后是三十年的人生历练与艺术修行。读这样的文字,像喝一杯温茶,初尝时清淡,细品却有回甘。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能精准触到人心最软的地方——比如回不去的少年岁月,比如化不开的浓浓乡愁。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这样一座“村庄”:可能是童年住过的老房子,可能是外婆灶台边的烟火气,可能是少年时偷偷读过的一本旧书。这些细碎的记忆,平日里被生活的忙碌掩盖,可当遇到像张述这样的文字,便会忽然苏醒,让人想起自己也曾是“失语”的追梦人,也曾在沉默里守护过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这个喧嚣躁动的世界里,“交际并不困难,难的倒是惜缄默无语,惜墨如金”。这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许多人的状态:我们习惯了在社交平台上频繁表达,习惯了用碎片化的语言交流,却渐渐忘了沉默的力量,忘了文字的重量。张述老师的“失语”,不是真的无言,而是对文字的敬畏——不愿轻易开口,是怕辜负了内心的真诚;不愿随意下笔,是怕稀释了情感的浓度。这种敬畏,让《失语者的村庄》有了独特的温度,也让每个翻开这本书的人,愿意慢下来,在文字里感受寂静的美好。
合上书页,想起序言结尾的话:“让读者诸君走进失语者的‘村庄’吧——那些轰轰烈烈的孤单寂寞,那些缥缈难求的前尘往事,那些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乃至文学之梦的格外沉重,这一切,都有待读者亲自领略与品味。”其实,我们走进的何止是张述的“村庄”,更是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曾被忽略的角落。在这座“村庄”里,我们看见写作者的柔软与坚守,也看见自己的过往与憧憬;我们听见失语者的“声音”,也听见自己心底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
或许,每个热爱文字的人,都是一只蜗行的蜗牛:带着柔软的心,背着沉默的壳,用文字的触须探索世界,用漫长的时光书写热爱。而《失语者的村庄》,便是这趟蜗行路上的一盏灯,照亮了那些沉默里的坚守,也温暖了每个在文字里寻找共鸣的灵魂。当我们在喧嚣里感到疲惫时,不妨走进这座“村庄”,听一听失语者的独白,看一看文字里的星光——那里,藏着所有与热爱有关的答案。
付朝兰,山东省济南市人,笔名大海。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编《大家风范文库,拾贝集》《中国少儿沙画》《诗意人生》《乡情乡韵》。刊发在《山东广播电视报》《山东教育报》《济南时报》等。并有多篇作品获奖。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