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叩问节义亭:
当生命成为道德的祭品
崔志亮
钱塘五日,虽值新秋,却因一念之差,与凤凰岭下的节义亭失之交臂。归来后,那对在历史尘埃中若隐若现的崔升夫妇身影,却如幽灵般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清嘉庆年间,崔升携妻陈氏赴杭投亲不遇,困顿无依,面对劝陈氏改嫁之声,夫妇二人选择了“固穷守志,至死不移”,最终在凤凰山下双双自缢。这段被冠以“节义”之名的悲剧,被钱塘县令建亭表彰,成为教化百姓的道德标本。然而,穿越两百年的时空,这亭台所承载的,究竟是令人景仰的气节,还是生命被礼教吞噬的悲歌?
在中国传统伦理的天穹上,“节义”如同北极星,指引着无数士人的精神航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屈原怀抱理想,自沉汨罗江;项羽乌江自刎,不留恋苟且之生;文天祥面对威逼利诱,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他们舍生取义的壮举,源于对某种高于生命的价值的坚守——或是家国大义,或是理想信仰。在《孟子》构筑的道德体系中,“生吾所欲也,义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成为士人面临终极抉择时的黄金法则。
然而,当我们把崔升陈氏夫妇的悲剧置于这面道德镜鉴前,却发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这对夫妇所面对的,并非国破家亡的大时代悲剧,亦非忠孝难两全的道德困境,而仅仅是“投亲未果,穷困不能返乡”的生活窘境。在劝陈氏改嫁的声音面前,他们本可有多种选择:崔升可以务工糊口,陈氏可以织布补贴,甚至可以乞讨返乡。但他们却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双双自尽。这种抉择,与其说是对“义”的坚守,不如说是对现实困境的逃避,是对生命价值的轻蔑。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轻生之举,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重要价值维度形成了尖锐冲突。《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儒家伦理中,生命不仅是自我的,更是祖先血脉的延续,是家族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崔升若有父母在堂,他的自尽无疑是对孝道的彻底背叛;即便双亲已故,他也肩负着传承血脉的责任。而劝妻子同死,更是对“夫妇之义”的扭曲——真正的夫妻情义,应是相互扶持、共渡难关,而非携手赴死、成就虚名。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的反思尤为深刻:“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他深知赴死可能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只能忍痛抉择。相比之下,崔升夫妇的抉择显得如此单薄——他们没有子嗣需要抚育,没有家国需要守护,只有那不堪一击的“面子”和被人议论的恐惧。孔夫子路遇欲自缢男子的故事,恰恰提供了另一种智慧:“你既有自缢的勇气,怎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呢?”生命的韧性,往往在绝境中才能迸发最耀眼的光芒。

节义亭的建立,暴露了传统社会价值导向的某种偏执。当权者通过表彰这类极端行为,将复杂的道德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以此强化礼教对社会个体的控制。这种表彰背后,隐藏着一种冷酷的逻辑: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符合特定道德规范时才值得肯定;否则,生命的消逝不仅不可惜,反而值得鼓励。这种逻辑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贞节牌坊下的寡妇,到愚忠赴死的臣子,无数生命成了道德祭坛上的牺牲品。
司马迁的抉择,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生命哲学的范本。面对宫刑之辱,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并非因为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完成《史记》这一文化使命。在给任安的信中,他悲愤地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深刻理解——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瞬间的壮烈,更在于持续的创造——远比草率赴死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节义亭,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清醒和勇气,对传统进行理性的扬弃。我们敬重那些为崇高价值献身的英雄,但拒绝将任何形式的轻生浪漫化、道德化。每个生命都是独特而宝贵的存在,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面对困境,真正的“节义”不应是逃避现实的决绝,而是承担责任的勇气;不应是成就个人名节的自私,而是关爱他人生命的慈悲。

湖山烟雨隔,心祭寄云流。当我遥拜那座未曾谋面的节义亭时,心中涌起的不是对“节义”的景仰,而是对生命的悲悯。我宁愿历史少一座这样的节义亭,多一对在困境中携手前行、见证岁月流转的平凡夫妻。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如何壮烈地死,而在于如何坚韧地生——这或许是穿越时空后,我们对节义亭最应有的叩问。
2025年11月10日于虞河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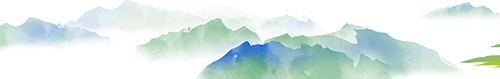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