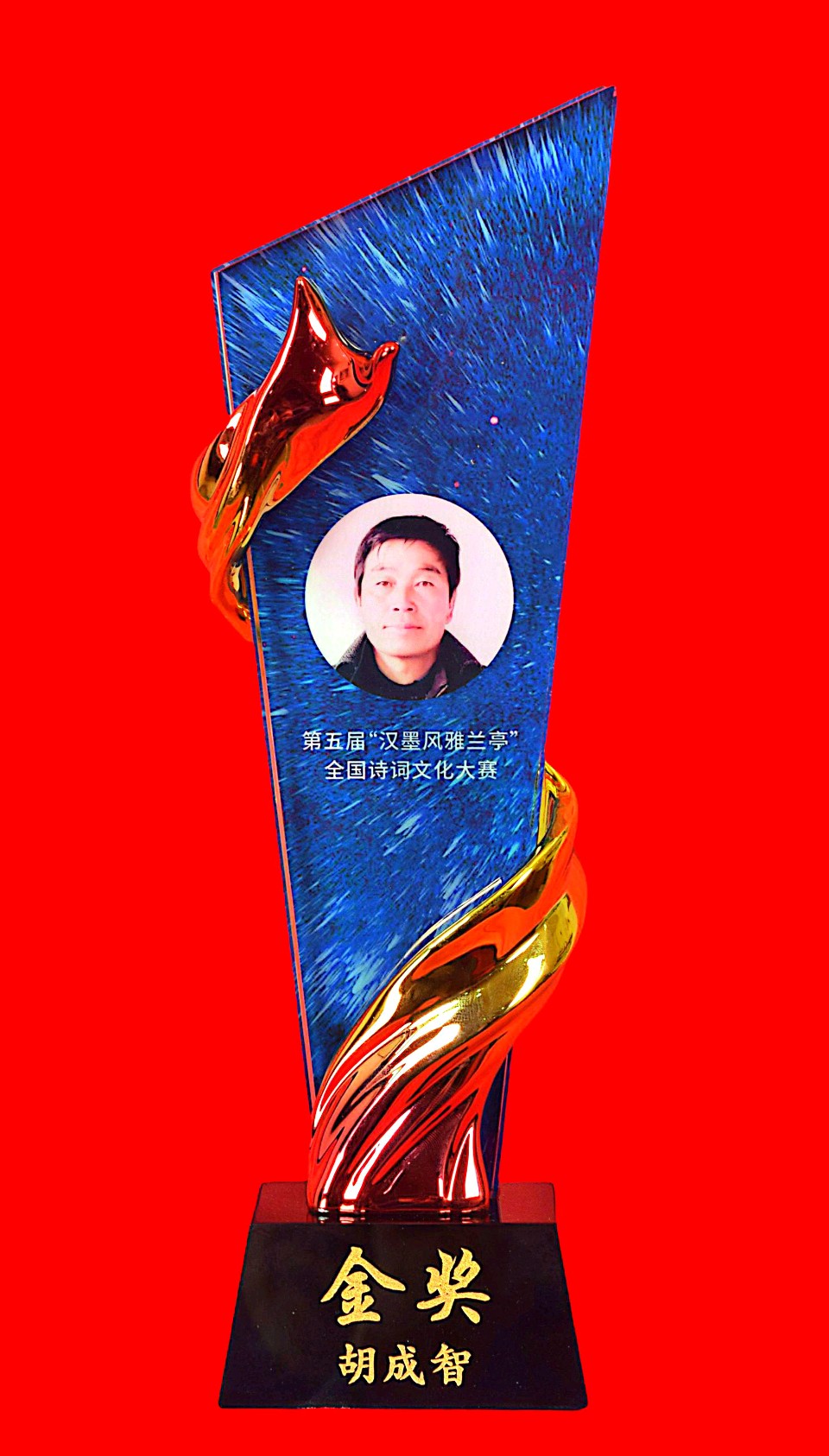第一卷:入梦
第一章 瓷梦
沈墨笙是在伦敦肯辛顿区这间终日需要点灯的书房里,想起那个关于“客”字的训诂的。
暮色四合,泰晤士河上氤氲的湿气,透过厚重的丝绒窗帘,依然能浸润进来,给满室维多利亚风格的繁复家具蒙上一层冷寂的微光。壁炉里的火哔剥作响,却驱不散这深入骨髓的、英伦特有的阴寒。他坐在那张陪伴他跨越了半个地球的紫檀木圈椅里,身子深深陷进去,像一枚被时光遗忘在旧书页里的干枯标本。手中是一卷摊开的《庚子销夏记》,指尖正停留在“倪瓒”二字上,那元代的高士,也是散尽家财,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做了大半生的“客”。
他的手指有些僵冷,不仅因为这天气,更因为心头那缕挥之不去的凉意。目光从书页上抬起,落在书案正中那只北宋影青釉划花缠枝莲纹碗上。碗是极好的,釉色青白淡雅,如玉如冰,内壁刻划的缠枝莲线条流畅宛转,透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冷静的完美。它是这间堆满异国物什的书房里,唯一的精神锚点,是他从故国苏州、从已然倾颓的沈家老宅“锦云记”带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旧物之一。光影在它光滑的弧面上流转,恍惚间,他仿佛看到的不是莲花,而是故乡老宅“听雨楼”外,那几株老梅在冬日疏朗的枝干。
就在这时,书房门外传来了争执声,是他十六岁的女儿沈薇拉(Vera Shen)和她的同学。声音由远及近,大约是刚从什么聚会回来,少女清亮的、略带夸张的英语,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刺破了书房里凝滞的怀旧空气。
“我告诉你,亨利,那根本不算什么!”是薇拉的声音,带着一种被冒犯了的、急于证明什么的急切,“我祖父在苏州的庄园,听雨楼,光是藏书就有三万卷!花园里的太湖石,是从宋朝的‘花石纲’遗物里选出来的,每一块都值你现在住的这整栋房子!那里的宴席,用的是明朝的官窑瓷器,吃的是一道道需要十八道工序的精细点心,哪里是今天这粗糙的蛋糕和红茶能比的?”
每一个单词,都像一把小锤,敲击在沈墨笙的心上。他握着书卷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出青白色。庄园?听雨楼确实是一座精美的园林宅邸,但在他离去的那个雨夜,它已在连天的烽火中显出破败之相。三万卷藏书?大半已随着他那只沉入长江的行李船,化为了鱼鳖的巢穴。官窑瓷器?除了眼前这一只他贴身携带的影青碗,其余的,早已在颠沛流离中或损或卖,或不知所踪。那些她口中用来证明家族荣光的、具体而微的物象,早已被时代的巨轮碾得粉碎,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影子,供他在无人时的梦里反复摩挲、拼凑。
可这些,薇拉如何能懂?她生在利物浦,长在伦敦,她所认知的“故国”,是他和妻子在无数个夜晚,用语言、用回忆、用刻意美化的细节,为她精心编织的一个华丽的、遥远的梦。她不曾见过真正的听雨楼,不曾触摸过那些带着体温的丝绸,不曾嗅过江南梅雨时节,那潮湿空气里混合着的书香、墨香和腐朽木料的气息。她把那个梦当成了真实,并且用这虚幻的真实,来武装自己在异国他乡那敏感而脆弱的自尊。
沈墨笙感到一阵深切的无力与悲哀。他不是在生女儿的气,他是在气自己,气这命运的拨弄。他们这些离人,如同无根的浮萍,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艰难地扎下一点须根,而下一代,却已然把这漂泊的状态当作了常态,甚至将父辈记忆里的海市蜃楼,当作了可以炫耀的勋章。他们才是真正的“客”,不仅在空间上是客,在时间上、在文化上,都成了永远的“客”。薇拉炫耀的,恰恰是她永远无法真正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更深沉的、属于流亡者后代的悲剧。
“薇拉。”他终是忍不住,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不容置疑的威严,穿透了门外的议论。
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片刻,书房门被推开,沈薇拉走了进来,脸上还带着未褪尽的、与人争辩时的潮红。她穿着伦敦时下最流行的及膝裙,头发烫成了波浪卷,完全是一副西方摩登女郎的样貌,只有那双微微上挑的凤眼,还依稀保留着东方血脉的印记。
“父亲。”她唤了一声,眼神有些闪烁,似乎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高谈阔论可能被听了去。
沈墨笙没有立刻说话,他只是缓缓地将手中的书卷放在膝上,目光深沉地落在女儿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脸庞上。他看着她,仿佛要通过她,看向那个遥远、模糊,却始终盘踞在他心头的江南。
“你在跟同学,讲听雨楼?”他问,声音平缓,听不出喜怒。
薇拉有些局促地点点头,随即又扬起下巴,带着一丝倔强:“是的,父亲。亨利他们总以为我们……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来自一个真正有历史的文明古国。”
沈墨笙的嘴角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近乎苦涩的弧度。他伸出那双曾经能辨识出最上等蚕丝、如今却已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手,轻轻捧起了书案上的那只影青碗。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直抵心脏。
“历史……”他喃喃道,目光垂落在碗壁那清冷的划花上,“薇拉,你知道‘客’这个字,在中文里,除了‘客人’,还有什么意思吗?”
薇拉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客,寄也。”他缓缓说道,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寄居者,外来者,暂住者。古人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苍茫天地间,其实都是短暂的过客。”
他的手指摩挲着碗沿,那细腻温润的质感,是故乡的泥土,是故乡的火焰,是千百年的时光锻造出的精灵。
“这只碗,”他继续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痛楚,“它在这里,在我的手上,在这间伦敦的书房里。它是一件珍宝,一件‘历史’。可是,它离开了它的窑火,它的故土,它原本应该陈设的案几,它在这里,是什么?”
他抬起眼,目光如炬,直视着女儿茫然的眼睛。
“它在这里,是‘客’。和我一样,和你一样。”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我们炫耀的,或许正是我们永远失去的。我们居住的,或许正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拥有的。这才是最深的……客愁。”
话音落下,书房里一片死寂。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以及窗外伦敦永不间断的、如同背景噪音般的雨声。那雨声,潺潺地,绵绵地,像极了无数个夜晚,响彻在苏州听雨楼外的、那场下在他心头的、永无止境的雨。
沈薇拉怔怔地看着父亲,看着他手中那只在灯光下泛着幽光的古碗,看着他脸上那种她从未完全理解的、深沉的痛苦与落寞。她似乎隐约触摸到了什么,那是一种比失去庄园、失去财富更深重、更无法排遣的失落。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那些流利的英语词汇,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沈墨笙不再看她,他将目光重新投向窗外无边的黑暗。他知道,那个关于“听雨楼”的、由他亲手编织的梦,在这一刻,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而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残忍,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迟来的启蒙。
他只是更紧地、更紧地,握住了手中那冰凉的影青碗。仿佛握住的,是整个世界沉没前,最后一抹虚幻的倒影。
---
第二章 听雨
记忆,如同被那一声“客”字撬开了闸门,汹涌地倒灌回沈墨笙的脑海。不是零碎的片段,而是完整的、带着湿漉漉气息的、属于江南春天的场景。
那不是伦敦这黏稠阴冷的雨,而是苏州的雨,是“锦云记”沈家老宅“听雨楼”外的雨。是润如酥的春雨,淅淅沥沥,打在庭院的芭蕉叶上,打在鱼鳞瓦上,打在青苔遍布的假山石上,汇成一片绵密而富有层次的交响。那声音,不惹人厌烦,反而让宅院显得愈发幽静,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柔软的雨声包裹、安抚。
他记得,那是光绪三十四年的春天,他十六岁。身子是清瘦的,穿着月白色的直缀,坐在听雨楼二楼的轩窗下。窗外是迷蒙的雨幕,将远处的亭台楼阁、近处的花草树木都渲染成一幅氤氲的水墨画。空气中弥漫着新茶的清香、古籍特有的霉味,还有雨水带来的、泥土和植物的鲜活气息。
他的父亲,沈家那一代的当家人沈文渊,就坐在他对面的红木嵌螺钿扶手椅上。父亲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杭绸长衫,面容清癯,眼神却锐利如鹰,手中正拿着一份刚刚由驿站送来的《申报》。报纸上,充斥着“预备立宪”、“铁路国有”、“革命党人起事”之类的字眼,那些方块字组合在一起,像一颗颗不安分的石子,投入了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以丝绸和诗书传家的宁静世界。
“墨笙,”父亲放下报纸,目光透过窗棂,望向雨中的庭院,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你可知,我们沈家这座‘听雨楼’,名字的由来?”
少年沈墨笙抬起头,放下手中的《昭明文选》,恭敬地回答:“儿子记得,是取自南宋词人蒋捷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之意。曾祖当年建此楼,是为赏景怡情。”
沈文渊微微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复杂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多少欢愉,反而有种看透世事的苍凉。“赏景怡情,固然不错。但蒋捷那首词,后面还有——‘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他顿了顿,目光重新落在儿子身上,那目光似乎要穿透少年单薄的身体,看到他无法预知的未来。“‘听雨’二字,听的何尝是雨?听的是人生境遇,听的是世道变迁,听的是……身为‘客’的漂泊与无常。”
少年沈墨笙似懂非懂。他的人生尚未完全展开,听雨楼于他,是坚实、温暖、永恒的庇护所,是承载了他全部童年欢愉和少年梦想的乐园。他无法理解“客舟”的孤寂,更无法想象“僧庐”的冷寂。他只觉得,在这雨声环绕的楼里,守着满室书香,听着父亲教诲,便是人间至境。
“我们沈家,以丝绸立世,‘锦云记’三个字,是靠着一代代人,像春蚕吐丝般,一点一滴织出来的。”沈文渊的声音将他的思绪拉回,“蚕吃桑叶,吐丝作茧,将自己困于其中,最后破茧成蝶,或者……被人缫丝煮茧。这其间的分寸,存乎一心。”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负手而立,望着窗外被雨水洗刷得愈发青翠的竹林,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如今这世道,就像这场看似温柔的春雨,底下却藏着惊雷。外面的世界在变,变得很快,很剧烈。我们守着这祖宗基业,守着这听雨楼,是福是祸,犹未可知。”
他转过身,眼神凝重地看着儿子:“墨笙,你要记住。无论将来是安居于此,还是漂泊异乡,心要定。要记得我们根本何在。这听雨楼,不只是一座宅子,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若有一天……若有一天你不得不离开,也要记得这雨声。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还能‘听’见这雨声,你的心,就还没有完全变成无根的浮萍。”
父亲的话,在当时十六岁的沈墨笙听来,虽觉沉重,却仍觉得遥远。他无法想象离开听雨楼,离开苏州,离开这浸润了他全部生命的江南水乡。他只觉得父亲是忧心时局,未免有些过虑。
然而,此刻,在伦敦这间昏暗的书房里,隔着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和万里之遥的距离,重温父亲的这番话,沈墨笙才骤然明白了其中全部的、血淋淋的预言性质。
“客舟”、“僧庐”、“鬓已星星”……父亲早已在那一刻,为他,也为整个沈家的未来,写下了一纸残酷的判词。
而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才真正读懂。
他放在膝上的手,无意识地蜷缩起来,仿佛想要抓住那早已消散在苏州雨幕中的、父亲的身影,抓住那场再也听不真切的、故乡的雨。
伦敦的雨,依旧在窗外潺潺地下着。但在他耳中,那只是噪音。真正的雨,只下在记忆里,下在那座永远回不去的“听雨楼”外,下在他这颗早已千疮百孔、却依然为那场梦而悸动的——客心上。
---
第三章 裂帛
记忆的画卷继续展开,色彩却陡然变得浓烈、尖锐,带着一丝不祥的预兆。那是在父亲与他“听雨”谈话后不久,一个晴朗的午后。春光烂漫,听雨楼外的海棠开得正盛,粉白的花朵堆云叠雪,几乎要灼伤人的眼睛。
沈墨笙奉父命,去“锦云记”的工坊熟悉家族核心的织造业务。工坊就在老宅后身,占据了整整一条巷子,空气中常年弥漫着蚕丝煮熟后特有的、略带腥甜的蛋白质气息,以及染料、浆糊混合的复杂味道。数百架织机发出的“唧唧”声,如同一种庞大的、永不停歇的背景音乐,是沈家财富与声望的基石。
他穿过忙碌的晾丝场,那里如瀑布般悬挂着无数绞丝,在阳光下闪烁着象牙般柔和的光泽。工人们见了他,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恭敬地唤一声“少爷”。他微微颔首,径直走向最里面、守卫最森严的“天工阁”。那里是织造最高等级织物的地方,特别是专供宫廷的、被誉为“寸锦寸金”的云锦和缂丝。
那天,天工阁里正在织造一幅巨型的《瑶池吉庆图》缂丝。缂丝,通经断纬,宛若雕镂,画面上的王母、仙姬、祥云、瑞兽,正随着老织工颤抖而精准的手,一寸一寸地从无到有地显现出来。色彩绚烂,辉煌夺目。
负责天工阁的大师傅,姓顾,是跟了沈家三代的老人,一双眼睛因常年审视丝线而显得有些混浊,但眼神里的精光却丝毫不减。他见沈墨笙进来,忙起身相迎。
“少爷来了。”顾师傅的声音沙哑,带着长年累月吸入棉绒丝絮的磨损感。
沈墨笙的目光被那幅即将完成的缂丝牢牢吸引,忍不住赞叹:“顾师傅,真是鬼斧神工!此等精品,恐怕宫内也难得一见。”
顾师傅的脸上却不见多少喜色,反而笼着一层忧色。他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少爷,精品是精品,可这世道……唉,听说武昌那边又不太平了,宫里头的供奉,银子是一年比一年难要了。咱们‘锦云记’,外表看着光鲜,内里的流水,也紧巴得很哪。”
正说着,一个小学徒捧着一匹刚织好的、准备做袍料的湖绉,脚步匆匆地从旁边走过,不知是被门槛绊了一下,还是心慌,一个趔趄,竟直直地朝那架着的《瑶池吉庆图》缂丝撞去!
“小心!”顾师傅脸色剧变,嘶声喝道。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沈墨笙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只见那小学徒手中的湖绉脱手飞出,边缘恰好扫过了缂丝画幅下方的一角。只听“嗤啦”一声——清脆、锐利,带着一种丝绸特有的、决绝的撕裂感。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工坊里沉闷的空气,也劈在了沈墨笙的心上。
时间仿佛凝固了。小学徒面如死灰,僵在原地,浑身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周围的织工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梭子,惊恐地望着这边。
顾师傅一个箭步冲上前,小心翼翼地捧起那被撕裂的一角。画幅上,一位仙娥的裙裾处,一道寸许长的裂口,狰狞地张开着,破坏了整体的完美,像一道永难愈合的伤口。
老织工的手指颤抖着抚过那道裂口,混浊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泪水。他不是心疼这价值千金的物料,他是心疼这倾注了数月心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艺术品,毁于一旦。
“这……这……”他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沈墨笙也呆住了。他怔怔地看着那道裂口,看着顾师傅脸上的泪,看着小学徒绝望的神情。方才父亲关于“世道惊雷”、“福祸未知”的话语,言犹在耳。而此刻,这清脆的“裂帛”之声,就像那声惊雷,第一次如此真切、如此具象地,炸响在他的世界里。
这不仅仅是一匹缂丝的损毁。在那一瞬间,一种莫名的、巨大的恐慌攫住了他。他仿佛看到,某种坚固的、永恒的、维系着他全部生活的东西,就在这“嗤啦”一声中,出现了第一道致命的裂纹。是“锦云记”的基业?是听雨楼的安宁?还是他所熟悉的那个完整无缺的世界?
他不知道。他只是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让他在这春光煦暖的午后,如坠冰窖。
工坊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道裂帛的余音,似乎还在梁间缠绕,不肯散去。
许久,顾师傅才颓然地放下手,对那面如死灰的小学徒挥了挥手,声音疲惫到了极点:“罢了……罢了……也是它的命数。你,下去吧。”
小学徒如蒙大赦,连滚爬爬地跑了。
顾师傅转向沈墨笙,惨然一笑:“少爷,您看……这或许,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沈墨笙没有回答。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道裂口,仿佛要把它烙印在灵魂深处。
他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他还将听到无数次、更剧烈、更无情的“裂帛”之声——家族的、情感的、信仰的、国家的……
而这一声,不过是命运奏响的、第一个冰冷的音符。
---
第四章 远行
“裂帛”的余音,仿佛一种不散的阴魂,缠绕在听雨楼内外,为那个春天提前画上了一个仓促而灰暗的休止符。接下来的几个月,沈墨笙敏感地察觉到,府内的气氛日渐凝重。父亲沈文渊待在书房里的时间越来越长,来往的客人也变得形色匆忙,脸上时常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焦虑。就连下人们走路的脚步都放轻了许多,说话也带着小心翼翼。
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骇人听闻。“保路运动”风潮席卷数省,“武昌新军暴动”的消息终于不再是谣传,而是变成了触目惊心的铅字——“辛亥革命”。一个个省份相继宣告“独立”,大清王朝268年的江山,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风雨飘摇。
终于,在那个秋意已深、梧桐叶大片大片凋落的下午,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沈墨笙被唤到父亲的书房。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在紫檀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扭曲的光斑,像一道道流淌的血痕。沈文渊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书案后,而是站在那幅巨大的《江山社稷图》缂丝面前,背对着他。父亲的背影,在斜阳中显得异常挺拔,却又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孤寂与决绝。
“墨笙,”父亲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仿佛在讨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你准备一下,三天后,动身去英国。”
沈墨笙如遭雷击,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英国?父亲!为什么?现在外面那么乱,我怎么能……”
“正因为乱,你才必须走!”沈文渊骤然转身,打断了他的话。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双眼睛,燃烧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沈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锦云记’的根在苏州,但枝叶必须延伸到更安全的地方。我们在利物浦有一家合作的洋行,你去那里,名义上是学习西方的纺织技术和商业模式,实则是为我们沈家,留一条退路,存一点血脉!”
“退路?血脉?”沈墨笙的心狂跳起来,一股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父亲,那您呢?母亲呢?还有弟弟妹妹们呢?我们一起走!”
“糊涂!”沈文渊厉声喝道,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一走,‘锦云记’立刻就会垮!沈家立刻就会散!这听雨楼,这祖宗基业,不能就这么扔了!我必须留下,稳住局面,能守多久是多久。”
他走到沈墨笙面前,目光如两把锥子,直直地钉进儿子的眼睛里:“你是长子,是沈家未来的希望。你的肩上,担着不只是你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整个家族延续的可能。记住,此去不是游学,是……是播种,是潜伏。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你都要在那边,活下去,站稳脚跟。”
沈文渊从书案的暗格里取出一个紫檀木匣,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银票、几张地契,还有那枚象征着家族信物的、温润如脂的羊脂白玉螭龙钮章。
“这些,是你启动的资金。这枚章,见章如见我。”他将木匣推到沈墨笙面前,动作沉重如铁,“还有,带上它。”
父亲的手,指向了书案一角那只北宋影青釉划花缠枝莲纹碗。
沈墨笙的视线模糊了。他看着父亲,看着那只在夕阳下泛着凄清冷光的碗,看着这间充满了熟悉气息的书房。离别的痛苦,对未知的恐惧,对家族命运的巨大担忧,像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他想哭,想喊,想拒绝,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知道,父亲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是乱世中,一个家族掌门人所能做出的、最理智也最无奈的抉择。
“记住这听雨楼的声音,”沈文渊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抬起手,重重地按在儿子的肩膀上,那力道,几乎要嵌入他的骨骼,“记住你是沈家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梦里,别忘了归路。”
“父亲……”沈墨笙终于哽咽出声,泪水夺眶而出。
三天后的夜晚,没有月光,只有凄风苦雨。码头上灯火昏暗,人影幢幢,弥漫着一种仓皇离乱的气息。一艘前往香港的客轮像一头巨大的黑色怪兽,停泊在浑浊的江水中,发出沉闷的汽笛声。
沈墨笙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略显宽大的西装,站在湿滑的跳板前。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膀,冰冷刺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来送行,这是父亲的意思,怕场面失控,也怕人多眼杂。
只有父亲沈文渊来了。他穿着一件深色的斗篷,站在雨伞下,面容隐在阴影里,看不真切。临别时,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用力地、紧紧地握了一下沈墨笙的手,那一下,仿佛倾注了他全部的力量、嘱托,和无法言说的悲痛。
然后,父亲猛地转过身,决绝地走向了停在不远处的马车,再也没有回头。
沈墨笙在贴身老仆的催促下,一步步踏上摇晃的跳板。他怀中紧紧抱着那个装着银票、地契、玉章和那只影青碗的行李箱。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当他终于踏上甲板,回头望去时,父亲的马车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雨幕和黑暗中。
只有苏州城模糊的轮廓,在夜雨中沉默地伫立着。还有那场下个不停的、冰冷的雨。
汽笛再次长鸣,轮船缓缓离开码头。沈墨笙僵立在船舷边,任由雨水和泪水混杂在一起,流进嘴里,苦涩难当。他望着那片生他养他、如今却正在陷入动荡和未知的故土,一种前所未有的、刻骨铭心的“客”的悲凉,如同这漫天的寒意,将他彻底吞噬。
他知道,他出发了。从一个实实在在的“家”,走向了一场前途未卜的、漫长的“客旅”。
而故乡的雨声,和父亲那句“梦里别忘了归路”,将成为他此后一生,反复咀嚼、却再也回不去的、最沉的梦魇,与最虚妄的慰藉。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认证作家。曾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并参加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创作的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荣获全国“春笋杯”文学奖。
目前,已发表作品一万余篇,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等诗词,以及《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等近二百部长篇小说,多刊于都市头条及全国各大报刊平台。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