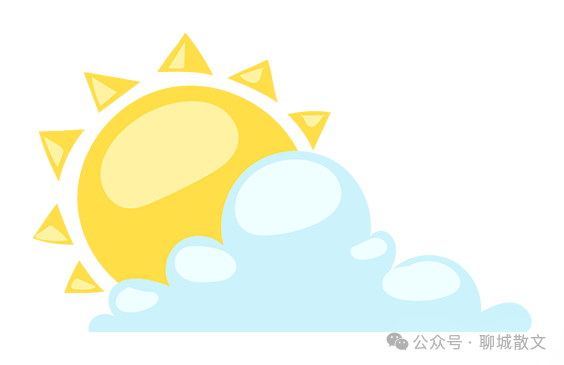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文/老土
留居北京的东阿同乡、军旅作家童村,领我去了一趟宛平城。
作为首都和国际大都市的北京,无论历史的悠远,文化的厚重,还是自然风光,人们可选择要去的地儿很多。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去宛平。宛平于北京,似乎很不起眼儿。
童村约了著名作家王培静,两人早早地来到宛平城的东门等我。这两位老兄经历相似,都是军人出身,培静兄久居北京多年,他老家济南平阴,与东阿就隔着一条黄河,老乡间自然走得就近。
说来不巧,他们事先并不清楚,宛平城正处于半封闭状态,不许游客参观。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宛平城里的主干道和很多重点场所都进行了封堵与围挡,里面正在翻修施工。童村说,我们既然来了,还是要走一走,能看到什么就算什么吧。
童村把自己最美好的几十年生命,都献给了绿色的军营,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军旅文学。虽为军人,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却是温润和儒雅的气质,无时无刻不透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细腻、敦厚与内敛。
来北京之前,我刚好读了他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一篇散文——《去看一条河》。那条河,在东北牡丹江的黑土地上。文章中看那条河的过程,实际是寻着自己军旅生涯中,一段与自己“八女投江”系列小说相关联的记忆,在多年后,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探访,从而产生了一次生命的美妙回流。他的小说取材于牡丹江东北抗日联军中著名的“八女投江”的真实故事,八女投江的那条江,叫乌斯浑河。
几年前,他去看一条河,而这回,又来看一座城。黑龙江的乌斯浑河,和北京的宛平城,相距近三千里,它们本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吧。而此刻,这两者似乎被童村轻松地拿捏在了一起。
其实,同在中华大地这块版图上,又怎么可能八杆子打不着呢,乌斯浑河和宛平城,不就被日本鬼子“一杆子”的枪炮打着了吗?由于城内纵横着正在施工的机械,我们无法从城中穿过,只好折返出了东门,然后沿着城墙向南绕着城墙边走边聊。童村说,我领你去看看卢沟桥。与宛平城西门隔着一条路,正对着的,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枪,就是从这里打响的。
此刻,我一下子领悟到了老兄无意识的用意,这是一种植根于他灵魂深处的家国情怀。作为军旅作家,从事了半辈子军旅文学创作的他,是要让我亲临现场,感受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从1931年开始,由最初的东北义勇军,逐步发展成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军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战斗,无数抗联将士的灵魂,被永远封存在了那片黑土地上。
2016年,为了拍摄一部东阿籍抗联英雄刘海涛的纪录片,我曾带领摄制组专程去了哈尔滨,采访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一位老馆长。镜头前,八十多岁的老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他当年建馆时整理英烈遗物时的情景。而童村“八女投江”系列小说中,八名女战士宁死不降的英雄形象,就是东北抗联这巨幅长卷中的一组镜头。
每年的9月18日,一声长鸣的警报,划破中国的万里长空,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房里持久震颤。
走着走着,我们把同时把目光投向高高的宛平城墙上。古城墙上,是当年日本鬼子用大炮留下的,一个个大小深浅不一的弹坑。我站在弹坑的城墙下,童村为我拍了好几张照片。他拍得很认真,每拍一下,都要打开照片仔细地看,生怕拍得不好,会留下遗憾。
我们能拍到的弹坑,也就城墙上的那么几个,或者几十个吧,而我们看不到的呢,那些划过城墙上空没有留下痕迹的无数炮弹,它们都落在了哪里?可曾有人还记得它们落地的样子?还有那些永远躺在了瓦砾与硝烟中没再爬出来的生灵?
城墙下排列着一个个黑色的圆形大石头,每一个石头上都刻有文字,记录着侵华日军所犯下的累累暴行。童村说,这些叫石鼓,是古代记录战争的一种方式,后人称之为石鼓文。走着走着,就会有三五位老人蹲坐在石鼓间的空地上,或打牌,或下棋,消磨着余下的日子。普通的百姓,也只能在这暴行与暴行的间隙中,苟且地活着。
从那个并不遥远年代过来的人,大都看淡了一切。他们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城墙上的弹坑也大体一致吧,而他们的脸上却多出了几分从容与淡定。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也与那些弹坑一样,有着深深的疤痕,那是无法抹去的记忆。
历史总该被铭记,包括我们用文学的形式。记下,不是为了在人们的心里种下仇恨,而是珍惜和平,阻止战争。在评价童村小说时,有人这样说,叙述战争,不是为了扇动复仇,而是指向反战,这几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战争小说,在描述国家民族危难的同时,开始聚焦战争对平民、对普通人的伤害。
世间所有的战争,真正受苦受难的,受伤害最大的,终还是无数底层的民众。作家不关注他们关注谁呢,文学作品不站在他们的角度说话,又为谁说话呢?这大概才是作家的使命,也是真正的文学面对战争而存在的意义吧。
我们似乎生活在了一个和平的年代,其实,那样一场场残酷的战争离我们并不远。人最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忘记战争的历史,不从战争中吸取教训,提升认知。只有铭记历史,才不会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只有全民对战争认知的提升,才有全民的幸福生活。只可惜,人类总是健忘的,就像此时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战争与冲突,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也许并不是健忘,而是人类骨子里自带的贪婪决定的吧。健忘与贪婪,都是人类的本性,当它们到达了一定的浓度,就会自然地发酵。
面对贪婪的枪口,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奋起反抗,要么跪着求生。奋起反抗,就必然有流血牺牲,跪着求生,就会让贪婪更加肆无忌惮。似乎,战争是一种必然。
童村兄以为卢沟桥在宛城城外,直接走过去,就可以近距离地触摸它感知它。遗憾的是,整个古桥也全被封了,只有施工人员与车辆可以出入,怎么向执勤门卫解释也无法通融。无奈,趁着施工人员出入的间隙,我从敞开的门缝里,向远远的古桥望了几眼,又急忙用手机抓拍了几下,算是到过卢沟桥了。
执勤门卫很客气,要想看就等半年之后吧。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确实值得庆祝,作为重要的国防教育基地和文保单位,也确实应该好好修缮一下。只愿能修旧如旧,保留住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原始风貌。
临走前,我用又手机拍了拍脚下古桥巨大的旧石板。那应该是卢沟桥上最原始的石板,历史的车轮,已经将它们碾压得凹凸不平,却又闪着岁月的光泽。这座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的卢沟桥,800多年来,还知道它到底承载了多少沧桑的岁月,与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只可惜,我的笔力不够,无法对它注入更多的笔墨。
好在千百年来,已有无数文人,为它写下了不朽的诗文佳作。当然还有我的童村兄,还有新结识的培静兄。回来后,在网上查阅后才知道,培静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表了大量作品,九十年代初加入中国作协,至今已出版《军魂》、《寻找英雄》、《编外女兵》、《男兵女兵》等几十部著作。
作品,凝结着作家的灵魂,军旅文学,也必然融入了作家更多的血性与正义。创作军旅和战争题材的作品,并非是赞美战争,而是对和平的渴望,和对侵略者的斥责。正如童村与培静,能走在一起的两个人,不仅仅因为是老乡和作家,一定还有着对事物相近的价值取向。
一场战争中,你为哪一方说话,表达了你的立场。而判断哪一方是正义的,则需要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所以,唤醒才显得尤其重要,唤醒的方式很多,文学就是其中的一种。
距宛平城不远,有一家叫宛平楼的饭店,这是培静兄订好的,我们坐下来点了几道北京菜。前来坐陪的,还有他的夫人,作家沈会芬大姐。虽然我也当过几年兵,也自称作家,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是我望尘莫及的。而共同的军营经历与文学爱好,还是让我们有了更多聊天的话题。当然,宛平城总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在它的脚下。
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中有“燕,宛也,宛然以平之义”,作为卢沟桥的桥头堡,宛平城最初是用于屯兵和保卫北京的。地名中带“平”与“安”字的,更多是寄托着天下太平的一种期许。
而这个宛平,又何曾真正安宁平静过呢?就像卢沟桥上巨大的石板,它最初应该是平坦的,而走的车多了人多了,它就不平了。岁月本身就是凹凸不平的,我们总是期盼世界和平,岁月静好,而这个世界又何时停止过战争?人类,就是在一场接一场战争与杀戮的夹缝中,一点点延续下来的。
身处和平环境里的人,无法真正体验一场战争的残酷。尽管,过去无数和现在发生的所有战争,都有它开战的理由。其实,人们总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战争。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她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那些留在宛平城墙上的炮坑,多么像烙在国人胸膛上的伤疤!而卢沟桥下的永定河水,又多么像从人们胸膛里涌出来的,经过岁月沉淀后平静而舒缓的诉说。
记得那天,沿着宛平城外公园的小径向外走,我看到一对年轻的小夫妻,从停好的车子上下来,五六岁的女儿欢快地跑在他们前面,转眼就消失在了宛平城乍暖还寒的春风里。而我脚下的步子,在那一瞬似乎也有了力量。
(本文获山东省作家协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主题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