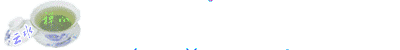心 上 山 水
作者:张庭
这几日,心里总有些莫名的烦扰,说是为事,却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事;说是为人,却也想不起究竟恼了谁。那烦扰便像江南梅雨天里濡湿的空气,黏稠稠地裹着你,挥之不去,挣不脱,只教人觉得周身都不爽利。今日午后,偶又翻到书上的几句话:“苦非苦,乐非乐,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便自在于心间。” 读罢,心口那团棉絮似的郁结,仿佛被一阵清风吹开了一丝缝隙,透进些微光来。我搁下书,踱到窗前,看外面日影西斜,光与影正缓缓地推移,心里便悠悠地想起许多事来。
这“执念”二字,实在是人生牢笼的一把巨锁。我们这一生,似乎总被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去追逐些什么,又或是牢牢攥紧些什么。求不得时,便觉着是苦;得到了,又恐其失去,依旧是苦。那苦乐的交战,竟不在这外物本身,而全在我们心头那一点痴缠的执著。这使我想起佛经上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二僧过河,见一女子踟蹰不敢渡。一僧便背起女子,助她过了河。事后,另一僧一路耿耿于怀,终忍不住质问:“我等出家人,岂可亲近女色?” 那背人的僧者却讶然答道:“我早已将她放下,你怎么还‘背’着她呢?” 这故事真是再透彻不过了。困住后僧的,何尝是那河边的女子?分明是他自己心头挥之不去的念想。他执于“清净”之相,反被这清净相所缚,比起那位坦荡行事、事过心空的同伴,他才是真正被玷污了的人。可见这“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实在是人间至理。
我们的心,仿佛一面奇妙的镜子。心里装着什么,眼中便看见什么。这便是古人说的“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了。同样一座秋山,在杜子美看来,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苍凉;在王摩诘笔下,却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旷。山何尝变过?变的,是看山人的心境罢了。昔时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斗机锋,东坡戏言:“我看你像一堆牛粪。” 佛印却安然道:“我看你却像一尊佛。” 东坡自以为得计,归告苏小妹,不料小妹一语道破:“心存牛粪,看人如粪;心存佛祖,视人如佛。哥哥,是你输了啊。” 这虽是轶事,其理至深。我们眼中的世界,何尝不是自己心性的投射呢?心中若是焦灼,看那花开也觉喧闹;心中若是平和,听那雨打芭蕉,也成了天地间最安宁的乐曲。
如此说来,那人间的万千烦恼,倒真个是“皆由心生”了。我们总以为,是外境的纷扰搅乱了内心的安宁,于是拼命地想去修正外界,想要一个全然顺遂的“顺境”。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最大的执著?《菜根谭》里有句话,我极喜欢:“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这真是自在的法门。风来便来,我自疏疏落落地应着;风过去了,我便恢复那挺直的姿态,不将风声留在耳际。雁子掠过水面,潭中便映出它的影子;雁子飞走了,潭水便复归澄澈,不存一丝痕迹。事情来了,我的心便全然地去应对;事情过去了,心也就随之空明,不粘不滞。这般境界,便是“放宽心态,顺其自然”的真谛了。这“自然”,既是外物的自然流变,也是内心的自然感应,不强求,不抗拒,如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这又让我忆起晚明文人袁中郎的癖好来。他生平最爱山水,曾说:“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 他所谓的闲适,并非懒散,而是一种将心灵从俗务中拔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状态。他看山,能看出山的性情;听泉,能听出泉的言语。他之所以能如此,正因他放下了对功名利禄的执念,将心“放宽”了,这才能领略到天地间无价的“便宜”。这份自在,是那些在宦海风波中紧紧攥着乌纱帽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
由是观之,这“放下”二字,并非消极的舍弃,反倒是积极的解脱。它不是要我们万念俱灰,如槁木死灰般了无生趣。恰恰相反,它是卸下心灵的重担,好让我们更轻盈、更真切地去拥抱生活本身。好比一只攥紧的拳头,除了紧张,什么也抓不住;而摊开手掌,反而能承托清风明月。
一念转变,天地皆宽。我们仍是凡人,仍在这红尘中奔波,仍会遇着顺逆悲欢。但若能时时常保这份觉照,苦乐当前,便知是“一时的执念”,如看镜中花、水中月,虽则真切,却并不实在。那么,纵不能全然如圣贤般“事去心空”,至少也能在烦恼生起时,多一分回旋的余地,多一丝超然的微笑了。
窗外的光,此刻已变得十分柔和,给万物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远处传来归鸟的啼鸣,清脆而安宁。我方才心头那点无名的烦扰,不知何时,已悄然消散了。它或许还会再来,但我知道,它也只是心湖上偶然泛起的一道涟漪罢了。
风平浪静,湖水依旧映照着天光云影。我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茶,轻轻呷了一口,竟品出了一丝前所未有的清甜。
【作者简介】
张庭,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即现在的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曾在机关,银行等单位供职,现已闲赋在家。曾有多篇论文,散文,随笔,发表于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扬州日报,扬州晚报。对文学是喜爱,亦是毕生追求。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