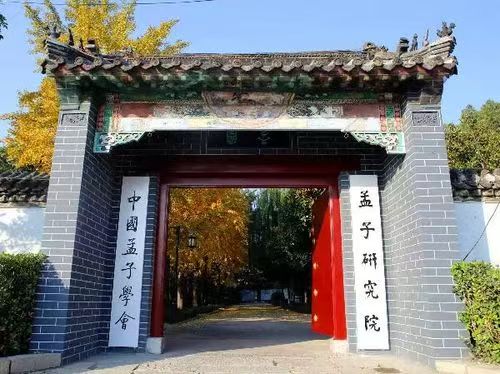承孔启儒 光耀千古
—— 评二月梅《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魏佑湖
在当前学术研究日益追求创新突破与现实观照的背景下,一篇兼具理论深度、实证支撑与思想温度的论文,往往能为所属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引发学界同仁的广泛共鸣与深度思考。“二月梅”的这篇题为《孟子对孔子几个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正是这样一篇极具价值的学术佳作。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儒家思想如巍峨灯塔,照亮了数千年的文明进程。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以“仁”为核心构建起早期思想体系;而孟子承其薪火,在战国乱世的特殊语境下,对孔子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更深厚的现实关怀与理论力量。二月梅的文章以清晰的脉络、深刻的洞察,系统梳理了孟子对孔子“仁”“民本”“人性”三大核心思想的继承与突破,不仅精准把握了孔孟思想的内在逻辑关联,更揭示了孟子思想穿越时空的当代价值,读来令人深感认同,亦引发对儒家思想传承创新的深层思考。
一、从“仁者爱人”到“仁政天下”:孟子对孔子“仁”思想的政治升华
二月梅指出,孟子“仁政”主张的思想源头是孔子的“仁”,这一判断精准切中了孔孟思想传承的核心脉络。孔子以“仁”为道德伦理的基石,提出“仁者爱人”,其核心指向是个体层面的道德修养,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还是“克己复礼为仁” 的行为规范,都聚焦于引导个体在家庭、社会关系中践行仁爱,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倡导。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崩塌,孔子寄望于通过个体道德的觉醒,重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其思想更多停留在“修身”“齐家” 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治国理政方案。
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残酷现实,让单纯依靠个体道德修养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想彻底破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将孔子的“仁”从个体道德层面,提升至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层面,提出了“仁政”主张。这不仅是二月梅所言“最重大的发展”,更是儒家思想从“伦理学说”走向 “政治学说”的关键转折。孟子的“仁政”并非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有着具体的实践路径:在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通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让百姓拥有稳定的生产资料,实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政治上,反对“虐民”“残民”的暴政,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权稳固的根本;在文化上,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通过教育涵养百姓的道德素养,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这种从“爱人”到“爱民”、从“修身”到“治国”的升华,让儒家思想具备了回应时代困境的现实能力。
二、从“尊卑有序”到“民贵君轻”:孟子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大胆突破
二月梅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定义为“挑战皇权的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孟子在君臣关系认知上对孔子的超越。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但仍未脱离“周礼”的框架。他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主张“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甚至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其民本思想更多体现为“重民”“安民”的治国智慧,本质上仍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君主民本论”,目的是通过善待百姓维系君主的统治,尚未突破 “君为中心”的认知局限。
而孟子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等级桎梏,将“民”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一论断,绝非简单的“重民”主张,而是蕴含着“主权在民”的朴素思想:在孟子看来,君主的权力并非“天授”,而是源于百姓的认可。“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种思想直接挑战了“君权神授” 的传统观念,甚至赋予了百姓“革命”的正当性。当君主“虐民”“残民”,沦为“独夫民贼”时,百姓有权推翻其统治,这正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天下大道。正如“汤放桀”“武王伐纣”,并非“弑君”,而是“诛一夫”而安天下。
二月梅敏锐地指出,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宋太祖时期“公开谈论‘民贵君轻’而不受追究”的政治清明,到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再到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不闪耀着孟子民本思想的光辉。这种从“君为中心”到“民为中心”的转变,是孟子对儒家思想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也让儒家思想获得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三、从“性近习远”到“性善四端”:孟子对孔子人性论的理论建构
在人性论问题上,二月梅清晰梳理了孟子 “性善论” 对孔子 “性近习远”的继承与发展,精准把握了两者的理论关联与差异。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探讨人性的思想家,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类的本性具有普遍性、共同性(“性相近”),而个体之间的差异源于后天环境与习惯的影响(“习相远”)。但孔子并未明确回答“人性究竟是什么”,是善是恶?还是无善无恶?这一理论空白,为后世思想家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孟子则直面这一问题,提出“性本善”的论断,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性善论体系,填补了孔子人性论的理论空白。正如二月梅所言,孟子以“四心”为“性善论”的核心依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并非后天习得,而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是人与生俱来的“善端”。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孟子举“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任何人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都会本能地产生怜悯、救助之心,这种不加思索的反应,正是“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也是“性本善”的直接证明。
二月梅将孟子“性善论”与法家“性恶论”对比,指出两者分别为“仁政”与“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分析极具启发性。事实上,孟子的“性善论”不仅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根基,更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它相信人性中存在善的可能,相信道德教化的力量,这种对“善”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和谐社会的精神源泉。即便在今天“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也仍能看到孟子“性善论”的深远影响。
二月梅的文章以简洁有力的笔触,勾勒出孟子对孔子思想继承与发展的清晰脉络:从“仁”到 “仁政”,是儒家思想从伦理到政治的升华;从“尊卑有序”到“民贵君轻”,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革命性突破;从“性近习远”到 “性善四端”,是儒家人性论的理论建构。这三大发展,不仅让儒家思想在战国乱世中站稳了脚跟,更使其成为塑造中国传统文明、影响当代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
孟子的贡献,在于他既坚守了孔子思想的核心精神:对“人”的关怀、对“善”的追求、对“和谐”的向往,又能根据时代需求,突破传统框架,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生命力。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千年的关键。
四、论文的论证特色同样令人称道,其严谨性、逻辑性与实证性的完美结合,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扎实的研究功底。
在论证过程中,“二月梅”始终遵循 “提出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路径,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充分的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避免了空泛的理论空谈。一方面,作者对相关理论的运用精准娴熟,并非简单地堆砌理论名词,而是通过理论的“本土化”“场景化”解读,为问题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清晰揭示了问题的生成机制与内在逻辑,让复杂的问题变得清晰可辨。
另一方面,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更是展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了验证核心观点,通过对案例的背景、过程、结果进行全方位梳理,结合理论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呼应”的论证方式,让论文的观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依据,极具说服力。
“二月梅”的这篇论文,用严谨的论证、深刻的思考与温暖的关怀,践行了学术研究的使命,它打破了既有认知的桎梏,为领域难题提供了全新解答。这份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温度”的论文,不仅是对所属领域的重要贡献,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也是关注时代的需求,让学术成果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论文提醒每一位追光者,唯有以敬畏之心对待学问,以赤诚之心关切现实,才能让学术研究真正拥有穿越时光的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坚实而有温度的印记。我相信这篇论文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吸引更多学者为推动领域发展与社会进步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链接
孟子对孔子几个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月梅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思想最卓越的集大成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儒家思想创发上的影响仅次于“至圣”孔子,被世人称为“亚圣”。
孟子出生在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的战国时代,比孔子小179岁。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孟子出生和成长在那个时代,不可能不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所以,他和孔子比起来,其思想体系虽然是一致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创新、很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比孔子的思想更丰富、更实际、更深刻和更有社会价值。因此,研究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孟子思想。
孟子思想极其丰富,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儒家思想创新体系。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孟子》一书中,也就是《孟子》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这七篇阐述的内容十分浩繁,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概括起来,从对孔子思想创新发展的层面讲,我感到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仁”而来的“仁政”主张
施“仁政”,是孟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根本的要义,就是强调君主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慈的政治措施,要求统治者要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争取民心;反对欺压百姓、残害群众,反对暴政。强调只有施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并还告诫统治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认为能施“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这也和老子强调的“人之患在于有为、国之患在于重刑”的道理是一致的。施“仁政”的观点,其思想来源就是孔子所倡导的“仁”。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强调“仁者爱人”。实际倡导的是道德个人主义,就是要爱人,而这种爱人并不是爱一两个人,而是要爱所有的人。而孟子的“仁政”思想,则是把孔子强调的“仁”所处的个人层面,上升到了群体层面、国家层面,把“仁”作为了一种治国理念、治国之道。所以,这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发展。当然,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动荡不安,他的“仁政”观点在当时没能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但他为后人治国还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秦二世而亡,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法苛暴,失去民心。后来,很多朝代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政权稳固后都是采取了施“仁政”的治国之策,如汉文帝、汉景帝都是采取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国内政策,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也由此带来了“文景之治”。当然,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无不与广施“仁政”有很大的关系。
二、挑战皇权的“民本”思想
这是孟子最鲜明的历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其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而奠定了他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这句话的重要意义,首先,他突破了孔子一贯强调的上尊下卑、尊卑有序、君君臣臣,“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愚民政策、愚民思想,打破了君臣常规,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重大突破和有力扬弃。其次,他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就没有君主。第三,为后世治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引领。特别是在宋太祖时期,人们都可以在大街小巷上公开谈论“民贵君轻”而不受追究,因而,宋太祖时期也是一个政治特别清明的时期。以至到后来,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第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现在,习近平同志又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所有这些,都应当是来自于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的这一观点,对历代明君治国、对推动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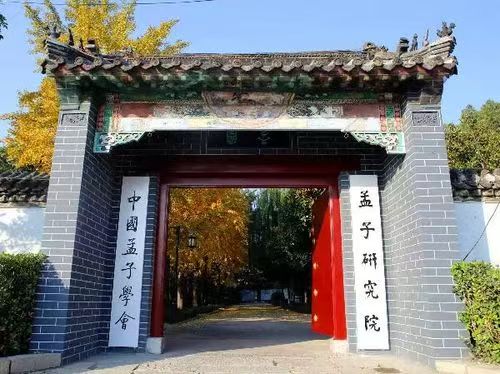
三、独树一帜的“性善”理论
“性本善”是孟子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认识论的基础和重要的世界观。他强调“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他认为性善是由“四心”所证明了的。关于恻隐之心,其中说到,人们看见小孩爬到井边,不用谁说就会自动地去救他,这就是心善的本性;羞恶之心,人们会自动地用衣服遮避身体,羞恶感与生就有;恭敬之心,尊老爱幼,孝敬老人与生即来,就是野兽都是如此,虎不食子,人就更不用说了;是非之心。对待事物人们总有一个生来就有的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所以,孟子始终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当然,他也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正是因为他有了“性善论”这个认识基础,认为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善良的,所以,他才主张要施“仁政”、要以民为本,这些政治主张皆来源于此。性善论是对孔子“性近习远”的继承和发展。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承认有人性,但并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人性是善良的。围绕性恶和性善的问题,历来都有两种不同认识的争论,最典型的就是法家,如韩非子就始终主张性本恶,强调人一生下来就是恶的,比如小孩生下来吃母亲的奶,吃不出水就咬母亲一口等;人都有欲望,比如食欲、情欲、贪欲等等,是很难靠自己控制的。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用法规来限制和遏控人们的欲望。这也就是强调法治。性恶论是法家严刑峻法的基础。我个人认为性本善、性本恶都有道理,但也都有偏颇的一面,更主要的还是要靠后天的教育、环境的影响等。在性恶、性善谁为本源上,我感到还是性善要多一点,因为人类经过了上亿年的进化,他们自然的、原始的本性已经得到改造,人已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了,他体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属性,善良的东西还是要多一些,邪恶的东西要少一些。所以,我更多的赞成孟子的观点。
四、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点
重义轻利是孟子所奉行的重要价值观。他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告子上》一文中还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明确的表明了孟子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概况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义利并重、以义为先。他在与梁惠王的交谈中就已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义”与“利”相比较,应把“义”摆在前面。二是义利矛盾,以义为重。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若不符合道义,应当是虽利不受,始终以“义”为重。三是义利冲突,舍利取义。当“利”和“义”相冲突时,要保持自我尊严,不惜牺牲生命来换取“义”。孟子的义利思想源于孔子的义利观。孔子不反对“利”,但强调“利”要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强调“义”要大于“利”,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的人是君子,重“利”的人是小人。孟子则强调的是舍身求“义”,所以更高于孔子的义利观,孟子是真正的大君子。孟子的义利观激励了后代无数的仁人志士,舍其小家为大家,像霍去病就说过,“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南宋宰相文天祥,抵制了金人高官厚禄的诱惑,誓死不投降,英勇就义,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我们党新四军军长叶挺,皖南事变被捕后,蒋介石以高官厚禄一再劝降,叶挺将军丝毫不为所动,在狱中写下了《囚歌》,一下坐了5年牢,体现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高尚情怀。这些都是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典范。所以,孟子的义利观对后人思想的引导塑造,所给予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五、刚直磊落的独立人格
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柔”的学问,强调的是柔和、中庸,和为贵,特别是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上一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如孔子一生都强调要“克已复礼”,恢复周朝的礼仪典章。但孟子这方面就与孔子有很大不同。一是睥睨王者、踔厉风发。面对君王总是意气昂扬、刚直不阿、磊落恢弘。如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体现着这种性格和胆魄,一般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他还指出:“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认为不必屈于权势,君臣之间地位上由差别,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二是尚志自立、不媚权贵。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强调人要有志气,不迁就、不迎合、不献媚。同时还强调,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要做到不失志,经得住艰难的磨砺。指出:“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认为只有经受得住艰难困苦,才能担当大任。三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也是孟子最著名的独立人格精神,他指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强调在诱惑面前守住节操,不因贫贱改变志向,不向武力低头屈服。认为大丈夫要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刚强不屈的人格形象。孟子强调的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特别是直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像方志敏、江竹筠、赵一曼、杨靖宇等,都是坚守气节的典范。孟子强调的这种人格精神,在新的时代仍然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自觉地坚守,认真地践行,不断把中华民族的这种高尚的精神发扬光大。
六、 教以人伦的教育理念
孟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40岁以后,游说各国,到过宋、鲁、滕、梁等国,最后又回到齐国,被齐宣王聘为客卿,也就是不任职而论国事。因齐宣王不肯实行孟子的建议,孟子遂告老还家,专意讲学。孟子的教育思想在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拓展,特别是在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形成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孟子的教育:一是在教育对象上,由普通百姓发展到君主。他特别注重对君主的教育,如《孟子》七篇,有两篇讲到对君主的教育,即对梁惠王、滕文公的教育。二是在教育方式上,由一般的讲解到思辩教育。孟子是伟大的思辩家,很善于雄辩,把思辩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去,注重说理、逻辑性强、语言犀利,极大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三是在教育目的上,由教授知识到明确提出“明人伦”。孟子提出:学校要“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使学生懂得并遵守道德规范、培养自觉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的君子、圣贤。从而大大增强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的作用更为明显。孟子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教育影响也是深远的。如我们党就特别注重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各级都有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就是教育封疆大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些教育思想,很多都能从孟子教育思想中找到渊源。

(写于故乡邹城,2025年9月15日修改于泉城济南)
作者简介,二月梅,山东邹城人,研究生学历,山东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