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文|文竹
一个世纪一百年,早年感觉那么长!
半个世纪五十年,早年感觉那么长!
不知不觉,淄博师范文史一班毕业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了!
早先听到“缘分”这个词,总觉得肉麻。
后来想到“缘分”这个词,总觉得亲切。
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我们都是一粒尘埃。五十多粒尘埃遇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史一班”,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1973年9月至1975年7月我们在淄博师范文史一班两年的学校生活,我写过一篇文章,详见公众号【大荒经纬】文竹的《我又上学了》。
1995年10月28日,淄博师范1973级文史一班毕业二十周年在张店聚会,我写了一篇文章,详见公众号【大荒经纬】文竹的《我们风华正茂》。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我们的群主刘莉莉同学在文后留言:三十年前我们风华正茂,今年离校五十周年了,我们都老了,但我们身体尚可,虽不能为社会做贡献了,但我们还能为儿孙服务。我们享受着国家给的退休待遇,过着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趁现在身体还好,期待再次相聚。我们班的才子刘上恭同学在文后留言:文竹的文章让我们回到了近三十年前的师生聚会现场,回到了近五十年前在学校读书学习的情景。尤其对几位老师的描写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如同见到了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那是青春烂漫的时期。
2025年10月12日,淄博师范1973级文史一班群里下了通知——毕业五十周年之际,10月20日中午在张店聚会。
看到通知,情不自禁的就一幕一幕回忆起来:
大概应该是刚入学不久,休息日,我到商家公社戴家庄走姨家。姨与我谈论起我到张店上学的事,我说:“俺有个同学蒋化彪老师还是您商家公社的呢,杨家涡的。”姨说:“杨家涡离俺庄挺近面!你不去找你同学玩玩啊?”我于是拿着花一块钱买的两包周村烧饼(强起空着手吧),到了杨家涡蒋老师家。蒋老师不在家,其夫人和几岁的儿子在家,夫人漂亮,儿子帅气。大概十几年前,杨明銮同学和刘上恭同学到淄川蒋老师家玩,蒋老师在其楼房附近的饭店宴请老同学,持顺、鸣鸾和我应邀赴宴。宴后,蒋老师、明銮、上恭、持顺到我的陋家坐了一会儿,我用我那仅仅是能拉响的二胡水平,呕哑嘲哳的为蒋老师伴奏,蒋老师唱了一段吕剧,声情并茂,韵味十足。
上学期间,忘记了是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是到淄博一中或是淄博三中听课吗?活动结束,庞继芬同学邀请我们几个女生到她家玩,我们就坐车去了山头她的家。正好庞大爷刚蒸了全麦粉大卷子,并且馇了一锅渣豆腐,我们每人一碗渣豆腐,每人一个大卷子,吃得那个香啊!至今回味无穷。
才女崔玉玲同学,毕业前学校安排她给我们班讲课,讲的是韩非子的《五蠹》。她教态自然,普通话极好,音色也美,“股无胈
毕业前夕,同学们常常周末这家那家的去玩。陈淑贞同学拿了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跟我到了我家,晚上我们住在我奶奶宅子的西屋里。相貌少相的淑贞晚年搞器乐,弹奏得很好。只是她谦虚,只在群里发过一次。
在分配问题上,我的祖辈父辈和我本人,理想很低——“磁村公社中学”,距离我家刘瓦庄五华里,连距离故乡十华里的淄博十中也没有去想。没想到分到了淄博四中,距离故乡三十华里。家人们都觉得离家太远,我则有些举目无亲的感觉。
那年代的联系方式是写信。1975年毕业后,我给班主任朱秀德老师写信说抽空去看他。朱老师的夫人纪大夫是淄川医院收费科的会计,他们的家在淄川医院职工宿舍。中秋节前,我拿了两包月饼,打听到了纪大夫的家。朱老师不在家,纪大夫在绵被子,棉花绒子飞满屋。我向纪大夫说了我的姓名和单位,匆匆告辞。几天后,我提了一网兜苹果,到淄川酒厂找同学翟秀清玩。到了酒厂,一说翟秀清的名字,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她的家。不巧,秀清母女不在家。秀清父亲翟大爷热情的让我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我说:“翟大爷,我叫孙凤玲,我是翟秀清的同学,我分配的单位是淄博四中,今天来找秀清玩玩。”然后,我把苹果倒在八仙桌上,把网兜缠悠缠悠攥在手里,向翟大爷告辞。
那一年,王明芹同学到淄川找我玩,我通知了淄川的娄艳玲。我在淄博四中对面的淄川饭店请同学们吃饭。饭后,我急匆匆去吧台付款,被明芹一把揽住,我挣脱动弹不得。明芹向吧台扔下一张大钞,拽着我就往楼下跑。过后我想:那四菜一汤是花不了一张大钞的,不知两位营业员女士如何瓜分那多余的钱(一笑)
工作多年后,娄艳玲同学从老家岭子公社的学校调到了淄川北关小学,我们交往较多,详见公众号【大荒经纬】文竹的《我的三位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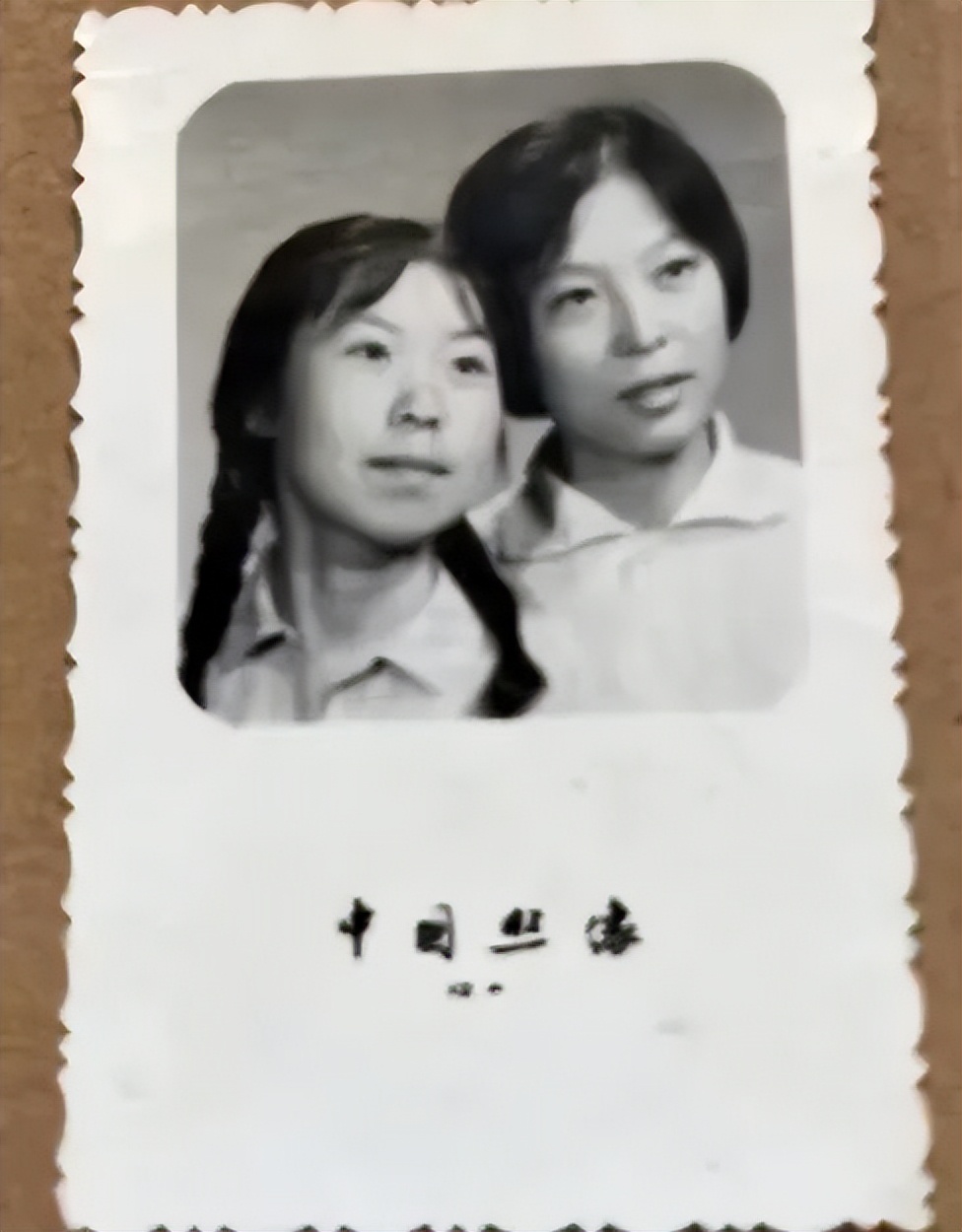
1975年毕业前夕作者与同学鸣鸾的合影
我和程鸣鸾同学交往最多,详见【大荒经纬】文竹的《初试养老院》等篇目。今从我文章中选出下面这一段,作为“代表作”吧。
要回忆的很多,暂写至此吧。
五十年聚会,我心驰神往,但因故我不能参加,遗憾!遗憾!写下这篇文章,以作纪念。预祝聚会圆满成功!
2025年10月13日于静虚庵

用ai想象一下聚会的场景

作者简介
文竹,原名孙凤玲,女,淄川人。中学从教三十余载,学文教文作文化文,俨然“文痴”。其书斋始名“苦竹斋”,后名“静虚庵”,遂自号“静虚庵主人”。退休十余年,犹笔耕不辍,坚持以诗意情怀来对抗琐屑庸俗的现实生活,不断开拓生命的新境界。其文笔清新自然,情感真挚细腻,意境雅致悠远,体现了她对世界、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其为文为人脱然不俗,展示了老一代语文教师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