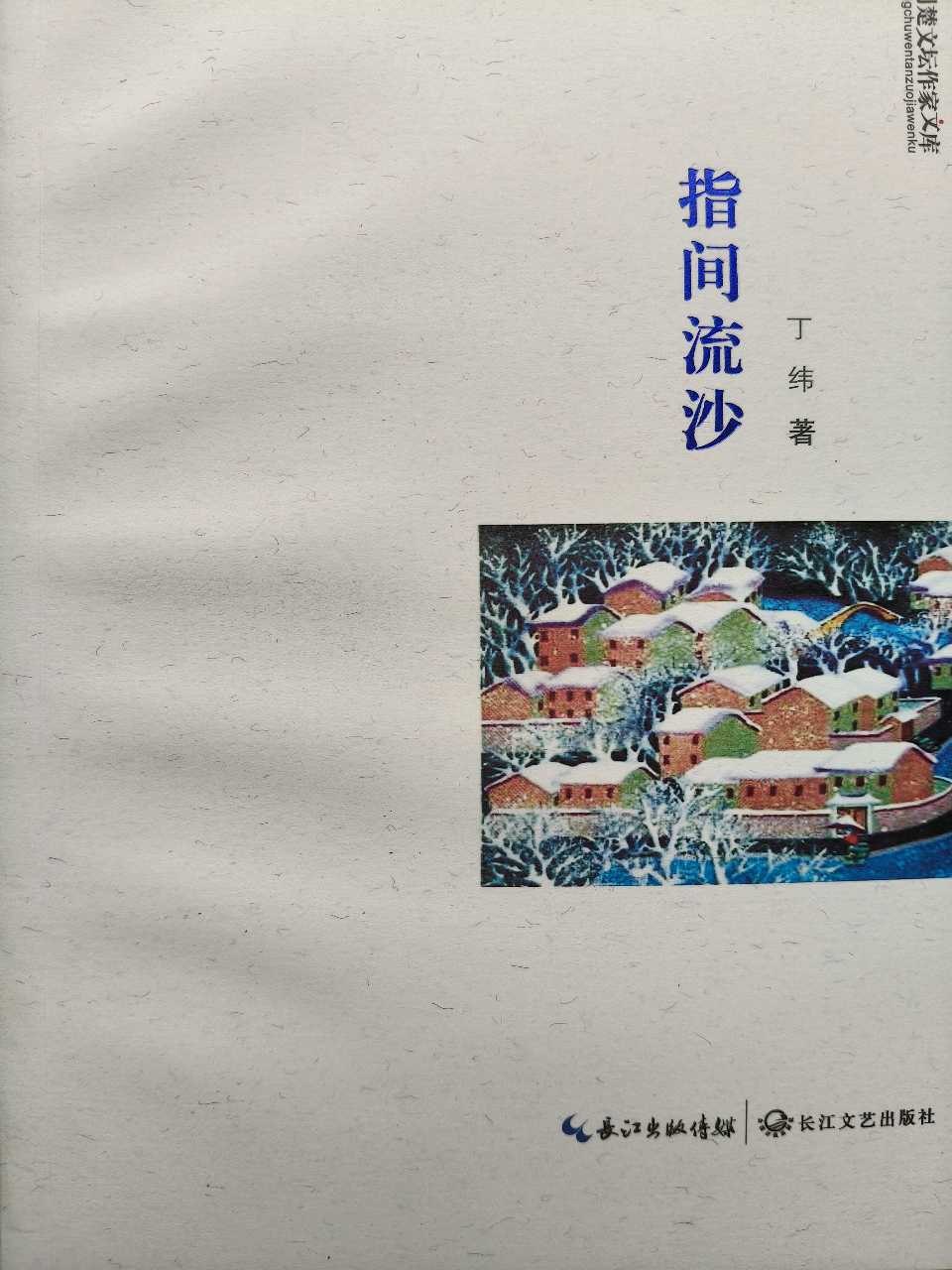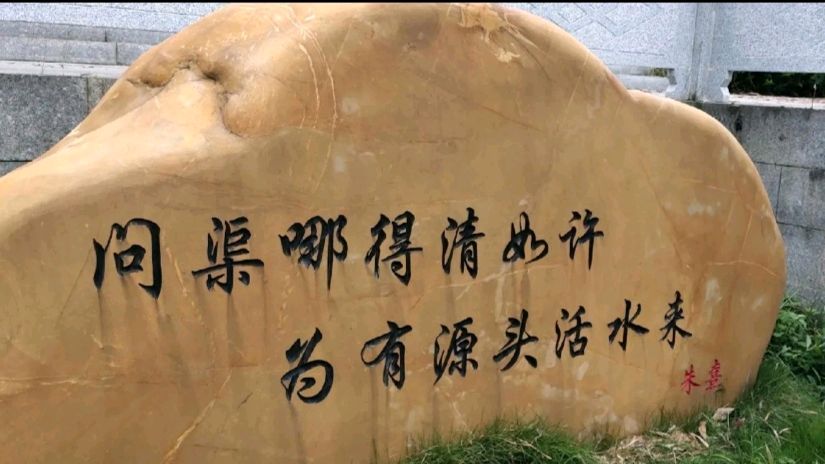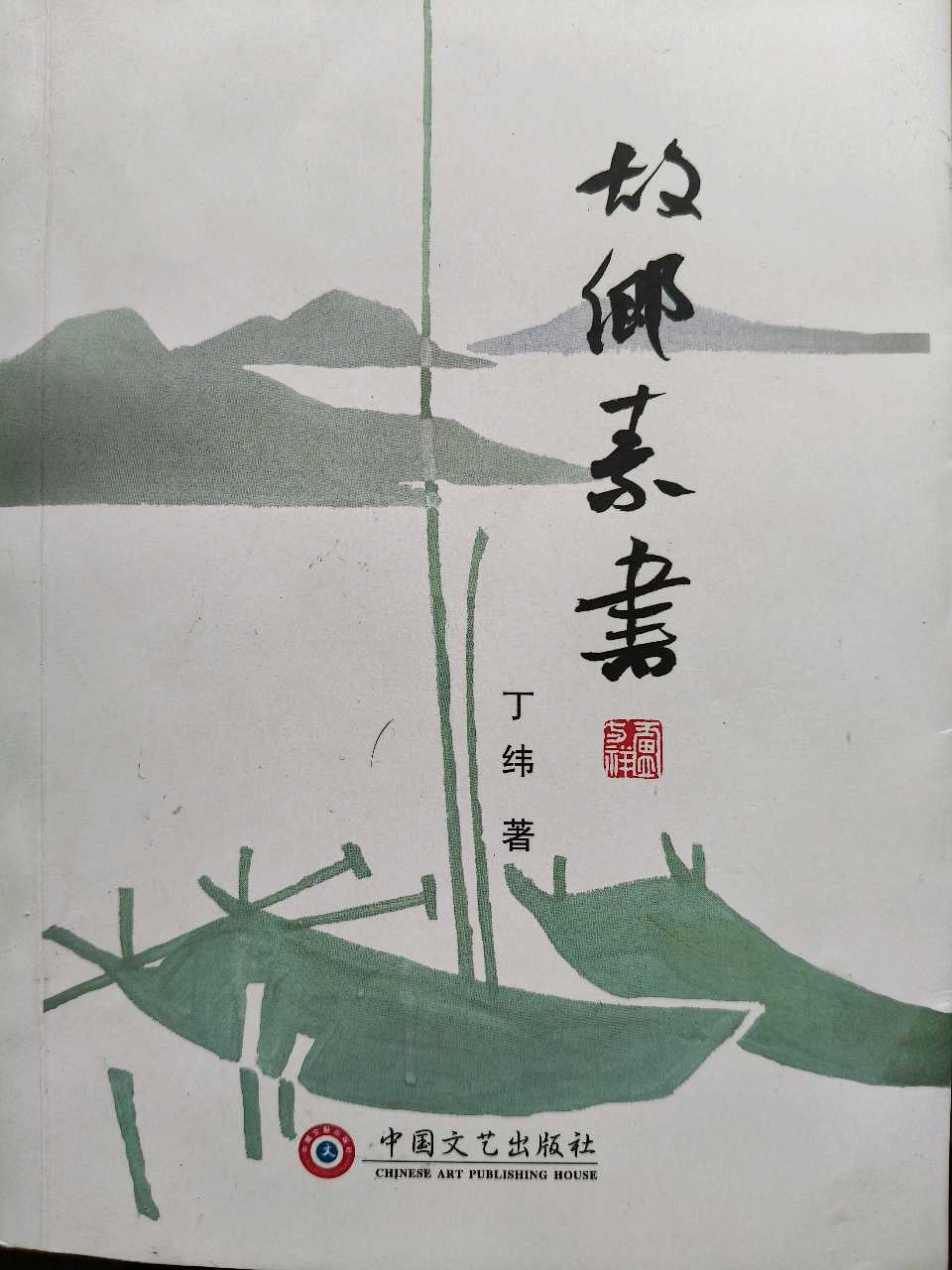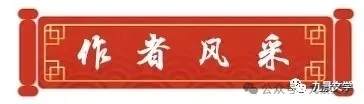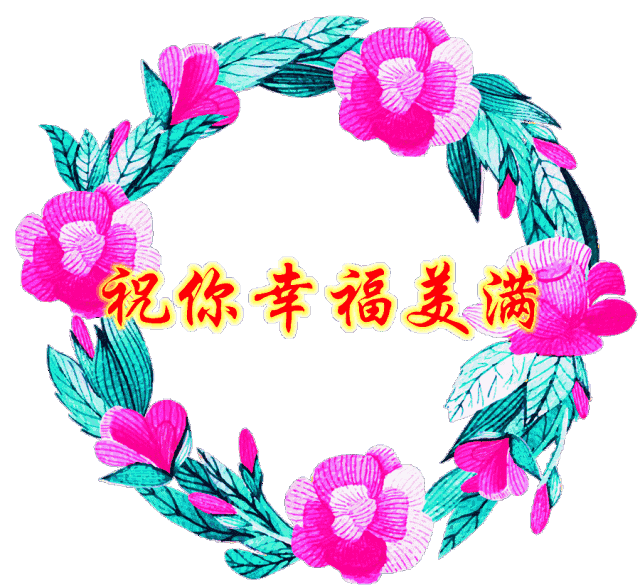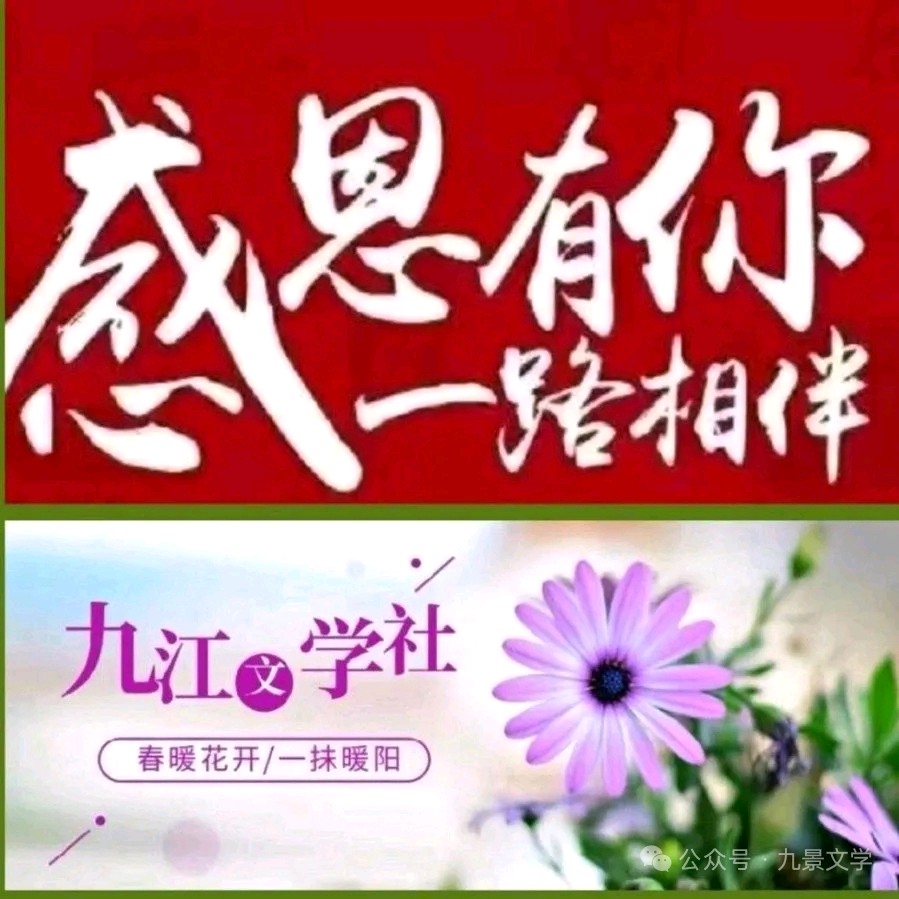问渠那得清如许
-----从几个文学常识谈丁纬的创作
多年来,我阅读的文学作品大致源于两处:一处是优质读本,如《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刊》;一处是身边文友的原创。文友多,原创也多,不可能一一拜读,所以有选择性。简而言之,我选择的标准一是作者确实与我私交甚笃;二是文章也确实不错,值得一读。符合前一个标准的不少,符合后一个标准的也有一些。但同时符合两个标准的就不多了,丁纬是其中之一。
认识丁纬有些年头了,具体始于哪年哪月哪日缘于何事记不清了,应该是公事。那时候丁纬担任市安监局局长,我正在市国土部门从事矿山管理工作,矿山企业最是需要安全监督的,所以我俩的工作就有广泛的交集。总体而言,我的性格偏内向,不大喜欢交际,也不大善于交际,但和丁纬打了几次交道,便希望能和他长久地交往下去。究其原因,一是他友好厚道;二是他诚信踏实;三是他斯文儒雅:都契合我的交友观。认识不久,我便知晓他热爱文学,这一点我们更是意趣相投,于是友谊更有理由延续下来,直至今天,也必将直至永远。我们的交往没有尊卑之分,却有长幼之序——他比我长五岁,我的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
一、情感,文学的灵魂
认识丁纬后,我无意听到或有意打听到他的一些情况: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爱好文学,业余创作,并具备深厚的写作功底,常有作品见诸报刊。我很崇拜,尽可能地找到那些报刊一饱眼福。可是,这样的阅读究竟是零散的,不全面不系统,对他的创作没有一个整体的认知,直到弄来他的两本散文集。
时至今日他一共出版了三本书:诗集《长江黄河之恋》,再就是那两本散文集《指尖流沙》和《故乡素书》;编纂了多部期刊和文集;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他的诗是早年写成的,诗集也是早年出版的,那时候我们都年少,还不相识,也没有拜读那本诗集,姑且不谈。但对他的散文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出版社所为,按照文章的内容,八十三篇的《指间流沙》被分门别类为七辑:“赤壁我家”“山高我为峰”“寥廓江天”“人间情怀”“百味人生”“读与思”“时光十三章”;八十二篇的《故乡素书》则为八辑:《故乡素书》《亲情缱绻》《灵肉走笔》《时代报告》《知青往事》《草木融情》《风物揽胜》《庚子特稿》。仅从这些编目就能看出,他的文章涉及面广,恨不得包罗万象,读后我惊叹他的深邃阅历和博闻强记,更佩服他的情感丰富、细腻和炽热。
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情感的,一幅漫画是,一曲小调是,一支劲舞也是,而其中尤以文学艺术最为突出。没有情感的文学作品好比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即使五官再端正身材再匀称也激发不了人们的热情和好感。文以情动人,这是一个常识。
既然如此,谈论丁纬的文章如何具备感情色彩似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反正像样点的文章都能做到这点,有什么值得言说的呢?可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方面丁纬的文章尤显突出。石器是笨重的,粗糙的,实在缺乏美感,然而在丁纬的笔下,家乡的石磙、石臼、石磨却有血有肉,亲切感人。老实说,“乡村石头记”看起来像一篇介绍劳动工具的说明文,而说明文相对来说可读性不足,可是我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很快就投入了,沉浸了,因为这些仿佛从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石器,承载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勤劳、智慧、执着和艰辛,我从字里行间里读到了作者对他们的无限深情。“
如今,我选择了远方。当我风雨兼程追求生活的彼岸,故乡的公路却像慈母的双臂,永远向我延伸,期待游子的归来。”《故乡的公路》“老屋闪烁独有的风韵和气象,在风吹雨打中弥久不衰。如今,它卓然不语,注视着村庄的变迁。”《舍不去的青砖黛瓦》“在密密的深林里,我看到生命的节奏。每一棵树都载起一颗灵魂,载起亲人的惦念和记忆,弹唱生命的歌,跳起生命的舞。”《安歇的灵魂》“那绿树掩映的古街永远撑起我心灵的一片蓝天;古街驴蹄踢踏、骡子磨米的跫音常在心中回荡。天涯那么远,走在路上,耳边常能听到家乡的风声,听到亲人的乡音。”《古村驼岭情韵》“如今父母早都灯枯油尽,去到一个不再需要油灯电灯的地方。但父母消瘦而疲惫的面容,常在我眼前浮现。”《故乡的灯》 这些发表在《学习强国》平台、《散文选刊》、《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厦门文艺》上的散文,无不饱含作者的深情。
丁纬的文字是由情感凝结而成的,但叙述的语气却自然,平静,一点也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毫无“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
二、写作,是一门手艺
写作,是一门手艺。
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出自当代作家贾平凹之口。此前的近代和古代是否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不得而知,但自从有了写作,这一事实便一直存在了。
我们知晓应该将某件衣服搁放在衣柜的哪个格儿里,知晓多高的饭桌大致配置多高的凳子,可是很少有人知晓衣柜和桌椅该如何打造出来,因为不需要,我们不是木匠。上完小学就能阅读“红楼梦”,但能写出“红楼梦”的,自古及今只有曹雪芹一人;我们身边几乎人人都能阅读,但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作家毕竟只是少数。
既然写作是一门手艺,写作也就有门道有诀窍了。
首先脑子里一定要装有一定数量的词汇,这就好比要做一件家具得有原材料一样,木头、铁钉、油漆之类。词汇从哪里来?平时读书积累而来,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捷径可走。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里说她七岁时写小说,够天才的吧?可是常常遇到不会写的字词要去问家里的厨子,可见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后天学习的。丁纬的童年和少年处于文革时期,读书无用,但是到了一九七八年,文革结束了,时代完全变了样,他开始疯狂读书学习,像是对童年和少年虚度光阴的忏悔。这些他在“第一站”“悠悠蒲师情”“武科大,心中的圣殿”等作品中均有记叙,读后令人动容。他在知识的海洋里涉猎最深最广的还是文学,多年不辍,一生不辍,很年轻时就颇有造诣。所以我自从开始阅读他的文章,后来又系统地带有研究性地通读他的文集,也没能找出几处有毛病的字句。而诸如“捕鱼野趣”等篇章中字词运用的准确、简洁、生动,则即使入选中小学生课外读本也当之无愧吧。
相对于遣词造句,文章的结构更为重要,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写作功力。人们都说,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远高于其他三部名著,确实如此。别的不说,仅其结构就远比其他三部复杂得多。“西游记”的整体布局是线性的,故事是按照师徒四人取经的顺序展开的,这就显得相对简单了。倒不是说,简单的结构就缺少艺术性,而是用这种相对简单的结构来构建“红楼梦”根本行不通,因为“红楼梦”里的人物太多,故事太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这种宏大庞杂的叙事即使如吴承恩这样的文学巨匠,怕是也驾驭不了,只有曹雪芹一人才能完成。
那么,文章究竟应该怎样谋篇布局?
答案是:没有答案。
“那段求学路”是一篇叙事散文,分为四节。第一节写的是作者高中毕业后到当民办老师前的田间劳作;第二节写的是当民办老师时的教学和生活,以及稍后的高中文化补习;第三节写的是跳出龙门,考入蒲圻师范学校;第四节写的是继续深造,考入武汉科技大学。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条理清晰,读来一目了然,轻松自如。或许有人会说,就不能不按这个顺序来写吗?比如第一节就写他考入高等学校学习,再在后面插叙他如何当上民办教师的,又如何考进师范学校的,等等。当然可以,问题是就篇文章而言,需要设置悬念来倒叙吗?需要卖关子来插叙吗?都不需要,就这样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地叙述,最适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整体布局科学合理,便省却了一些笔墨,文章显得简洁洗练,这就好比某项工程设计得科学合理,就能节省原材料一样。略举一例:还是那篇“那段求学路”。第一节写我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很自然地牵扯出父母以及三个哥哥,也就是说在没有另行文字的情况下,向读者介绍了家人情况,增加了文章的内容,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说情感是贴在丁纬文章上的醒目标签,那么,简洁便是他的文章的又一大特色,一大亮点。“
榨杆被高高地抛起,重重地砸下。飞起万钧之力,撞出雷霆之声。‘榨床’的小槽汩汩流淌‘黄金雨’,一滴一滴漫入心沛。”《油榨坊》“废铁再次送进炉膛,拉风箱,夹起,用大锤小锤对打。如此不断反复,方方的岁月被锻打成圆形,圆圆的岁月又被锻打成方形。”《铁铺轶事》 这是发表在《中国散文家》上的一组散文,简洁而细腻地描绘了乡村生活。
简洁,不同于简单。
三、美,既相对又绝对
无论在什么人的眼里,鲜花都是美丽的,这是美的绝对性;在黑人的眼里,黑皮肤的美女大有人在,但是再美的黑人在我的眼里却不美,估计在不少白种人和黄种人眼里也是如此;同样,许多白种美人和黄种美人在黑人眼里,也是不美的,这是美的相对性。美的相对性还包括: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是美的,但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却不美;反之亦然。
这是实物在人类的大脑里引发的审美效果,那么,艺术之美也能引发同样的审美效果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写过小说,偶尔也拿到一些内部刊物上交流,每每刊发出来总有几个读者叫好,并且还能有板有眼地道出叫好的理由。是真好还是假好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他们读过。可我的女儿几乎从来不读我的文章,尽管她很喜欢读书。原因是我写的故事多发生在乡下,而乡下的事她根本不熟悉,“农村的家长里短就是这样的吗?”有次她好不容易翻了两页又随手扔掉了。
我表示理解。美是生活,美是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而农村的一切对于女儿来说,都是空白。
可是后来,她还是读了我的小说。我问怎么回事,你不是一直没去乡下生活吗,怎么突然对乡下的故事感兴趣了?她说她读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后,就喜欢上农村题材的小说了。她接着并没大谈“白鹿原”,而是谈起我的一个小说叫“香喷喷的国军太太”。这是个仅有二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二0一0年刊登在中国最基层的县级刊物《赤壁文学》上。讲的是文革时期,一个生产队长带领贫下中农种粮食的故事,另有一条副线说的是他和本生产队里的一个国军遗孀的情事。女儿说,她最欣赏那位队长说的一句话,“无论社会发生了什么,也永远改变不了最基本的事实:人要吃饭穿衣,人要生儿育女。”她说老爸的这篇小说她不想妄加评论,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讴歌了人性之美。“
人性之美不分时代,不分种族,不分地域,更不分城乡,永远闪耀着最温暖的光辉!”她说,“老爸有一双发现真善美的慧眼呢!”那时,她刚从铁路学院毕业参加工作。
然而,当我通读完丁纬的散文集后,想起女儿评价我的话,觉得丁纬的一双眼光才叫深邃,才叫开阔,才叫慧眼识珠。
“乡村石头记”前面已经讲过,就不说了。“木桶”堪称其姊妹篇,介绍的是几件木制的容器:板桶,斛桶,饭桶,水桶,屠宰桶。写作风格和“乡村石头记”差不多,初看也像乏味的说明文,但越品越有味道。“油灯照亮的乡村”“老屋四题”等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生生把那些呆板的老古董写得活灵活现,活色生香。而更令我叫绝的还是“洋名”。
“洋名”说的是母亲称呼许多物品,总要在其前面冠以“洋”字:洋火、洋布、洋芋、洋姜、洋车等等。文章说母亲那辈人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她们所用之物多有舶来品。这且搁置不论,也不论这篇文章如何颂扬了母亲的勤劳和母爱的伟大,单说我读完这篇小文之后,禁不住泪目了。因为我想起了我的早已作古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称呼家什的,“把门角落的洋锹拿过来。”“帮我把洋线穿进针眼,老妈的眼睛看东西模糊了。”“灯灭了,浪费洋油。洋油贵着呢!”如今人们都在喊记住乡愁留住乡愁,“‘洋’名”就蕴藉了遥远的乡愁……丁纬的文章里,随处可见冷僻的不为一般的作者和读者在意的素材。
疫情期间是最令人压抑的一段日子。丁纬同样能用极美的文字展示生活、展示自然,在无奈的日子里寻求着春光。“广场上空无一人。静寂的山茶花耀不亮眼睛,沁人心脾的梅香让人打不起激灵。广场四周的门店紧闭,那卷闸门像一块块盾牌,时刻抵御上空的‘黑云’入侵。”“此刻,每一顶帐篷都是防控的营寨,每一盏灯都是城市的眼睛。那低旋的‘蝙蝠’在窃窃私语,却无力偷袭铁桶般的小区。”《打开春天的门》 这是丁纬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一组抗疫日记,曾获市级非虚构文学一等奖。
从写作层面上讲,这是一个选材的问题;从文艺评论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艺术审美的问题。能够如此独到审美的作家,必是个上了档次的作家;出自这样作家的文字,也必不会肤浅。
问渠那得清如许?相信丁纬在文学活水的滋润下,文学水平将会达到更高的层面。
作者简介
谢培武:湖北石首人,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干部,自由撰稿人。发表十多部中短篇小说、一部长篇纪实和一部电视连续剧。
主编:洪新爱
组稿:放飞 石 慧
编辑制作:放飞
图片主要来源于网络侵权告知即可删除。个别图片由作者提供。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