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间诗话》是作家陈本豪先生的一篇散文佳作。文章以春末夏初的相聚为引,借酒兴谈诗,深入剖析诗人与诗歌的紧密联系。作者以海子、孙膑、司马迁等为例,阐述诗人应执着于诗歌创作,即使面临困境与磨难,也要坚守阵地,用热血浇灌诗歌之花。炳阳的执着与悲壮,更彰显诗人对诗歌的至高追求。此文不仅展现了诗人对诗歌的热爱与执着,更传递了对诗歌的敬畏与礼赞,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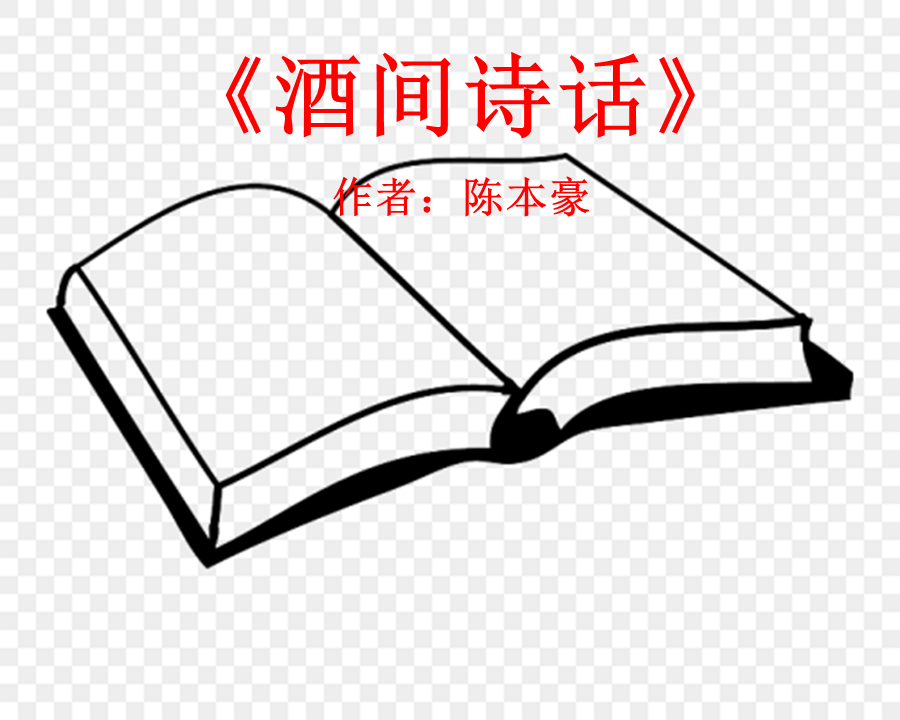
酒 间 诗 话
陈本豪 春末夏初的一天,朋友们相聚谈天,酒一到位情趣便高涨起来,几位不是诗人的人,却谈起了与诗歌有关的话题。有一位说,人说诗人是最有智慧的人,我看很多诗人都不大正常,甚至像疯子。小弟斜眯着眼接过话头说,这句话真还被你说对了,假如诗人都像你我一样,世界上恐怕就没有诗了。小弟从不写诗,却读懂了诗人,他的那句话不啻(chì)是对诗人的认可,且充满了理解与情感。诗人就是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应该有别于常人。特别是在诗人写诗的时候,心中的激情足以冲破世间万物对他的约束,他的心中只有诗意的寻求与灵性的表达。
海子以死而谢天下,他为诗歌而死,也为诗歌而生,令所有爱诗的人敬仰。但对诗歌而言,他的死却是一种消极的逃亡,诗歌更需要执著而健康的诗人,没有诗人就没有诗歌。昨天的诗歌无可阻拦地走进了历史,今天的诗歌却只能靠今天的诗人以热血去浇灌。
海子义无反顾地走了,却把他的诗歌孤独地留给了世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令诗歌更加高贵的悲剧。孙膑被剐去双膝,他却毅然地活下来而立著兵法;“哀莫大于心死,辱莫大于宫刑”的司马迁,承受了非人的痛苦与屈辱,却依然写下了《史记》。也许,海子真不该走的。一个战士为了坚守阵地,抛洒热血或献出生命,无疑具有伟大的意义。假如那个战士即使是浑身浴血却能与阵地同在,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欢欣与鼓舞,只要生命存在,就能继续创造。
炳阳是一位很有建树的诗人,他几乎把所有都给了诗歌,除了诗歌,他还有什么呢?1979年1月4日深夜,在一个无人无月的旷野,他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对着苍天豪饮,眼内噙着泪对上帝说,我的生命永远属于诗歌。一个曾经温暖的家破了,孑(jié)然一身,流浪漂泊,但他依然不停地写诗。他很瘦弱,却很精神;他虽然贫穷潦倒,却活得悲壮。他相信,用心血来喂养诗歌是一种崇高,用热血浇开的花朵比太阳更加鲜艳。他天天与诗为伍,步步当诗,与人群的世俗似乎越来越远,与诗歌却越来越近,他的灵魂几乎已与诗歌的内在融为一体。
“我的家就在我的体内”,炳阳像蜗牛一样把整个家背在背上,用它透明的声息在夜幕下呵出一道道发光的内在之痕。他带着浑身的痛在黑夜里碰撞,让磷火点燃心灵的孤灯。他勇敢地与死神对视,昂首挺胸,像一匹四蹄生烟的烈马,让灵魂艰难地脱壳,让黑暗在体内变成烛光。他用自己的肋骨搭建高台,供奉诗歌的头颅。一颗诗歌的诗心,一颗诗人的诗心,在相互激励中存活,诗人让心跳的频率与诗性的灵动和谐地奏出诗魂的乐章。
无论何时,只要尝到酒,就想借酒痛吟炳阳的诗;只要触摸到诗,就想起醉卧在诗中的炳阳。人间有喝不完的酒,也有写不尽的诗,只要有酒,只要有诗,诗人就无处不在。
作者简介:陈本豪、中作协会员、音乐家,籍贯武汉江夏。已出版散文集三部,纪实文学集七部。长篇纪实文学《京剧谭门》全四卷,被列入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八届湖北文学奖。由选择来诠释与宽博他的含义,则有待未来时空的论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