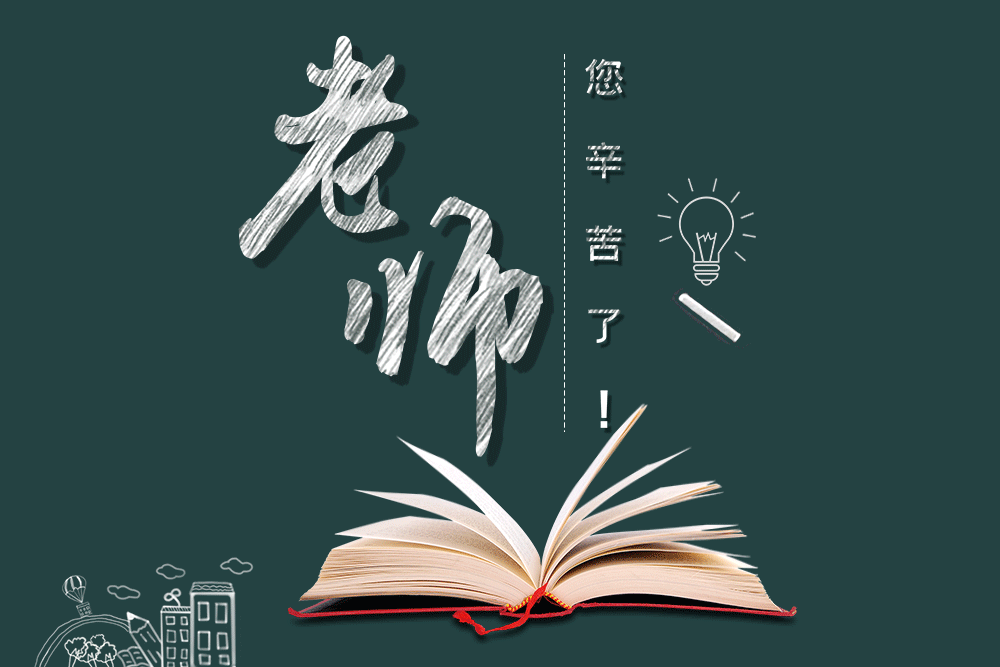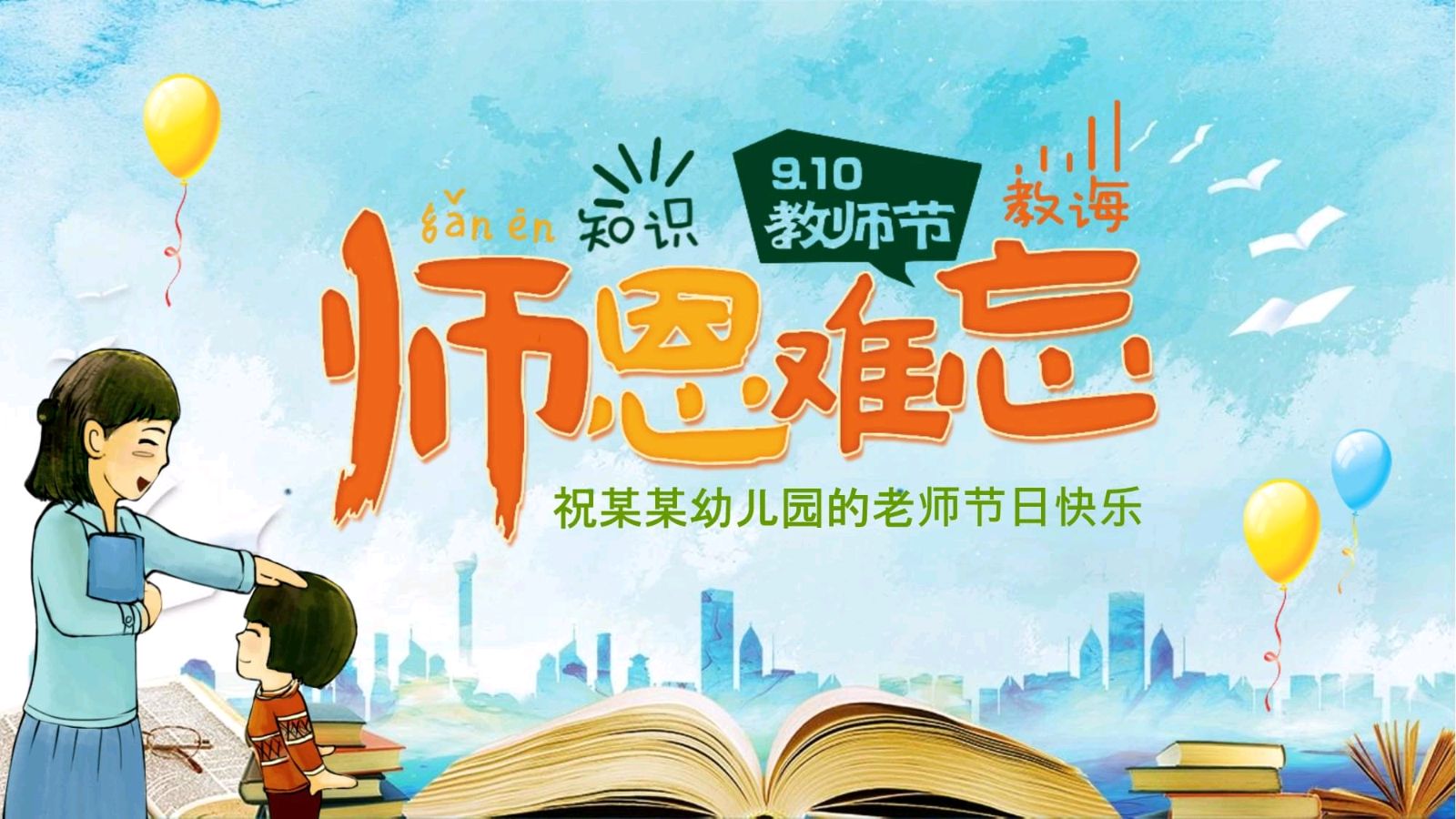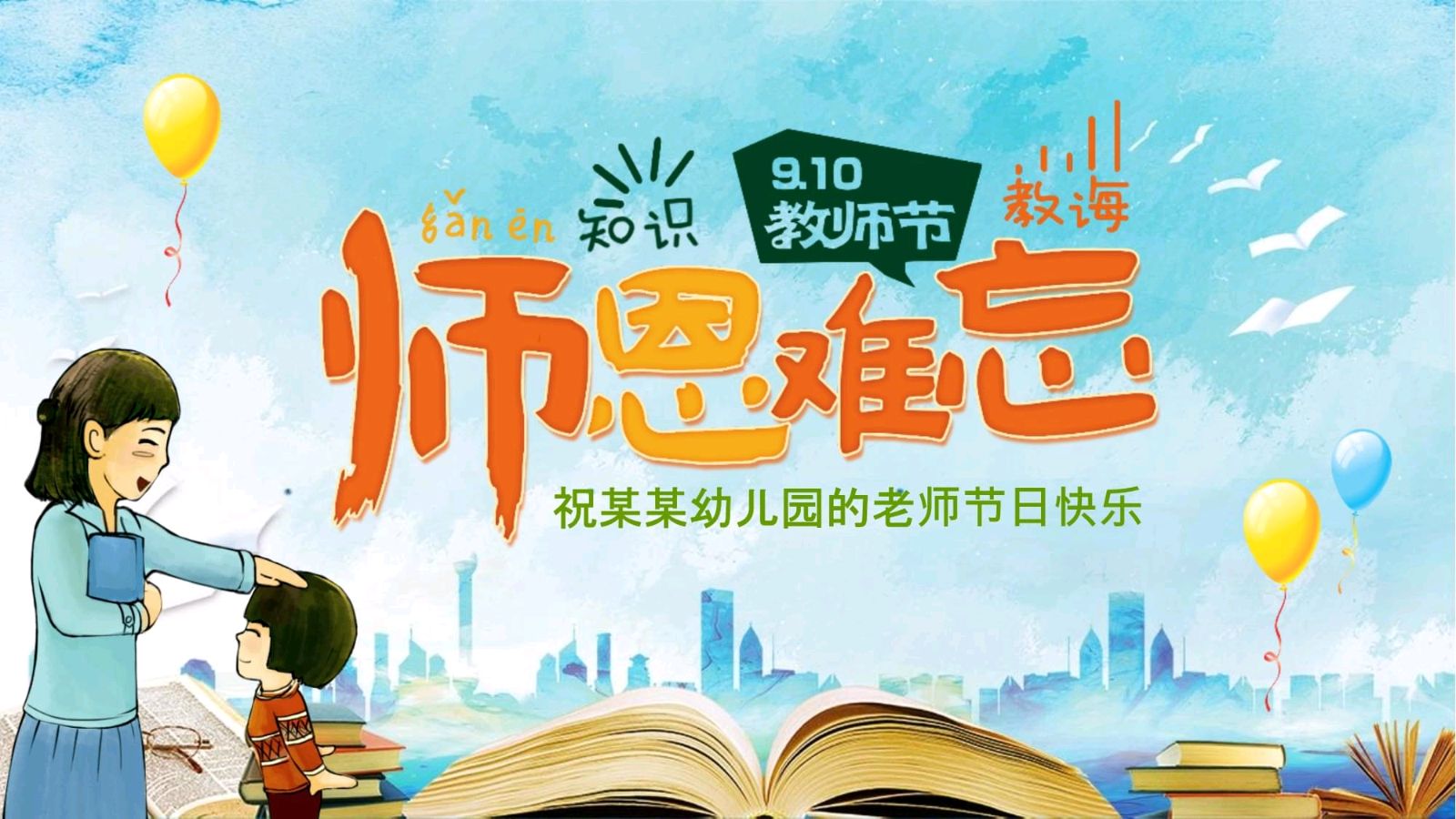白先生
---献给我曾经的老师一
文/邹 冰
先生姓白,名曰银玉,三个字皆有光,闪闪发亮。听村长先一天说,白先生要来村里教书,第二天,他的名字连同他本人一同光芒四射就降临在村口的小学里。
学校重新开门,他的名字和娃伙的读书声让灰不踏踏的山村小学亮堂起来。村里的小学一亮堂,整个村子也跟着亮堂,显得格外有生机。白先生课堂里高声领读《我爱北京天安门》,教我们唱《小松鼠快长大》《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娃伙们兴奋地摇头晃脑,双手背后,仰着脖子卖力地大声跟着念、跟着唱。
学校有了书声、歌声,大人们喜悦,一大早忘记了上工,肩上扛着锄头,一群人立在那儿雕塑一样裤腿挽得很高,麻杆一样的一双腿一下一下在打节奏。
村民们站在学校门外看风景,听娃伙们唱这么好听的曲儿,嘴角上扬,心里流淌着蜜糖,眼里点燃了一把火。
七十年代末,偏僻山村念书的人本来就少,先前小学里一个教师,他是本家的大叔,有年在沟里捡了一头肥猪,折一根柳树枝吆猪去了公社。公社意外得一头肥猪,书记说,教书要先育人,育人比学知识要紧。
斗大的字识得一箩筐的大叔,去村里学校当了老师兼校长。村里大人们说大叔脑袋里面装的那些墨水,走路一晃荡都能听出响声。
村长说,老大虽胸无点墨,却给娃伙们传递一份善良,也是幸事。
一日,大叔忽的得了中风,学校没有老师了,学校大门便自然关了。
白先生是乾县城关镇人,县里选调来在村里暂时接替大叔当老师。先生一身灰色的中山服,白塑料镜框的眼镜,雪白的衬衣扎在腰间。四十多岁的人,走路轻快脚下带风,显得十分干练。
白先生脑袋里是一片海,知识装得瓷实,走路是听不见响声的。
白先生双手背在身后走在村道里面显得威严、高贵,满村道全是“先生好”的问候声,先生不停招手,像检阅士兵的将军。
。白先生在村里教娃伙们识文断字,万能的村长披着夹袄,幌着两个空荡荡的袖管,昂首阔步挨家挨户下任务。
村长耷拉着一张驴脸霸道地安排先生吃派饭。村长说各家必须拿出招待丈人的饭菜招待先生。
先生第一次来我家吃派饭,老爸摸黑下沟进城割肉买米。
父亲说先生是文曲星上门,家里会沾上先生的文气,娃伙们会兴旺发达。
学校晨读一毕,我领先生来家里吃饭,白先生进大门在院井里弹了一下脚面上的灰,拍打了一下中山装,拱手给父亲说:“自己人,家里吃什么,碗里盛什么,就添一双筷子。”
先生嘴上这样说,父亲还是翻箱倒柜拿出藏着的、掖着的、准备过年走亲戚的花生大枣招待先生。
我们家的早饭和村里人家一样千篇一律——一碗小米稀饭,一把地里揪来的蔓菁菜。绿油油的菜叶在开水里焯了,放葱花用热油一激,香味便弥漫开来,在窑里窜来窜去。炕桌上的盘子里放的却是两个白面馍馍,是一大早上母亲、大姐专门上笼屉蒸好放在盘子里用白布苫了的。
早饭简单午饭就有分量,是一盘莲花白炒肉片,一盘凉拌红萝卜丝,一碗雪白的蒸米饭。
先生说,都是山里的人,面条的肚子,吃不惯大米饭,也不用那么讲究。
午饭有荤腥,晚饭一碗米汤泡馍,先生喝小半碗小米稀饭,剥了锅灰里煨的红苕,就着父亲喝很酽的茶,吧嗒着嘴吃得很香。
父亲见先生吃得畅快,吃得高兴,饭毕,父亲让先生给当兵的大哥写了一封回信。
信写罢,先生来了兴致,提笔写了一幅对联,父亲用浆糊贴在窑门上:
上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是:五洲震荡风雷激。横批是:转革命促生产。
先生来了,村里的标语显得有文化,写在土墙上斗大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比先前的字有力量,看着也顺眼。
先生来学生家里吃派饭,学生们欢欣鼓舞,大人们却暗中较劲,互相打听,变着花样做给先生吃,其实,也没有啥山珍海味,全是家常饭,只是这一家和另外一家换一个花样而已。
先生也不生分,吃过饭,盘腿坐在炕上和村民拉家常,帮村民代笔写信,提笔写对联。
先生越是客气,越是没有架子,大人们压力越大,老是想着给先生做好吃的。
先生第一次来家里吃派饭时,父亲进城割肉,又轮到来家里吃派饭,父亲和母亲思谋着做点什么好饭给先生吃。那时候物质匮乏,两人也是犯难。
我和弟弟四目一对,去沟里的那条河里摸鱼。先生在课堂上讲过,世间好吃没过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山里跑的。旱塬上的娃没有下过水,在河坝里打开一个缺口用竹笼去接,忽然蹦出一条大鲤鱼来。四岁的弟弟性急跳进坝里,鱼是捉到了,人却滑倒在坝里,河坝溃堤了差点淹死他。沟里的大人帮忙救下弟弟,弟弟脸上划出一道很长的口子,肚子鼓胀如鼓,那条鲤鱼却一直在弟弟怀里抱着。
第二天白先生来家里吃饭看见弟弟脸上有伤,父亲支支吾吾不肯说。
家里中午吃的是清炖鲤鱼,大姐请教过村里的知青,锅里只撒了一把盐,飘几片葱花。
先生挑起一筷子让我尝,我含在嘴里,鱼肉太腥,刺也多,我“呸”地吐了,看来,先生口里的鱼肉好吃是一条假信息。
晚上先生来家里吃饭,叫我到大门外,先生眼角闪着泪。
先生说:“娃啊,老师不是客人,是家里的人,以后不敢这样干,老师担心呐。”
这之后,先生来家里吃派饭,家里吃什么他吃什么,加菜加肉他转身就走。如果按照特殊标准待客先生,先生宁可饿着肚子一天不吃饭。
后来,县城和村里之间修了一条大桥,先生每天可以骑车回家,再后来,先生放弃调回县城的机会,在村里教了一辈子书。
先生不认得我了。
作·者·简·介
邹 冰 男 笔名 四眼周,关中刀客。1963年出生陕西乾县一农户家里,1981年冬季应征入伍,在河西走廊当兵21年,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军区《西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2001年转业陕西省政府工作,退休之余,重拾写文章的爱好,有幸加入散文协会成为会员,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青年作家》《人民日报》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若干,2020年《一个人的秦腔》荣获《中华散文》一等奖,出版散文集《特色》《雁塔物语》,现居西安曲江新区。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