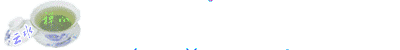茶烟里的缘分
作者:墨染青衣
第一章 茶香氤氲
弘一法师的话总让我想起城南那家老茶馆。那茶馆有个极雅致的名字,叫"一味轩",取自"万味归一"之意。木格窗棂滤进的阳光里飘着茶末,八仙桌的漆色剥落成地图模样,茶客们来了又走,像极了法师说的"稀薄寡淡"的缘分。
我初到一味轩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那时我刚从北平回到南方,带着满身疲惫和一颗破碎的心。老茶馆的门槛被岁月磨得中间凹陷,我抬脚跨入时,铜铃轻响,迎面扑来的是陈年茶香与木质家具混合的气息,仿佛一下子跌进了时光深处。
跑堂的老周从雾气中探出头来,他约莫五十出头,脸上的皱纹如同茶树的年轮,深浅交错。见我生面孔,他并不急着招呼,只是用那双被茶烟熏得发红的眼睛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默默指向靠窗的一张空桌。那桌子临着天井,光线正好,又不直晒。
"先生喝什么茶?"老周的声音沙哑,像是被茶水浸润过。
"随便什么好茶。"我那时对茶道一窍不通。
老周嘴角微微上扬,转身离去。不一会儿,他端来一只白瓷盖碗,碗身绘着青花山水,釉面温润如玉。"这是今年的明前龙井,先生慢用。"
我揭开碗盖,只见茶叶在水中舒展如初醒的蝶,茶汤清亮如春水。第一口入喉,苦涩中带着回甘,竟让我想起北平那位已经嫁作他人妇的姑娘。从那以后,我成了这里的常客。
每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窗棂,在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时,我便拣个临窗位置坐下。老周很快摸清了我的喜好,不必开口便端来白瓷盖碗,有时是碧螺春,有时是铁观音,偶尔还会推荐些稀罕的品种。他说茶叶如人,各有性情,需得用心体会。
茶馆的常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靠墙那对下棋的师徒。老者姓陈,据说曾是前清的秀才,后来家道中落,靠教私塾为生。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举手投足间仍保留着读书人的气度。少年叫阿明,是隔壁绸缎庄的学徒,十五六岁年纪,眉清目秀,下棋时总爱咬着下唇。
他们每天对弈三局,雷打不动。老者执黑,少年执白,棋子落在楸木棋盘上的声音清脆悦耳,与茶馆里其他声响交织在一起——跑堂的吆喝、茶客的谈笑、卖花女的吴侬软语,还有门外偶尔经过的黄包车的铃声。这般光景,倒应了弘一法师那句"相伴一程已是万分感激"。
我常常一边品茶,一边看他们下棋。老者教棋极有耐心,每走一步都要讲解其中道理。"棋如人生,"我听见他对少年说,"落子无悔,就像人不能重活一遍。但棋局可以复盘,人生却只能向前。"
少年似懂非懂地点头,眼睛却始终盯着棋盘。有时他会突然走出一步妙招,让老者捻须微笑;更多时候是陷入长考,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而老者从不催促,只是静静地等,偶尔啜一口茶,目光越过少年的肩膀,望向远处,仿佛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茶馆里还有一位特别的客人,是位穿月白衫子的姑娘。她总在午后出现,坐在离评弹台最近的位置,点一壶碧螺春,十指纤纤转着青瓷杯,眼波比杯中的茶汤还清。我听老周说,她是城东柳家的独女,名叫柳如烟,在女子师范读书,酷爱评弹。
后来茶馆里多了个穿学生装的青年,总是"恰好"坐在柳姑娘旁边的桌子。他叫林书白,是省立中学的教员,教西洋文学。开始时两人只是点头之交,渐渐地,青年会借故请教评弹的典故,姑娘则问他新诗的含义。霜降那日,我看见他们合撑一柄油纸伞离去,伞面上积着金黄的银杏叶,像极了弘一法师说的"只要同行的时候是快乐的"。
第二章 萍水相逢
前日茶馆里来了个穿西装的商人,公文包搁在条凳上,不经意间压着本《饮水词》。邻座戴圆眼镜的先生瞥见,忽然吟了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商人闻言抬头,两人目光相接,竟同时笑了出来。
"先生也喜欢纳兰词?"商人问道,声音里带着惊喜。
圆眼镜先生推了推镜框,点头道:"纳兰性德词情深不寿,最是动人。尤其这一句,道尽人间聚散无常。"
"正是!"商人激动地拍了拍桌子,引得周围茶客纷纷侧目。他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在下李景明,做点小生意。没想到在这茶馆里能遇到知音。"
"敝姓赵,赵砚之,在书局做编辑。"圆眼镜先生拱手道,"李兄是做哪行生意?"
"主要经营茶叶和丝绸,偶尔也涉足些金融业务。"李景明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烫金名片递给赵砚之。
我在邻桌听着他们从纳兰性德说到江南织造,又从《红楼梦》里的茶道谈到汇丰银行的股价,话题跳跃得令人眼花缭乱。赵砚之知识渊博,谈起古籍版本如数家珍;李景明见多识广,说起各地风土人情绘声绘色。两人越谈越投机,竟忘了时间流逝。
"赵兄,我明日要去上海谈一笔生意,恐怕要半月才能回来。"临别时,李景明有些不舍地说,"回来后定要再与兄台畅谈。"
赵砚之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正是他自己校注的《饮水词笺》手稿。"李兄若不嫌弃,请带上这个路上解闷。"
李景明接过,如获至宝,当即从西装内袋取出一支金笔相赠。"这是我在瑞士买的,一直没舍得用。今日得遇知音,正好相赠。"
我望着他们消失在门外的背影,茶烟袅袅中忽然明白,原来缘分不必似古树盘根,亦可如萍水相逢的欢喜。老周过来给我续水,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轻声道:"这李老板上个月才第一次来,说是路过避雨,后来就常来了。赵先生倒是老主顾,五六年了,每次来都带着不同的书。"
"他们之前不认识?"我有些惊讶。
老周摇摇头,提着铜壶走向另一桌。壶嘴吐出的白汽在阳光下形成一道小小的彩虹,转瞬即逝。
半个月后,李景明如约而至。那天正下着细雨,茶馆里人不多。赵砚之已经在老位置看书,面前摊着一本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李景明风尘仆仆地进来,西装下摆还沾着泥水。
"赵兄!"他快步走到赵砚之桌前,从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包裹,"这是我在上海旧书店找到的,想着你一定会喜欢。"
赵砚之解开包裹,是一套光绪年间的《昭明文选》,品相极佳。他抚摸着书页,手指微微发抖。"这...这太贵重了..."
"比起赵兄赠我的《饮水词笺》,这不算什么。"李景明爽朗地笑道,随即压低声音,"其实这次去上海,还打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最近动作频繁,恐怕..."
赵砚之神色一凛,示意他噤声。两人凑近低声交谈,表情越来越凝重。我隐约听到"战事"、"早做准备"等字眼。
那天之后,他们见面的频率更高了,有时甚至会约在茶馆打烊后长谈。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大概:李景明利用经商之便,为抗日力量筹集物资;赵砚之则通过文化界的关系,传播救国思想。谁能想到,一段因《饮水词》而起的缘分,竟会发展到这般地步?
第三章 棋局人生
靠墙的棋桌旁,陈老秀才和阿明的对弈仍在继续。但最近我注意到,老者的咳嗽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要停下棋来喘息半天。阿明总是担忧地看着老师,递上手帕和热茶。
"先生,要不要去看大夫?"一天,阿明终于忍不住问道。
陈老摆摆手,从怀中掏出一个青瓷小瓶,倒出几粒药丸吞下。"老毛病了,不碍事。"他指着棋盘,"来,继续。这局你下得很好,有望赢我。"
阿明咬着嘴唇,犹豫道:"可是先生身体..."
"下棋如做人,要有始有终。"陈老的声音虽轻,却不容置疑。
那天阿明果然赢了,是他第一次战胜老师。陈老不但不恼,反而欣慰地笑了。"青出于蓝啊,"他轻拍阿明的肩膀,"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
"先生别这么说!我还差得远呢。"阿明急道。
陈老摇摇头,从怀中掏出一本手抄的棋谱,纸张已经泛黄。"这是我毕生心血,收录了古今名局三百余谱。本想等你出师时再给,现在看来..."他咳嗽几声,"你拿去吧。"
阿明双手接过,眼眶发红。"先生..."
"记住,棋道即人道。"陈老语重心长地说,"落子前要三思,但一旦决定了,就不要后悔。赢要赢得光明,输要输得磊落。"
第二天,陈老没有出现。第三天,阿明独自坐在棋桌前,摆着一局残棋。老周告诉我,陈老病重卧床,恐怕时日无多。
一周后,绸缎庄的伙计来告诉阿明,陈老去世了。那天下着细雨,阿明在棋桌前坐了一整天,面前的茶水凉了又换,换了又凉。傍晚时分,他忽然自己跟自己下起棋来,左手执黑,右手执白,落子的声音在安静的茶馆里格外清脆。
老周给他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藕粉,轻声道:"吃点东西吧。"
阿明抬起头,眼睛红肿,但神情平静。"周叔,我想继续在这里下棋。可以吗?"
老周拍拍他的肩膀:"当然可以。陈老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
从那以后,阿明每天都会来茶馆,有时一个人研究棋谱,有时教其他茶客下棋。他渐渐长成了挺拔的青年,但眉宇间总带着一丝忧郁。我想,那是对逝去恩师的怀念吧。
第四章 战火纷飞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时,茶馆里一片哗然。李景明和赵砚之面色凝重地低声交谈,不时在纸上写着什么。
"真的要打起来了?"有茶客不安地问。
李景明站起身,环视众人:"诸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李某虽是一介商人,也愿尽绵薄之力。"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传单,"这是抗日救国会印制的,请大家广为传播。"
赵砚之也站起来,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文化界同仁已经行动起来,我们书局正在筹办抗战刊物。希望有识之士踊跃投稿。"
茶馆里议论纷纷,有人热血沸腾,有人忧心忡忡。老周默默地给大家续茶,眉头紧锁。
随着战事扩大,茶馆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常客中有的参军去了,有的举家逃难。柳如烟和林书白也来得少了,听说他们加入了地下抗日组织,负责印刷传单。
一天深夜,我已经睡下,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满身是血的林书白,怀里抱着昏迷的柳如烟。
"求您...救救她..."林书白声音嘶哑,"我们被特务盯上了...如烟中弹..."
我连忙让他们进屋,简单包扎了柳如烟的伤口。她伤在肩膀,血流不止。林书白告诉我,他们的印刷点被破坏,好几个同志被捕。
"我们必须离开城里,"林书白说,"但如烟这样..."
"我去找李景明,"我说,"他有办法。"
李景明果然神通广大,连夜安排了一辆救护车,把柳如烟伪装成传染病患者送出城。林书白执意同行,临别时紧紧握住我的手:"大恩不言谢。若他日...我们还能活着回来..."
我目送救护车消失在夜色中,心中五味杂陈。弘一法师说得对,怎么走散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同行时的温暖。
战争终于波及到我们的城市。空袭警报成了家常便饭,茶馆的窗户贴上了米字形的防震纸条。老周在院子里挖了个防空洞,空袭时就招呼茶客们下去躲避。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防空洞里,突然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等我们爬出来时,茶馆的一角已经被炸塌,瓦砾遍地。
"大家没事吧?"老周焦急地清点人数,突然脸色大变,"阿明呢?"
我们四处寻找,最后在废墟下发现了阿明。他怀里紧紧抱着那本陈老给他的棋谱,已经没有了呼吸。原来空袭时,他想起棋谱还放在茶馆,冒险回来取...
老周跪在阿明身边,老泪纵横。我从未见过这个坚强的老人如此崩溃。他轻轻抚摸着阿明的脸,哼起一首古老的摇篮曲,仿佛阿明只是睡着了。
战争改变了一切。茶馆重修后,柜台多了台留声机,老周的儿子用铁皮壶换了电热炉。对弈的角落还在,但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棋声。我想起弘一法师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忽然发觉茶凉了。窗外卖玉兰花的阿婆换成了卖糖炒栗子的后生,香气却一般暖人。
第五章 茶凉人散
战后,我偶尔还会去茶馆坐坐。老周老了,跑堂的换成了他的儿子小周。茶馆重新装修过,添了不少新式家具,但老主顾们都说少了点什么。
李景明和赵砚之战后都失去了音讯。有人说李景明去了香港经商,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在敌后运送物资时牺牲了。赵砚之据说随学校内迁到了西南,后来怎样就没人知道了。
柳如烟和林书白也再没出现过。有人说他们在延安,也有人说去了南洋。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因为战后有人在一味轩留下了一个包裹,里面是那本《飞鸟集》,扉页上多了一行字:"感谢这个茶馆,让我们相遇。"
如今我渐渐学会像对待茶渍般对待缘分。青瓷杯上的茶垢要留三分才显岁月,洗得太净反倒失了滋味。就像柜台后那面被无数茶客衣袖磨亮的红木,或是门口青石板上深陷的脚印,都是万千过客留下的"好的相遇"。
暮色漫进茶馆时,跑堂开始收拾茶具。白瓷盖碗相碰的清脆声响中,我忽然想起那个总坐在槐树下喝茶的云游僧人。他临走前用茶水在桌上画了个圆,说:"缘起性空,如露如电。"当时不解,现在看着茶汤里自己晃动的倒影,倒明白了七八分。
人生确如弘一法师所言,是"随风而舞"的缘分。那商人或许正在洋行签合同,戴圆眼镜的先生大概在书斋校勘古籍;月白衫子的姑娘可能已为人母,学生装的青年许是在南洋经商。但此刻茶香氤氲,新来的茶客正与跑堂说笑,阳光依旧斜斜地切过青砖地。
缘起时如春茶初沏,缘尽时似残茶冷却。我们这些世间客,不过是在光阴的茶馆里,借一盏茶的工夫,品味那些"好的相遇"罢。
第六章 茶烟未尽
茶馆重修后的第一个雨天,我撑着油纸伞站在门前,望着那块新漆的"一味轩"匾额发呆。老周的儿子小周正在柜台后擦拭茶具,见我驻足,连忙迎出来。
"先生来了!里面请。"小周比老周活络许多,脸上总挂着生意人的笑容。他接过我的伞,抖落水珠,"还是老位置?靠窗那张桌子特意给您留着呢。"
我点点头,目光扫过焕然一新的茶馆。原先的八仙桌换成了西式圆桌,墙上挂着月份牌美女画,角落里那台新买的留声机正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跑堂也不再是提着铜壶的老周,而是几个穿着白制服的年轻伙计。
"老周呢?"我问道。
小周的笑容僵了一下,"家父去年冬天走了。肺病,医生说是常年吸茶烟落下的毛病。"他很快又挤出笑容,"不过先生放心,茶还是原来的配方,我跟着家父学了十几年呢。"
我心头一颤,想起老周那双被茶烟熏得发红的眼睛。他总说茶如人生,苦尽甘来。如今甘甜尚在,煮茶人却已不在。
小周端来的仍是白瓷盖碗,但碗身上的青花山水变成了机器印刷的图案,摸上去少了些温润。茶还是龙井,却没了当初那种让我想起北平故人的滋味。我啜了一口,望向窗外雨帘,思绪随着茶烟飘散。
战后第三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出现了。那日我正在读报,忽然听见柜台处传来争执声。
"这茶不对!一味轩的碧螺春从来不用紫砂壶泡!"一个沙哑的声音激动地说。
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个头发花白、西装革履的老者正对着小周皱眉。虽然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但那轮廓分明是——"李景明?"我试探着叫道。
老者转身,眯起眼睛打量我,忽然大步走来。"是你!那个总坐在窗边看书的先生!"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多少年了?十年?十五年?"
"整整十七年。"我答道,喉头莫名发紧,"你...还好吗?"
李景明在我对面坐下,西装面料考究却略显陈旧。他点了支烟,烟雾中我看见他右手缺了两根手指。"战后从香港回来,生意不好做啊。"他苦笑道,"倒是你,一点没变。"
"变老了。"我为他斟了杯茶,"赵砚之...有消息吗?"
李景明的眼神黯淡下来。"四三年在重庆,敌机轰炸...他为了救几个学生..."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死前还念叨着要回一味轩喝茶。"
我们沉默良久。留声机里换了白光唱的《如果没有你》,甜腻的歌声在茶馆里飘荡。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李景明突然说,"就坐在那个角落。"他指向如今放着留声机的位置,"他看见我包里的《饮水词》,就念了句'人生若只如初见'..."
"记得。"我点点头,"后来你们成了莫逆之交。"
"是啊,莫逆之交..."李景明从内袋掏出一本破旧的小册子,正是当年赵砚之送给他的《饮水词笺》,"这些年我一直带着它,走南闯北。"
他翻开扉页,上面有赵砚之的题字:"赠景明兄:萍水相逢,亦是前缘。砚之,民国二十五年秋。"
一滴茶水晕开了墨迹,我才发现是自己的手在抖。李景明拍拍我的肩,起身告辞。"我得走了,下午的船回香港。"他犹豫了一下,把《饮水词笺》递给我,"留着吧,放在这里比跟着我漂泊强。"
我送他到门口,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云层,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李景明整了整领带,忽然说:"其实我后来见过柳如烟和林书白。"
"真的?他们在哪?"
"新加坡。开了间书店,专卖进步书籍。"他笑了笑,"他们问起过一味轩,问起过你。"
我看着李景明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想起那年秋天,柳如烟和林书白合撑的油纸伞上,落满银杏叶的样子。弘一法师说得对,只要同行的时候是快乐的,怎么走散的并不重要。
茶馆的常客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个戴金丝眼镜的银行家总在午后出现,点一壶祁门红茶,读英文报纸;两个女学生喜欢在周末占着靠窗的桌子写作业,叽叽喳喳像小麻雀;还有个穿中山装的政府职员,每次都带着不同的文件批阅。
小周的经营很成功,一味轩成了城里小有名气的"新式茶馆"。他引进了咖啡和西点,还定期举办读书会。年轻人喜欢这里,说是有"文艺气息"。
某个春日下午,我正在读一本新出的《围城》,忽听门口铜铃轻响。抬头望去,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穿着藏青学生装,眉目间有几分熟悉。
"请问..."他环顾四周,声音清朗,"这里以前是不是有张棋桌?"
小周从柜台后走出,"是有,靠墙那边。不过早撤了,现在放留声机。"
青年略显失望,从包里掏出一本旧棋谱,"我爷爷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这本棋谱送回一味轩。他说...这里有个叫阿明的棋手会明白它的价值。"
我和小周对视一眼。小周接过棋谱,翻开泛黄的扉页,上面是陈老秀才工整的毛笔字:"赠爱徒阿明:棋道即人道。为师毕生心血,望珍之重之。陈观棋,民国二十五年冬。"
"这..."小周声音哽咽,"阿明已经不在了。战时为了救这本棋谱..."
青年愣住了,"爷爷说,如果找不到阿明,就交给一味轩的主人保管。"他犹豫片刻,"爷爷叫陈明德,是陈观棋先生的孙子。四八年去了台湾,一直想回来..."
小周郑重地接过棋谱,"我会好好收藏。令祖父和陈老先生...都是重情义的人。"
青年告辞后,小周把棋谱放在柜台后的玻璃柜里,和几件老茶具摆在一起。阳光透过玻璃,照在那些褪色的字迹上,仿佛给往事镀了层金边。
我开始整理这些年在茶馆的见闻,写成一本小册子,取名《茶烟录》。小周很支持,特意在茶馆辟了个角落展示我的手稿,还让顾客随意翻阅。
"您写的故事吸引了不少客人呢。"小周笑着说,"尤其是年轻人,说很有'民国风情'。"
我笑笑,没有告诉他,我写的不是风情,而是那些在茶烟中渐渐模糊的面孔——老周被茶水浸润过的沙哑嗓音,陈老秀才教棋时的谆谆教诲,阿明咬着下唇思考棋局的侧脸,柳如烟转着青瓷杯的纤纤玉指,林书白谈论新诗时发亮的眼睛,李景明和赵砚之因《饮水词》相视一笑的瞬间...
暮春时节,我照例去茶馆小坐。推门进去,却见一群学生围在留声机旁,听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姑娘唱评弹。那眉眼,那姿态,活脱脱是当年的柳如烟。
"她叫柳梦梅,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小周凑过来小声说,"听说她外婆年轻时也爱唱评弹,常来我们茶馆。"
姑娘正唱到《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一段,吴侬软语,哀婉动人。我闭上眼,仿佛回到战前那些宁静的午后,柳如烟坐在评弹台前,眼波比茶汤还清。
曲终人散,柳梦梅走过来向我致意。"先生常来?"她问道,声音清脆如铃。
"是啊,很多年了。"我示意她坐下,"你唱得真好,像极了我一位故人。"
"是我外婆教的。"她笑道,"她说年轻时在一味轩听过最好的评弹。"
我心头一热,"你外婆...可是姓柳?"
"您怎么知道?"她惊讶地瞪大眼睛,"外婆叫柳如烟,现在住在新加坡。去年回来探亲,还特意来茶馆看了看,说变化太大,认不出来了。"
我笑了,眼角有些湿润。"替我向她问好。就说...当年茶馆里那个总是看书的先生,还记得她和林先生撑的那把油纸伞。"
柳梦梅不明所以,但还是乖巧地点头。临走时,她送给我一张照片,是柳如烟和林书白在新加坡书店门口的合影。两人鬓发已白,但笑容依旧。照片背面写着:"岁月如茶,苦尽甘来。如烟、书白,戊子年秋。"
我把照片夹在《茶烟录》的最后一页。小周见了,提议在茶馆里办个"老照片展",让顾客们分享与一味轩有关的记忆。没想到反响热烈,短短一周就收到了几十张照片——有新婚夫妇在茶馆前的合影,有全家老小围坐喝茶的团圆照,甚至还有民国时期茶客们的单人照。
最让我意外的是,银行家带来了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年轻的李景明和赵砚之在一味轩门口的合影。两人一西装一长衫,对比鲜明却又和谐无比。
"家父留下的,"银行家说,"他是赵先生的学生。"
照片展持续了一个月,吸引了许多老顾客回来怀旧。茶馆里天天座无虚席,小周忙得脚不沾地,却乐在其中。他说这是"老字号的情怀",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秋那天,我照例坐在窗前喝茶。阳光斜斜地切过青砖地,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新来的跑堂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茶碗,清脆的响声让我想起阿明落子的声音。
我突然明白,弘一法师说的"随风而舞"的缘分,就像这茶烟一样,升起,缭绕,最终散去。但茶香会留在记忆里,那些好的相遇,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小周过来续水,见我出神,笑问:"先生在想什么?"
"在想...茶凉了可以再续,人散了就只剩回忆。"我端起茶杯,"不过这回忆,像好茶一样,越陈越香。"
窗外,卖糖炒栗子的后生吆喝着走过,香气飘进茶馆,与茶香混在一起。几个女学生推门进来,银铃般的笑声在茶烟里荡漾。留声机换了张唱片,开始播放《夜来香》。
我合上《茶烟录》,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在一味轩相遇的灵魂。缘起时珍惜,缘尽时释然。茶烟里的缘分,淡如水,浓于血。"
铜铃轻响,又有新客人进来。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像极了那年春天,我第一次踏入这家老茶馆时的模样。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