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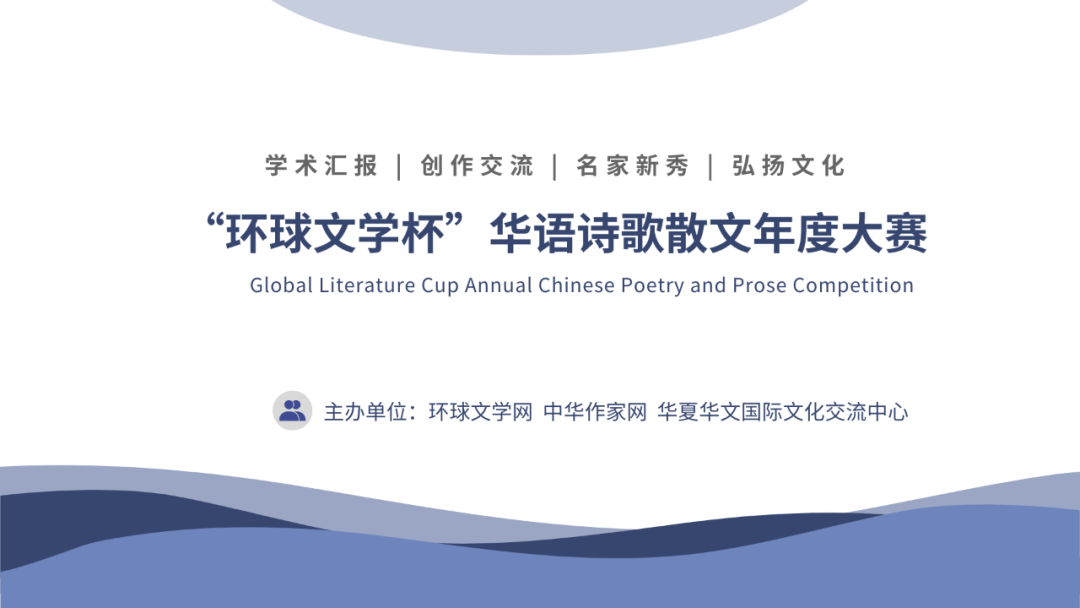
牛 歌(散文)
陋室居士
记起儿时,每当春耕季节,家乡苍茫辽阔的田野上,便会响起婉转嘹亮的歌曲,曲调悠扬,时而低沉,时而激昂,裹着晨雾,夹着炊烟,从岁月深处缱绻而来,一曲曲一声声洒落在田野上空,像似璀璨在精神归途上的一缕阳光,将人们的记忆和情愫照亮,这就是牛歌。
牛歌属古老的民歌范畴,也叫牛号子,方言称之为打“唻唻”:是赶牛人在劳作时唱给牛听的歌。牛歌从悠悠农耕岁月中应运而生,流行于苏北鲁南一代。在农耕生涯中,赶牛人把牛当成相依的伙伴,久而久之,便把牛人格化了。在共同劳作中,人们用牛歌与牛进行情感沟通和交流,向牛倾诉自己的忧愁和烦恼。
这淳朴而动听的牛歌,浸透了芬芳的泥土气息,称得上是大地之子的心曲:每一个音符都沉淀着赶牛人的血汗,每一个音节都是用牛人从生命最深处迸发出来呼唤和呐喊,是心中多年的渴望通过肺腑发出的声音,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文化底蕴。
可以说牛歌是苏北的信天游,是一首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虽然简单,却被人们称之为故乡田垅上的天籁之音,农民在牛歌声中垦荒耕种,播撒希望,开创未来。牛歌对他们而言,称得上是历史之歌,情感之歌,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内容。从文化层面上来讲,牛歌是淮剧的源头,淮剧是因牛歌而产生的地方剧种,牛歌的旋律在淮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那些世代以农耕为主的农民们,长期身处寂寞的荒田旷野,他们虽然没有文化,没有音乐细胞,却以牛歌自娱,用牛歌来抒发情怀。一代接着一代,他们既是传承者,又是创造者,他们从传唱中矢口寄兴,随意而为:时唱时哼时吟,把一支支牛歌演绎得抑扬婉转,荡气回肠。
牛歌的特点是结构短小简洁,曲调开阔奔放,感情炽烈深沉,具有浓郁的随感性。人们一直以为牛歌没有歌词,只有旋律和音符,是一首典型的无字歌。我内心并不认可,多次在周边县史吏志上查找,并未发现相关这方面的记载。也曾和地方史家探讨过,均无结果。而在一次和一位学者交谈中,无意中惊喜地得到了关于牛歌的传说:牛歌不但有词,而且词语十分精炼贴确,乃是神农所创。其中有一段传说:“神农年间,人类从原始守猎转入农耕,刀耕火种,不胜其力,上天派牛下凡协助人们耕种,牛起初不听使唤,不肯出力,神农根据牛的习性想出一法:教人们唱歌给牛听,歌词内容是:“尔不力我何依也”。意思是你不出力我依靠谁呀?牛是通人性动物,非常喜欢听音乐,闻歌则喜,于是便愉快地摇尾向前。
自从有了牛歌,牛从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劳作,成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悠悠几千年农耕文化中,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人们却把牛歌的歌词放弃了,也许没有歌词的牛歌唱起来更自由,更随意。所以,世世代代只延续下来牛歌的音符和曲调,歌词却早被遗忘了。唱者只用嗳、呓、哎、嗨、哦、嗬、啊、呀、哟之类的叹词自由组合,随情任性而为,倒也很有特色,很像新疆民歌中的无字部分。听久了、听惯了,会觉得比任何咏叹调都更能激动人心。
特别是耕田时所唱的牛歌更具特色:用牛者跟在牛的后面,一手扶犁梢,一手执长鞭,胸腔吸气,小腹用力,真嗓发声,引颈而歌,极具诗情画意。起首以悠长的高音从极弱的感觉中慢慢增强,音域显得十分宽广,雄浑而粗犷,送得远,听的清。如果聆听者凝神屏息,闭目而听,就仿佛署身于亘古荒漠边缘,听着一个古老的旋律从极远极远的荒漠之中在向你召唤。你刚产生感觉,荒漠之音却被紧接着的如潮涌般长长拖音所淹没,在淹没中高音又起,真可谓跌宕起伏,一气呵成,从而达到了腔调的自由延伸,让人感觉辽阔悠远。
有人觉得牛歌的唱腔简单,是的,牛歌虽然调子听起来简单,但高低运转自如,舒展流畅,给人以大象无形,大道至简的灵魂震撼:这就是牛歌的魅力所在。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在以农业为主的苏北平原上,人们一直把牛歌当着特殊环境中䇿牛劳作的特殊歌谣,伴随着区域的农耕文化一起生存和发展。无须伴奏,不需舞台,但却很有讲究,也需要一定的表现水平。人们耕田耙地,打场赶车,拉碾磨面等各种场合下趋牛劳作,只要情动之际,便是牛歌迸发之时。而且会根据不同的农活,不同的速度和节奏,把不同的心情和感受渗透进去,因此所唱的牛歌曲调也就完全不一样。
当犁铧插入泥土时,牛歌就背负了沉重的企盼。在打谷场上,牛歌则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尤其是在拉车上坡之时,是最需要牛出大力的时候,此刻的牛歌便成了高亢激昂的号角,扣人心弦,牛也会为这样的牛歌而竭尽全力向前。所以,牛歌在不同的劳作场合,音符有长有短,有急有缓:有悠扬豪迈,有深沉悲凉。一声声一曲曲,把生活在最底层的沧桑和艰难,把对日子的渴求和希望,都在牛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表达了人们在田园生活中的感受与情怀:这就是牛歌的韵味所在。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基础,国家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劳作又离不开牛。农民和牛几千年来就是相依为命的共同体。所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种者,心里都有一首牛歌,几千年来从未有一个艺术家去触碰过这首歌。因为这曲千古绝唱无可代替,也无人可以改变。
文革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异常地涤荡着传统,使一切人类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都在冲刷中更新变异,唯独牛歌没有变,还是老样子,老调子,没有被语录歌代替。不知是牛听不懂语录,还是人们没有唱语录歌给牛听的习惯,牛歌还是延用原汁原味的腔调在苏北广阔的原野上回旋:那么高亢,那么悦耳,那么质朴纯厚,那么激动人心。因为这是绝唱,是几千年来人们一代又一代合力打造出来的曲调,其中包涵着丰富的层次变化,属于多层面的艺术精华,每一个音符后面都需要深厚的功力。如果用丰富、华丽、华美、雄壮等精美动听的形容词来赞美牛歌,这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所有美好的东西,所有美好的艺术,都是从人们的心底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所以无可代替,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改编和重塑,因为这是有计较有出处的:这是苏北平原上广大农民,祖祖辈辈从旷古上世相传下来的心灵之声,是从耕种者心里茁壮出来的一颗明珠。他们世代殷殷相习,世代相传,从未间断。就如同中国的汉字一般,一直流传至今,成了劳动人民平淡日子中的一种追求和乐趣,一种点缀和倾诉。唱牛歌的人如此,听牛歌的人往往也会带着情感色彩,由着自我心情,从朦胧中感受牛歌深沉低缓的情调。
我小时候就是喜听牛歌的听众,百听不厌。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放学后的傍晚,夕阳西下,我背着粪箕,闻歌来到田头,只见一位孤独老汉赶着牛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耕地。老汉五十多岁,身子骨看上去并不硬朗,高高的身躯由于常年劳累,背已经驼得厉害,我依稀认识这位老者,知道他姓王,人们都叫他王二爷,他是生产队里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场上田里样样都行,耕田耙地更是在行,牛歌也唱得出色。
此时王老汉正一手扶犁梢,一手拿着长长的鞭子催牛向前。前面拉犁的是一头体型较大、却瘦骨嶙峋的黄牛,这头黄牛已经很老,身上的皮毛不再光亮,全然没了往日的雄风和气势,只是孤独而悲情地拉着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着,像极了一幅水墨画。我看着那粗大的牛蹄高高抬起,又慢慢落下,总是后脚踩在前脚印上,前后交替。随着前进的步伐,老牛的头在忽左忽右地摇晃着,这说明老牛走得很吃力,必须用左右摆头来配合。老牛的尾巴也在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摆动,似乎是在作自我鼓励,每摆动一下,就说明已经前进了一步。
老牛就这样吃力地往前走,吃力的后面是犁铧推着泥浪在款款翻动,这就是老牛吃力的成果。我在田头看了很久,王老汉手中虽然拿着鞭子,却并没有打过那头老牛,只是依着老牛的性子和能力在向前走着。有时他也把鞭子虚扬一下,甚至在空中甩出一声脆响,却并没有真的打在老牛身上:意在警牛以䇿。有时候也听到他高声喝喊,意在为牛加油。老汉耕种了一辈子地,他知道天行有常,季节不等人。他也想牛走快点,他也知道老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能力,再也走不快了。
所有在农村生活过人,都能体会到农民对牛的那份感情:他们白天和牛一起劳作,晚上甚至就睡在牛的身边,相依相偎,共度夜晚。早上起身牵着牛一起迎日出而作,晚上共同送日落而归。溯风冒雨,相互配合,这就是他们永恒的生活主题。那时候我在想,老汉是十分了解牛的,了解牛那种忠厚勤劳的本性,知道牛只会任劳任怨,却不会偷懒耍滑,它走不快是因为它已经力不从心。
老汉也许知道自己的命运和这头老牛相同,彼此需要抚慰,因此不忍心使用鞭子抽打。但又想它快走,于是便打起“唻唻”来愉己悦牛。他的“唻唻”虽然还有高亢悠远的成份,但更多的却是凄楚,还含有淡淡的悲凉。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每当耕种季节,牛和人一样辛苦,起五更睡半夜,天蒙蒙亮下地干活,一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工归去。他们不遗余力,却不思索取,只知道奉献,不去考虑享受。
我看着耕地的老汉一边在想:在这一望无际的荒瘠土地上,这个淳朴憨厚的老人,孤独寂寞地扶着犁梢,从早到晚跟在牛屁股后面,为了驱赶忧愁和困惑,唯一能做的就是唱牛歌,这牛歌既源于他,也源于牛,是互慰,也是倾诉。
时代变迁,用牛耕田和唱牛歌来愉己悦牛的时代已经不在,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却难以忘怀那段农耕历史,时时翻涌上心头,特写此文以记之。
作者简介:徐锦成,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市,69年参军,回地方后在医院工作。自幼甚喜文学,更爱诗词书画。几十年一直在探索和追求诗词书画艺术,勤耕不辍,创作亦丰,有很多诗词画作散落在民间被收藏,常有作品见注各类报刊,著有纪实长篇《岁月悠悠》。诗词书画作品在2019年大赛中曾获三个一等奖,一个金奖,一个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