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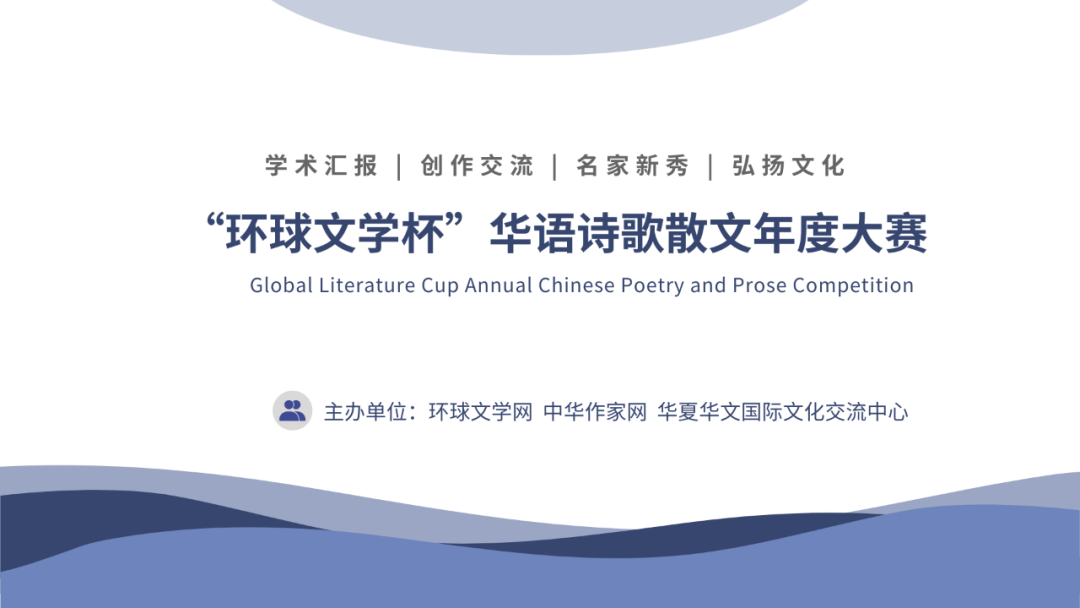
家春秋(散文)
蔡效华
引子
真正的记忆从不悬浮于脑海,而是蛰伏在旧物褶皱里。妈妈的毛衣针脚、阿Vo灶台上的油垢、甚至一张磨破边的木凳——这些物件是时光的琥珀,封存着比DNA更顽固的归属密码。
可物件会丢失,住址会变更。当海南戏的锣鼓声被短视频算法淹没,当族谱里的“迁琼始祖”成了外卖App上的籍贯选项,我们的乡愁该寄存何处?
这时代像一台失控的3D打印机:一边复制“怀旧网红店”的壳,一边把祠堂的青砖压碎成元宇宙的像素。
但人的根系总要找到土壤,不是么?或许“家”不再是地理坐标,而是三两好友在耳机漏音时相视一笑的心照不宣,是出租屋里一锅煮沸的椰子鸡——我们正在用新的物证,对抗原子化的冷。这种对抗的姿态,在我的童年已初现端倪
一折 何以为家
似乎自从我有记忆以来,生活就总是在东奔西走中度过,每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家庭住址总要重新填写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阿Vo的家里度过的,阿Vo就是海南话里的姑姑。阿Vo一家住在一栋非常破旧的小楼房里,外墙是一片片短条形白色小瓷砖,中间显露出一道道浅浅的深灰色沟壑。楼梯和扶手都是水泥做成的,一楼还有一个打磨光滑的石球连在扶手上。我们家在三楼,我常常想我们要是住在二楼就好了,因为一楼到二楼的楼梯只有其他楼层的一半高,对于小小的我来说,只有这里才能健步如飞,其他每一层都是大迈步的艰苦攀登,有时甚至手脚并用。楼下的一条石板路连向我阿爸阿嫲(我姑父的爸爸妈妈)住的瓦房,瓦房的对屋是养鸡的鸡舍,舍外是生火做饭的灶台,阿爸是木匠,常常在屋外的长条凳上画墨线,刨木头,打铆钉,上木漆,他专门给我亲手打的一张小板凳,现在还放在我房间的桌底下,只不过作用换成了垫脚。几个月前的深夜偷偷溜回去看的时候,只发现瓦房的木门虚掩着,屋内只剩一张积灰的木床,墙上的八卦镜蒙了蛛网,像一只失明的眼睛。鸡舍似乎被改造后转给了其他人家,暗夜里只剩风声呜咽。当灶台成了墓碑,八卦镜照见的只剩我们的追忆。这是我的家吗?我常常问自己。不是。或者说不是我的家,也许只是童年时代的缩影罢了。
此后我随着父母一直搬家,开始是龙华菜市场上的几间小屋,后来是九中对面的一间小公寓。等上了初中,索性直接搬到了学校里面。在初中毕业后,父母带姐姐搬回了爷爷的三层阁楼,而我却来到了海中继续租房子。直到去年爷爷去世,我在那边生活的时间也不超过三十天,我常常问自己,哪里是家?似乎哪里都不是家。
家不是填在表格里的地址,而是丢在时光里的那把小椅子。
人们常说:“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果真如此吗?和妈妈亲密而又疏远,和姐姐疏远又亲密,和爸爸总是有着无关的淡漠而又殷切的期盼,我们一家很少聚齐,要么就是缺少了某一个人,即使聚齐也总是有人在夹缝中生存——每一个人。因此我常常想在别人家表面和睦,美满,平等,和谐的幸福景象下,是否实际上也是暗流涌动的家庭关系呢?所以有家人的陪伴,便能体会家的感觉吗?家春秋!家春秋!家在春雨秋风前,还是春去秋来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我在寻觅归属的夜半清风里向天下恳切的叩问,何以为家?
二折 春意阑珊
想先请大家看一段我随手拍下的一段视频,我相信,大家一定什么都没有听懂,没关系,其实我也什么都没听懂,其实这是海中附近府城文昌阁柔惠宫的一段海南戏----《冼夫人》。琼剧,这个曾浸润海南人血脉的名字,如今蜷缩在电子屏的夹缝里,字幕滚动的速度比阿婆摇蒲扇的节奏还快。在我的记忆里,从前全然不是这般光景.每逢初一,十五或是公期(据我所知就是海南各路神仙的诞辰),很多社区都会请来戏班子,或是临时搭建,或是长期存在的戏台上演上几本,奏上几折,台下是密密地排成几长排的条凳,或是红色塑料凳,条件好一些的还会在戏台两侧各放一条长长的LED屏幕,上面实时的滚动着红色或绿色的字幕。我也不知道台下人挤人到底能看见什么,也许大多都只是看一个热闹罢了,可即便是这样的热闹,现在也并不多见了。曾经的戏台前,竹椅能摆出个‘八卦阵’,阿婆们摇着蒲扇从《冼夫人》看到《张文秀》,这出讲述书生落难、小姐赠金的传统戏码,曾让多少海南姑娘攥紧了手帕;现在的庙门口,只剩短视频外放的嘈杂声,和半截褪了色的红幕布。小时候尤其喜欢放的炮,爱点的鞭炮,长大多也都不乐意去点了,就算是近些时候放开的烟花,也似乎没有从前那么有年味了。每每看见一些以怀旧风格为特色的店铺----长条板凳、悬挂的电扇、格子式瓷砖,总有莫名的熟悉,又有说不上来的悲哀,“那些仿古招牌像一场拙劣的招魂术——我们消费着‘怀旧’的壳,却丢了魂魄”。这究竟是在过度消费人们的记忆,还是只是想在春意阑珊的时候留住这么一点残存的春色?人们总是喜欢在记忆中寻找,试图觅得一个熟悉而美好的地方,但随着乡土的不断变迁,人们梦想中的故土早已不再春意盎然,只剩下满城风絮下的一地鸡毛。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那样:“前尘隔海,古屋不再。”
三折 萧瑟秋风今又是
真正的记忆从来不存在于脑海之中,而是黏附在一些物体,一方住所之中,然而,物品总会遗失,住所总会更改,文化早已不再。人们脑中,自己所归属于的美好记忆,终会沦为空洞的呢喃。因此,从古至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无数美好的记忆寄存到了一片土地之上,这片土地叫家乡,这种归属叫乡愁。但是现在的人似乎和十年前,百年前,千年前的人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家庭关系的更易、生活地方的不断迁移、家乡故土的天翻地覆,都更加重了现代人自一出生以来就逐渐淡退的归属感。
曾经和北方的同学聊天,让我无比震惊的是他的大年三十是在朋友家里度过的,作为南方,尤其是两广和海南的孩子,自己的身后总是站立着一个大家族。然而随着不断成长,这种与家族其他成员的联系也逐渐减弱,多少年之后是否也会变得和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不再联系呢?我想是一定的。
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下,人际关系在经济因素的隔离与独立,乡土变迁过快的茫然与无依,以及渴望寻找归属却又不断被冷淡排斥的撕裂感,不同于过往的人口迁移。我们像京剧《双枪惠娘》里被拆解的铆钉,在时代的魔方中颠沛流离。王叔的山东煎饼摊支在陆家嘴二十年,城管来时的‘外地摊贩’与老家的‘上海腔’嘲讽,让他成了方言地图上的无人区;而阿强的潮汕鱼丸在深圳科技园的日料店里,被包装成‘和风手作’——我们似乎正在成为自己乡音的叛徒。人口流动过快和城市化使人们的价值观与原生地域文化逐渐疏离,形成心理上的“双重身份困局”。其次,数字时代使人们成为了“数字游牧民族”,用3D打印机“狩猎着”所谓的“家”试图在网络空间寻找与自己同志的集体来获得归属感,并且通过媒介化的“文化快餐”例如弹幕、兴趣圈层构建所谓临时归属。但这种身份标签极易变化,并且缺乏深层情感连接,从而进一步加剧齐美尔笔下“表面相连,其实疏离”的“社会原子化”。"当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成为时代症候,祖屋墙上的八卦镜便成了文明的遗骸——它曾见证阿爸刨木时与邻里的寒暄、阿Vo灶台边与路人的分享一块刚刚炒好的鸡肉,农耕社会的乡土情结正在不断瓦解,心灵的归处困扰着无数的人们,萧瑟秋风今又是,何去何从未可知?那我们,怎样从重新立足,寻找自我归属?
尾声 安土重迁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岁月流转得很轻、很缓,扎根了一片土地就永远都会想念,无论是从东走向西,还是由南走向北,无论是去向远方的哪里,还是一直都在这里。从前的人们安土重迁,所寄托的是一生。然而现代的多元文化爆发,世界日新月异,人们似乎很难在传统意义上的家中找到一方净土,收获平静的归属。因此人们必须重新迁移,出发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家乡,它可以还是海口还是三亚,还是河南河北,还是山东山西。只是他不再是先辈们所生活的地方,而是我与之深深相连,产生情感共鸣的新的空间。“我们拆掉祖屋的瓦,是为了用碎瓷片拼出新大陆”
它可以是一个社交圈子,三两好友不必牵扯什么社交的手腕,只是心有灵犀,相视而笑,我们在Livehouse的声浪里碰杯,有时比祠堂祭祖时更懂血脉相连的意义——那些不需要解释的默契眼神,正在重写《礼记》里的“族”字;它可以是一方温暖的小窝,只有爱你与你所爱的人,简单而平淡,真挚而自然。不留世俗,不服表面,先要割断蔓生的杂草,才能向生机里扎根,重迁未必重迁,只是要破除社会所套上的所谓家的束缚,重新用心,用手,用眼睛,去感受,去触摸,去看,与自己的土地相连,重迁而安土,知道葬于何处。葬我于每一次与土地的对视,葬我于每一场不期而遇的共鸣。墓碑二维码扫出的墓志铭,写着“此处心安是吾乡”。
作者简介:蔡效华,2007年8月30日出生,海南海口人,海南籍海南中学高三在读高中生,作品关注乡土归属感现代化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