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憨憨地笑着,不料正有“大聪明”
侯林
在我的印象里,鸿河常是憨憨地笑着,半张开嘴,带有少许矜持的,加之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壮硕的身材,由是,一位憨厚、浑朴的“男爷们”便赫然出现在你的身边。
然而,只有熟知并真知他的人们方才晓得,在这样一幅温厚良善、蔼然如春的相貌背后,是有着充分的生存智慧与人生谋略的。
人有大聪明与小聪明之分,济南人爱把终日喋喋不休的小聪明称做“皮精神”,而我则认为,鸿河是大聪明者,一言以蔽之,他有抓住机遇、改变人生的能力。

自左至右:黄鸿河、侯琪、戴永夏、侯林合影
与鸿河的结识在2019年,那是一次纯粹的“文字缘”。
那年,我应济南市水务局与济南出版社之邀,担任评委并组织一次济南泉水征文的评奖,评委们不约而同地都看好其中一篇名曰《清如明鉴五莲泉》的文章,它描写济南南护城河上五莲泉昔日的景观,从“玻璃池子”的称名,到作者少时在护城河里游泳,用自制的扣罩网捉鱼,特别是护城河里红掌绿水、活蹦乱跳的鸭子,写来活灵活现,令人不禁叹惋:人泉一体,才是济南最美的风景;济南人呀,向来是与泉水生活在一起的。护城河整饬了,人却走了,这最动人的烟火气也就消失殆尽了。惜哉哀哉!
文章的作者,恰是黄鸿河。
征文结束后,我主动拨响了鸿河的电话。
我以为他会有大的发展。
果不其然,2022年底,黄鸿河的《回望济南》一书,有济南市政协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济南市政协负责文化文史的副主席刘勤为之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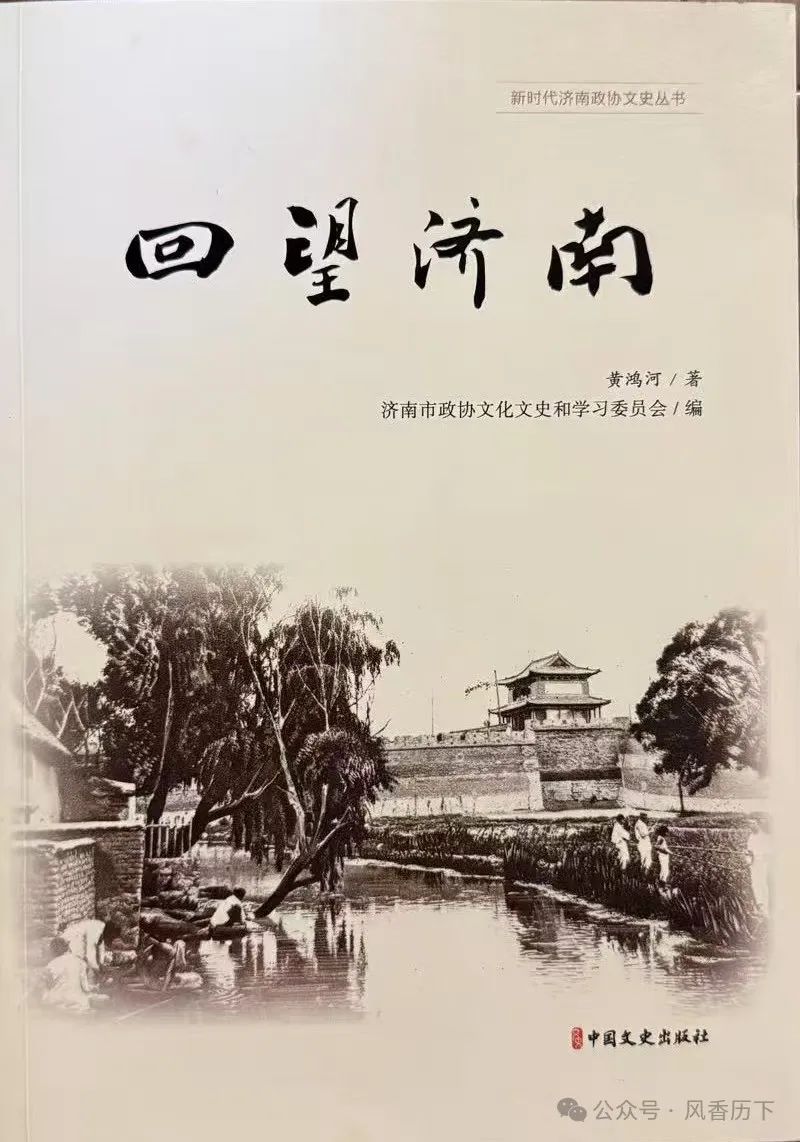
书影:黄鸿河著《回望济南》
鸿河是老济南,这是先天的优势。
他祖籍聊城东昌府堂邑县,爷爷一辈自1904年济南开埠之后,步行三天走进济南府,先是租住小布政司街和太平街,1947年在四里山下(后名信义庄)落户生根,如今已是五代老济南人了。其对老济南的故土情深、桑梓情怀是难以言表的。
鸿河自幼喜爱文学,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散文、诗歌居多。鸿河生命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97年。那一年,是信义庄建庄70周年。面对已经面目全非的老街和四处迁居的乡邻,于惆怅之余,他总感到应该写点什么,以记录传承真实的村庄史。他在济南文史学者张继平先生的鼓励下,写了一篇《信义庄的来历》,没想到文章发表之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称赞与欢迎。为此,他又一鼓作气,写出三里庄、四里村、五里沟、六里山、七家村、八大新村等回忆文章。
这是由文学而济南历史的一次转折。
在我看来,鸿河最大的嬗变还在其后,这就是他参与济南两个区市中与槐荫文史资料的搜集、采访与撰写,参与了《经天纬地》《日升月恒》《济南老工厂》《济南老企业》《济南老街巷》等书的编写。在一般人眼里,这些老企业、老街巷有什么意思,然而,鸿河却慧眼识珠,他敏锐地发现了这其中蕴含的机会与机遇,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他才熟悉了济南的老街巷,熟悉了生他、养他的老济南的。

济南雪景
于是,民国、街巷,形成了鸿河研究济南的两大兴奋点。
亲历与亲见,结构成鸿河文章的一大特点。如前述的护城河,此类文章还有他的四里村、六里山等系列。
这些来自心灵深处的珍贵记忆,乡愁一缕,风情万种,令人、特别是济南人回味不已。
街巷文化,正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领域。笔者有言:街巷,乃城市的骨胳与血脉,而名士与建筑,则是骨胳与血脉的支撑,有了它们,城市文化才变得鲜活且流动起来。济南作为名士之城,在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不为人知的小街僻巷里,都会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名人遗踪和风雅旧事。
而作街巷文章,难度也是最大的。
这些年,鸿河读了很多的书,济南府县志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凡与济南历史有关联的图书文献,他都找来阅读,如《济南快览》《济南大观》《济南指南》《历下志游》《历下烟云录》,直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写济南餐饮,则是《中国烹饪辞典》《济南餐饮概览》《中国名菜谱》,直至清代袁枚《随园食单》,民国范烟桥《历下烟云录》,凡是能够找到的有关书籍资料,必是贪大求全。因之,他便有了许多独家的发现与发掘。
比如,关于济南老字号“阜成信”棉花行的考证。他指出,“阜成信”号称1909年的建筑,而此时济南经二路西段几乎没有象样的建筑,且1914年《济南指南》、1927年《济南快览》、1928年《历城县乡村调查》、1934年出版《济南大观》中都没有“阜成信”棉花行的任何信息,但其它现在已消失的棉花行却历历在目,不可能25年间的数本写济南商铺字号的书中都忽略一家如此重要且在山东省举足轻重的棉花行?经过这样一番详考并参阅其他史料,他认为,阜成信应该是1934年后成立的老字号。
另外,关于南岗子新市场的创办年代。很多作者都认为是1905年由张怀芝购地创办的。鸿河认为,这是以讹传讹。他指出,张怀芝1905年前后在山海关和云南两地住防,官职也非显赫,是不可能到济南南岗子买一块荒地开办市场呢?
张怀芝于1915年到济南接替靳云鹏为山东都督,才有建新市场的可能。而人们则把时间错误地提前了10年。
为了考证清楚一件旧事,鸿河不怕吃苦,他特别注重现场考察。如济南有三里庄、四里村、五里沟、六里山、八里洼等地名,这些名称的来历,特别是起点何在,有人认为是南门,然而,无论如何与这些地方的“里数”也对不上,其后鸿河经过多少次实地考察地形,步行丈量,再参照文献记载,确认这衡量起点不是南门,而应是济南府西门(泺源门)。

趵突泉俯拍
街巷与餐饮,是最接济南地气的领域,鸿河专注于此,且以轻松幽默的文笔出之,这是鸿河济南研究的第三个特点。如他写的民国时的泰丰楼和东鲁饭庄:
属胶东福山风味,福山厨师的特点是擅长做海鲜类菜肴,早年间大厨腰间必藏一锦囊,热菜出锅前,趁人不备从囊中捏出粉末撒入,菜品顿时鲜美无比。外人不得其解,此乃福山厨师秘密武器也。“武器”者实为福山特产海肠,经干焙后压成粉末,是早期福山派厨师发明的“天然味精”。
(《老济南鲁菜馆》)
在风趣的叙说之中让读者领略胶东鲁菜的一大奥秘。
又如他借用范烟桥对于鲁菜馆的评析:
论商埠诸菜馆,济元楼如半老徐娘,犹存风韵,倘为熟客,倍见温存;新丰楼如新女子,活泼泼地,自有天真,间效西风,更新耳目;三义楼如少妇靓妆,顿增光采,已除稚气,颇有慧思;百花村如北地胭脂,未经南化,偶尔尝试,别有风光;宝宴春如新嫁娘,腼腆已减,妩媚独胜,三朝羹汤,小心翼翼。
(《历下风云录》)
取譬于风情万种的美女来言说济南的餐馆,可谓生花妙笔,别出心裁。
写作,从本质上看,是叙事的艺术。有了资料,只是食材而已,要作出精美的菜肴,才见主人的功夫。

五龙潭 王啸摄影
因而,对于资料的领会、消化、吸收与组织,才是更为根本的。在我看来,鸿河对此是有充分的悟性的。比如,他追溯当年济南经纬路及许多街道广植国槐原因时,这样说:
一是众所周知的风俗。老话说:“若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中国自古就有移民栽国槐的传统,据《槐荫区志·村庄概览》统计,槐荫郊区有村庄127个,其中24个村庄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过来的,有8个村庄是从老庄中分离出来的,另有51个村庄是从河北省枣强县移民过来的。国槐有吉祥平安长寿的含义,济南大户人家有在院门外栽槐树的风俗,有“门前栽双槐,升官又发财”之说。
(《槐荫大道经六路》)
移民迁徙的资料,与济南槐荫的大槐树一经挂钩,这原始的、库存的资料顿时变得灵动鲜活起来了,而且,它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还有,鸿河有着抓住事物关键要点的穿透视野,这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基础能力。如他谈到历下菜的特征之一:
历下厨师的特点是“烧菜必炒汁,烧扒分明,炒汁飞酱”;做菜必先吊汤,学徒先学熬汤:用老母鸡、老鸭、猪肘子骨等凉水下锅,大火烧开,撇去浮沫,下入葱姜、花椒、香叶、盐和火腿等佐料。再次烧开,然后小火熬制七至八小时后使用,炒菜时用高汤替代味精调味。
(《老济南的鲁菜馆》)

曲水亭街
在济南研究领域,鸿河属于后起之秀。他在五十岁左右才开始从事济南文史的专门研究,然而,成果颇为丰硕。
鸿河是一位大器晚成者,这其实是好事,这使得他有了更为丰厚的生命阅历与人生体验,厚积而薄发。
鸿河曾经采撷老人的回忆说当年的泰丰楼:
客商进店,泰丰楼都要免费送一盘葱烧卤水豆腐,说是让外地客人吃下当地豆制品,让肠胃先适应环境,不闹腹疼,这当然也是一种营销手段,但让顾客很受用。(《开商埠后的鲁菜“帮口”》)
培根有言:人是生活在自己的智慧之中的。
十年光阴,是足以成就一位有悟性的人才的。
希望鸿河写出更多让读者受用的文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谨以此与鸿河共勉。
(本文是侯林先生为黄鸿河新著所作的序)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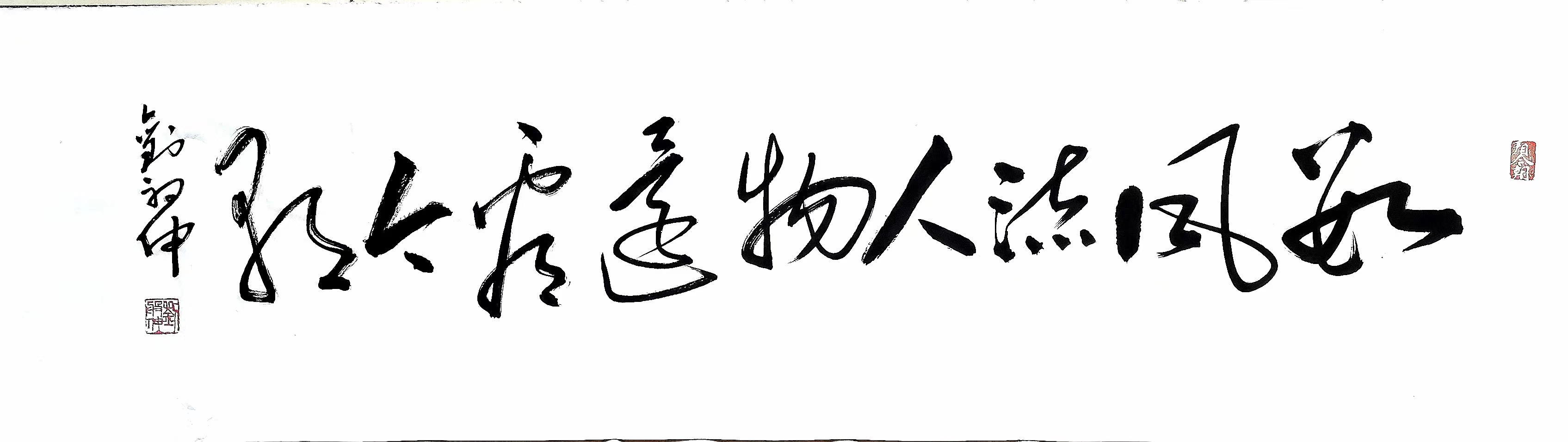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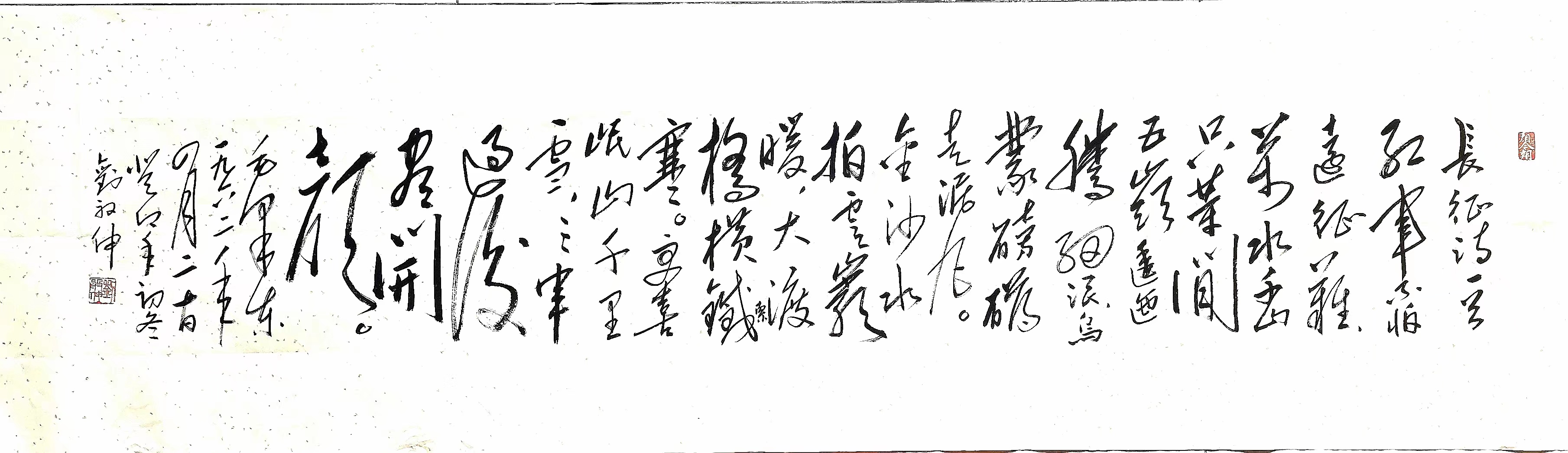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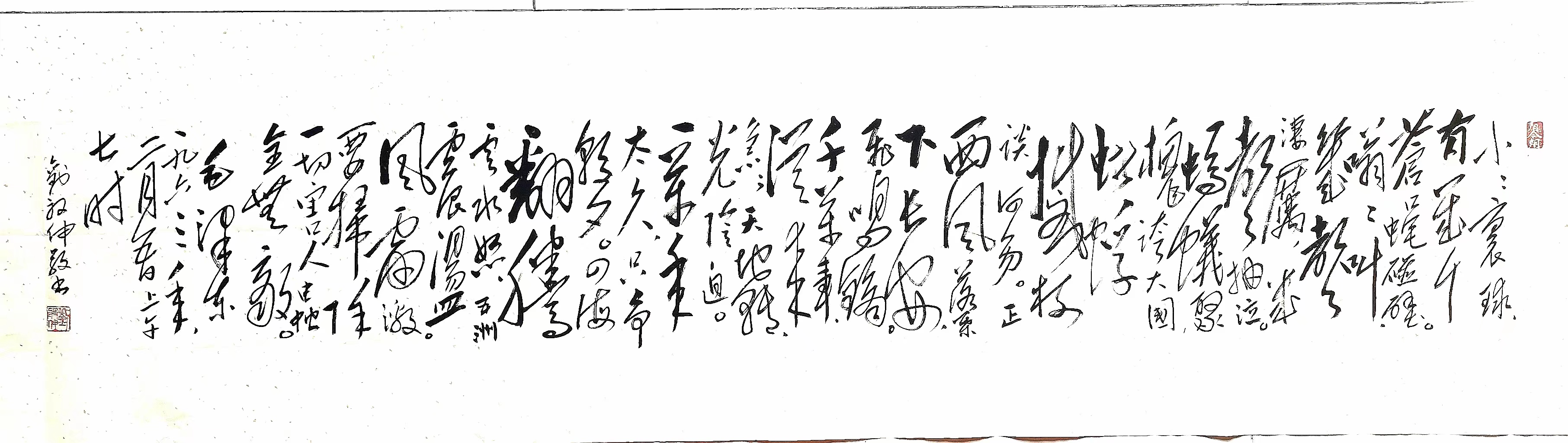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