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磊(吉林)
打开灯,用灯光把房间充满,
避免陷入黑暗的深渊,而现实恰恰与意愿相反,
已经在窗外的沥青街道上堆积起来,
漫过了七楼的楼顶,
那么像是孤独和恐惧的相加,
几乎是与漆黑的天空连成一片。
此时,正是凌晨两点钟栖居模式的重压,
使我伏在桌案的边缘上写作,
以一个意象在和黑暗较劲儿,
不论是楼顶的预制板在顶住高尚的音节,
还是封存了其中的意象及逻辑,
总是像一个自发光的人,在黑暗一隅,
以一个思想的头颅顶起思想,准备出现在破晓时分,
那么像一座坟场上的磷火,
从心有灵犀一点通开始,从不省略生命的词语,
使我从一个意象上滑过去,
哪怕是不为缪斯所知。
2023/10/17
好在我飞越了漫长的黑夜,
不是用梦,而是在恢复一本旷世书的话题,
仍在老宅的门楣上守候,
让祖辈一伸手就能够拿到我,
把我拿过去,让我在老屋的门槛上坐一坐,
在还原成回忆的原形,
能够记得父亲让我用双手攀上门楣高喊几声,
长高一些,再长高一些。
那时候,头顶上的阳光是没有边界的,
一直在迎接我,也交给我一座绿色的岛屿,
以及宁静的湖泊和青葱的树林,
让我打破天赋的禁忌,
在用隐形的墨水和镜像书写,似在解冻黑夜。
那不是打瞌睡的树冠,那是父亲嵌入星河的一团光芒,
能够告诉我父亲在那儿,
那是一个家族的灯塔,没有神话的自负,
诗歌的炫目。
2023/10/26
惊人的一面黑旗压在半空,
那是坏人的尸体,有一些虚张声势,
迷失在一片乌云中,
真的是一丝不挂了。
——那是从黑暗中蔓延出的寒冷,
在辖住我的双手,让我不能写诗,
而我并不是文学的坟墓,也不是墓碑上的墓志铭。
接下来是老灵魂手记,
像在把一个幽灵入殓,
在说:“假汝之名的哀歌只是汉语之恶,
说不出幽灵的消散。
自由在诉说着真相,真相却淹没在至暗时刻。”
此时,我想到一把空椅子,
活像活着有毒的一个人,
盘坐在一个广场中央在为自由寻根,
如同一枚银簪在雪花中熬炼过九次,
已经明白白发不是真理。
2023/11/2
并非是绝望,却不想看一眼人间,
哦,我已经羞于为人。
嗯,说着热爱生活但不爱生活意义的那个人,
是多么虚伪,一直在逃避生活,
到后来却活成了一个甲壳虫。
嗯,说着不想活成一棵树只想活成一棵树意义的那个人,
弄丢了自己活过的住址,
也弄丢了祖国,差一点停止了写作。
哦,我在用诗篇向艺术想象力致敬,
也勾勒出父亲的模样,既不在人间,
也不在天堂,让父亲活在心间,
与我同呼吸共命运,那是诗歌的心肠,
也是独一无二的亲情,仍然带着现代性遁去。
幸好我们不是词语的空洞幻影,
我们的亲亲相隐已经高于真理,
总是汇集真相的词语,愿意为真相去死,
有二十一克的灵魂就足够了。
2023/11/28
那是驱车走在祭祖的路上,
穿过腊月初一的暴风雪,我却被暴风雪所伤,
像我再次获得死亡的机会,
像我的目的地被一个族谱指定。
不,我在修改死亡的三种高度,
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气概弹奏七弦琴,
几乎是一个灵魂写手,
在说:“我从一座钟的年轮中走来,
将以诗讲述暴风雪中的命运。”
嗯,父母亲和叔父的骨灰被我存放在七星山顶,
接近千年的沉寂,
有着与白云的相似性,可以设想成为一首诗,
高于南山的一座白塔。
嗯,那正是一个家族的诗篇,
那是三眼泉在抬高一片湖水,
那是我一个人在攀登一条没有人攀登的生死落差,
几乎是生活和想象,
一个人,一个意象。
2024/1/11
满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只有我和自我相认,
而二十一克的灵魂正在把我遗忘,
不是昨天的音乐,今天的文学,明天的远方。
嗯,真相已经患上白内障,
像谎言涂抹的电影,
学会了用手势说话,像在弹奏一部钢琴曲,
仍旧相信被巫术蒙骗的金属舌头,
说起被踩踏的空气生产下子嗣,
在模仿b小调弥撒曲。
而我该如何称呼自己?我是在为真相赴死的一个人,
在黑暗的族群中负罪而行,
于一座渎神的坟墓中归于寂静,
那是我的单一,那是虚无的证明。
还有人在为我的错误争吵,
一方在用有毒的汉语耳语,一方在崇拜红眼病,
我说:“再见,耳朵。再见,眼睛。”
2024/1/24

把两个面具放在一个手掌上,在问诗歌的信使从何而来?
在这里,我把一首诗蓄满泪水|钟磊:相似之书 (12首)
中国新诗荐读|钟磊诗选30首 (2016~2021)
我总是在拱形的天幕下失眠,看见黑暗在包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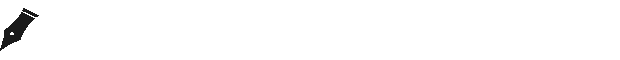
钟磊,独立写诗数十年。著有《钟磊诗选》《信天书》《圣灵之灵》《空城计》《失眠大师》《孤独大师》《意象大师》《活着有毒》等诗集,诗集被郑裕彤东亚图书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收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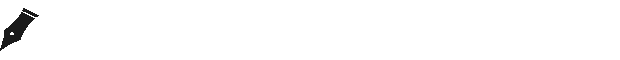
钟磊,1969年生,吉林长春人,诗人、评论家。中学时期开始写诗,倡导新意象诗歌写作,独立写诗数十年。曾出版诗集《钟磊诗选》《信天书》《空城计》《圣灵之灵》等。多次入选年度《中国最佳诗歌》《华语诗歌年鉴》等多种选本。现为《独立作家》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