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初秋游玉函山
宋文东
玉函山,又名兴隆山,小泰山,位于济南市二环南路领秀城南,最高峰海拔500余米,是城区诸山之中最高的山。唐代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有关玉函山的一个故事:“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黄,素翼,绛额,名‘王母使者’。昔汉武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 ,常令鸟守之。”此山便有了鸟衔玉函的神话传说,这便是玉函山名称的由来。
我曾经两次登临玉函山,一次是秋季自己探路去的,一次是初春与驴友结伙休闲而至,都到访了西佛峪。济南有两处佛峪,都在城郊。佛峪在城东南,龙洞之东,那里也有一座佛寺遗址,叫般若寺,悬崖上也有若干隋代摩崖造像和石刻,几处名泉,现在已成为旅游胜地。为了便于区分,人们习惯上称玉函山佛峪为西佛峪,不过来游览的人就不多了。
玉函山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山,不是一两次走马观花的驴行就能够认识它的。我深知对此山的了解甚为肤浅,尚有许多的未知需要仔细地品读。近日有驴友提出爬玉函山的要求,我也有意品读初秋时节的玉函山,于是约了几位驴友于白露次日成行。
那天一早,我们10位驴友在领秀城北门集合齐了,然后一起穿过小区到达泉子山下,沿着山体公园的石阶开始爬山。虽然是周末,但爬山的人却并不多,偶尔才遇到一两个下山的,给人冷冷清清的感觉。爬到泉子山顶,大家稍稍歇息。有几位老者在锻炼身体,我们彼此打个招呼,然后继续爬山。尽管时已白露,但天气依然炎热,山林里也没有一丝风,也许是在山阴之故吧?
爬上山顶观峰亭,一阵阵的清风徐徐拂来,颇为凉爽,惬意顿时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如果稍稍注意点,这种凉意与夏天的凉风是有明显不同的,毕竟现在时已初秋了。南面的玉函山高高耸立,雄伟壮观,又像一架翠屏横亘东西,一览无余。山峰上那个大圆球更是清晰可见。歇息一会儿,待汗水消了,大家却都不愿意动身了。
沿着山脊,我们又爬了一座小山头,通往玉函山主峰的那道拦路虎——小断崖出现在眼前。断崖高五六米,石壁直立,令恐高之人望之胆寒。早先未修通往山峰的栈道之前,不敢爬断崖之人皆至此无奈地返回。我前两次都从此登上去的,我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胆量了。这次我决定沿着栈道绕过去,无非多走点路罢了。
过了小断崖,又爬了一道较长的陡峻栈道,就登上了玉函山主峰东北面的山峰了。山峰上悬崖边有一处滑翔伞运动基地,一伙滑翔伞爱好者有的正在蓝天上翱翔,有的正在准备起飞,大家都很羡慕。
看着最后一架伞升空后,我们沿山顶水泥路一会儿就到了主峰——帅旗峰下面,也就是那个大圆球跟前。至此,大路没了,我们沿着松林里的羊肠小道,迤逦往后山而去。
据史料记载,宋代曾于主峰上建了一座泰山行宫,又叫碧霞元君祠,民间称作泰山奶奶庙。现仅存南天门和三大殿其中的一殿——三教堂。三教堂为一座4丈见方的无梁殿,其形似一座古塔,全用巨石砌成,门额有名“三教堂”。明清两代,每逢夏历4月前后,山上举办庙会,香客云集,烟霭缭绕,颇为热闹。现在大殿在军事管理区内。
走出陡峭的松林小路,忽然就下到了悬崖边上。居高临下,俯瞰峭壁,危崖临空,深渊万丈,令人胆战心惊。
沿着崖边西行几十步,松林之中出现了古道。古道宽一两米,石条铺陈,残损不整,蜿蜒向下,幽邃沧桑。这条古道显然是明清时期附近百姓上山进香的攀路。道内侧崖壁峥嵘,怪石嶙峋,不可名状;道外侧古木参天,藤萝缠绕,参差披拂,犹如原始森林。那次我自己走到此处,山野无声,林木不言,一片死寂,吓出我一身的冷汗。下到佛峪寺上面,忽听旁边树林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猛一抬头,见是一对男女。那女人也发现了我,喊道:牛哥!我也看清了那人面貌,原来是一位曾经一起爬过山的驴友。驴友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在家闲着没事,出来溜腿。闲聊了几句,他俩继续上山,我则下了佛峪。
下到半山,道旁峭壁上忽见石刻一幅,开头一句话勉强可辨:“乾隆四年……攀路……”后面字迹多漫漶不清,仅有小部分字迹尚能辨认,如“济南清军”、“山东右营把总”、“山东左营千总”、“仲夏”等等,由此判断,这可能是记载清军重修攀路的功德碑。石刻下面几步之外还有古碑一通,开头“济南府”,中间“三百五十”,末尾“大清”尚能辨识,其余字迹已漫灭难认,我认为这应该是清代先人修建攀路的碑记。
继续下山,驴友老丁在不断弯腰拔一种野菜,我却不认识。老丁告诉我,它叫紫花地丁,拌了吃,打汤喝,都很好吃。也是味药材,清热解毒,能治疗几种病呢。我们群的植物专家书亭看了说,这野菜叫山茄子。他们俩究竟谁说的正确,一时不好判断。下山后我查《形色》,还是老丁说的对。书亭说的也不一定不对,可能这种植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吧?
到佛峪寺遗址西面,道旁有小屋三间,坐北朝南,另有一座坐东朝西稍矮的尖顶小石屋紧挨着。屋前山坡上有古碑三通,一字排列,从西往东碑头依次刻有“万古流芳”、“代粮碑”、“碑阴”几个大字,皆依稀可认。从能辨认出的内容知悉,这是明清时期重修三仙宫灵官庙的碑记。不过眼前的小屋内已无神像,甚至连个门窗也没有,房顶像是新更换不久的铁皮,能遮挡风雨,有点不伦不类。小屋下面还有一层,屋西侧有一入口,我们偻腰而入。室内东、西、北各有一门洞,皆发碹,青石砌就,东、西门洞皆条石封堵,唯有北门洞敞,北望可以看到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却不知此屋原来做何用场。
小屋西面悬崖边有条东西向的小路,靠崖壁有一泉池,青石砌就,一米见方,半池泉水,清澈见底。上次结伙来,我们曾遇见两位村妇在此搬运砖头,村妇告诉我们这就是鹁鸽泉。问其所以,皆摇头不知,说村里老辈人都这么叫。这次来,我沿着两条小路寻找鹁鸽泉,却怎么也找不到了,真是奇怪!记得沿东西向小路,往西约百米,有一处弧形巨岩,离地四五米高处岩壁上赫然刻有两个金色大字:佛峪。字迹刚劲有力,出手不凡,只是落款处模糊不清,不知道是何人的手迹,有点遗憾。
小屋后面路边灌木丛多为黄栌,现在有部分叶子已经黄了。其实从山上古道一路下来路边也多黄栌,有的有海碗口一般粗了。记得那年秋天来,黄栌叶子正红,身处红叶丛中,别提心情有多美了。虽然现在黄栌叶子未红,但路边野花不断,有的认识,有的陌生,其中有一丛灌木,开满了紫红的小花朵,很美,以前来也没见过,因此并不认识。《形色》告诉我,她叫笐(杭音)子梢。并提醒说,此花很容易与一种叫作胡枝子的花混淆。胡枝子花跟笐子梢很相像,但有一区别很明显,就是胡枝子花根部有一紫斑,笐子梢花没有。正是:一点小区别,名字非一家。又识两种花,此行乐哈哈。
灵官庙东南百米远处也有段弧形巨岩,似乎与西面那段弧形巨岩相对称,长六七十米,上面凸出部分离地高约四五米,外伸一至三米,状如重檐,下面形成一个天然的巨型佛龛。“檐”下石壁上镌刻有近百尊佛像,上下共分为五层,有的站姿,有的坐姿,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排列整齐,阵势壮观,为济南地区罕见的隋代摩崖造像群,可以与四门塔千佛崖隋唐造像群媲美。佛像身躯均基本完好,线条流畅,衣袂飘飘,雕琢精美,只可惜佛脸皆遭到恶意毁坏,没有一尊是完整的,令人痛惜,也不知道是何人何时造的孽。更为可笑的是,不知何人用水泥给那尊最大的佛像造了张假脸,却一分像佛,九分像鬼,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
石刻不多,仅见几小幅,皆几十个字,其中一幅有“开皇八年……“的字样,为隋代石刻,大意好像是某某为母造像,这可能是西佛峪早期的石刻吧。另几幅因在高处,且年代久远,多数已经认不出几个字了。从能够辨认出的字迹来看,线条古拙,潇洒遒劲,令人赞叹。
巨岩之上,杂树丛生,蒙络摇缀,阴翳蔽日;巨岩之下,弧形石台,宽敞平整,浑然天成。佛峪寺遗址就坐落于此,可惜现在主庙连点遗迹也没有,仅剩下个空名了。
石台下是一条南北向的深谷——佛峪。坡陡峪深,松柏森郁,一眼望不到头。石台两端靠崖壁各有一门,北向,青石垒砌,红瓦覆顶,隔谷相对,与农家老式院门相似,却显然不全是古迹。
月台西面崖壁下有眼泉,泉水从岩顶珍珠似的往下嘀嗒不止,落在下面的池子里,清脆有声,这就是蕊珠泉,可以与历城区云台寺的玉漏泉相媲美。泉池水满外溢,清澈见底。驴友老丁问,这水能喝吧?大家说,还是别喝了,不放心。老丁蹲下洗几把脸,说,好清凉啊!
2023年9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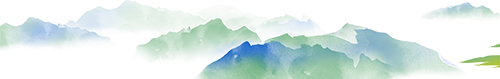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