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有多大
作者 辽河之子
小时候的家,是两铺土炕,三间草房,四分儿园田。土炕常常倒烟,草房总是漏雨,而园田则教会了我初识桑麻。土炕上,妈妈总是缝缝补补,累了针线,倦了灯花。春天的房檐下,燕子会按时飞回,一年又一年,去而知返,不嫌家贫。园田里,爷爷奶奶劳作的身影,早已剪纸般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镇上读中学,一天40里乡路,没有自行车,就靠两条腿。不住宿,一是住不起,二是想家。放学后,一到村口,心里便说“到家了!”
那时的家,是一个方圆几里的小村。村里有一条小河,两个池塘,四口老井,三百人家。河虽小,却教会了我横渡辽河,畅游大海的本事。池塘不大,在那儿,摸鱼、打鸟、溜冰,我贫苦的童年便充满了晶莹的笑声。井虽不深,水却清亮,有乳汁的味道,人喝,牲口也喝,天地和谐,水乳交融。三百人家,种姓杂糅,彼此照顾,相互扶持,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清贫而却温馨的日子。

上大学的几年,每年两个学期,是两截浓浓的望乡之苦。火车刚一进站,人便有了落地的感觉,心微微一疼:到家了!
那时的家,是一个叫开原的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常吹嘘它的饭勺子和铝锅盖,吹嘘老城的蒜业民的葱,吹嘘那个只有几只猴几对儿孔雀的公园。后来才知道,这时我的家有3000多平方公里那么大,家口好几十万呢!
去中原行走,到江南游历,蜷在京城居住,听到一句关东话就热透中肠,见到一个关东人就要干上两杯。折回的路上,车一出关便一声轻叹:到家了!

那时的家,它的名字叫东北。山河三千里,人民一亿众,不分辽吉黑,秉性一锅同。呼伦贝尔就是俺家的西草甸,大兴安岭就是俺家的后花园,松花江就是俺村的河汊子。大风雪、大平原、大脾气、大嗓门儿、大胸襟、大气魄,怎一个大字了得!
去国外旅游,一出国门便失魂落魄,想家。四处找中国餐馆,见到华人就套近乎,考古般寻觅当地的中国元素。返身回来,一进海关便眼睛一热:到家了!
那时的家,名字叫中国。长城是俺家的篱笆,黄河是俺家的水沟,有两个高土坎叫青藏和内蒙古,有一个大泡子叫青海,有一个大村子叫上海。墙上供着的祖宗叫炎黄,家里有文化的是孔孟,家里的书上写的都是方块儿的字。家里兄弟姐妹有很多,小鼻小眼黄皮肤,长得其实不好看。以前曾经阔过,是天底下的大户人家。眼下正行走在复兴的路上。
家,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家,其实就一颗心那么大!

作者简介:辽河之子,本名周惠民,锡伯族,辽宁省开原市人。渤海大学物理系毕业,当过教员和公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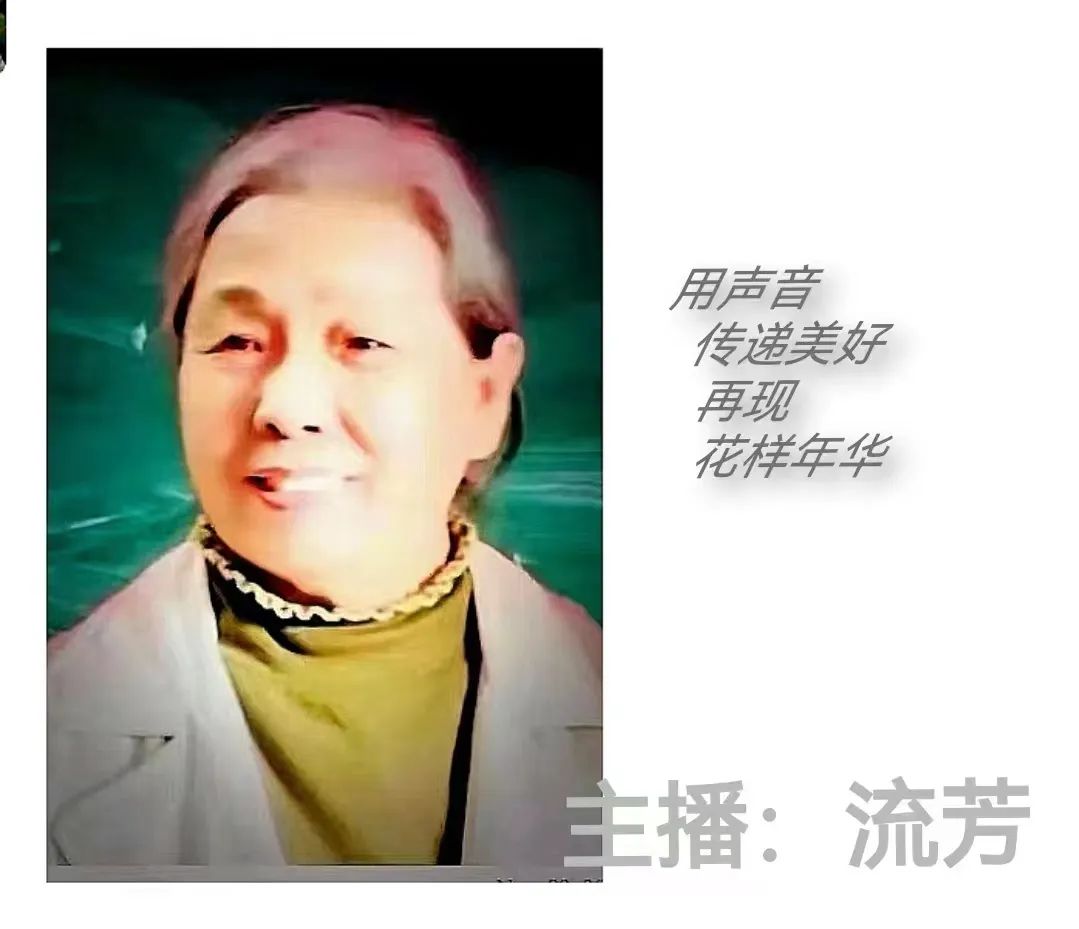
朗诵者简介流芳,本名王流芳,网名小潴姥姥,退休的人民警察,酷爱朗诵,北京花样年华女子朗诵艺术团团长,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会员,中国互联网朗诵联盟会员,喜马拉雅FM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