楣子下乡记
王广杰
1970年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没有了留城的指标。兵团开始报名,楣子可想穿上军装,享受一下那种绿军装下,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但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怎么会有这种待遇?楣子失落的等待降临她头上的命运,到山西去插队落户。听楣子说:学校安排她和另一个同学负责带队。好多同学听到她到山西去,纷纷报名和她一起走。
但是去向的改变,确从母亲关门那一刻开始。母亲拉上窗帘,掩上开着的房门,顿时泪水哗地流下来了。楣子命运也从那一刻开始,另一番知青生活。阿楣:你爸爸和你奶奶遣送回老家了,你再去山西,叫我这个当娘别分两股肠子了?就这样阿楣到学校开了介绍信,回老家联系办理原籍插队落户了。
楣子没有享受敲锣打鼓贴“喜报”,蔫蔫坐长途汽车来到了安宫县,当她下车那一刻惊呆了,爸爸带着大白绣箍上面公公正正写着“反革命右派臭地主孝子贤孙”,楣子眼泪一下子向提了闸的河水涌了出来,她知道这就是她一生的归宿“右派分子孝子贤孙”。可她父亲丝毫确没有任何表情,一切那么自然没有任何不快。爷俩回到村里,奶奶站在高跛上也带个大白布黑字袖箍迎接孙女到来。
进了屋右边是砌得炕,左边是房东存的白茬寿材。一个放碗筷旧橱柜就是她们家全部家当。吃饭只好把碗放在炕上了。楣子每天躺在寿材盖上就寝了。
扛着锄头下地,大队钟一响爸爸、奶奶和她就出现在社员堆里了。楣子也开始认识这个奶奶那个爷爷,都是没出五伏的亲戚。
下乡不久机会总是留给早有准备的人,村里排练文艺节目。上台对阿楣来说是天赐良机。指挥一群农村年轻人唱歌正中楣子下怀。想当初楣子在学校里是“校花”,因为她爹是“右派”,好几次面试被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其中包括文工团。每次学校上街演出,演出前红卫兵基干连负责人,把红袖章让她戴上,演出结束后就让她交回。这个节一直在楣子心里多少年。
杰出的表现引起了公社书记重视,楣子被调到公社挖河工地上当了广播员。
一步登天楣子成了“名人”,十里八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楣子的精明也让我佩服五体投地,当时社会时兴“假领子”,楣子虽然在父母不在身边时学过缝纫,并且一天拃两条裤子,挣过每天3元钱收入养活弟弟妹妹。但事过境迁做假领子她也买裁剪书,学习裁剪做“假领子”,楣子假领子很快在村里占领“市场”,村里人请楣子做“假领子”,农村人给楣子包饺子做面条酬谢楣子,她就顺手带给奶奶、爸爸打牙祭。楣子刚到村里下地看到父亲一个人割麦子,一个做学问人拿镰刀,简直是舞台小丑滑稽可笑。地里人割完一行在地头歇着拉家常,她爸爸抹着汗一噘一噘。楣子就下决心一定改变这种宭迫。插秧楣子来历夏了,楣子带着女人最难熬的娇贵,溜着月经血趟在水里,经血流在身后秧苗里,但和村里人速度不相上下。随着楣子能拉呱这个婶那个叔喊得哪个近,由刚开始楣子接父亲到后来变成大家一起接父亲。队里也安排父亲干些轻松农活了。
小品“换鸡蛋”,妹子演绎淋漓精致。随着楣子和村里人交往,她为别人帮这帮那忙。谁家养的鸡下了鸡蛋都给楣子拿几个,一来二去鸡蛋攒多了。楣子背上鸡蛋回到天津,这家送十个那家送十个,谁收了楣子鸡蛋就回送给楣子几斤面几斤米,楣子又把这米面捎回村里分给乡里乡亲。楣子讲起这段经历来眉飞色舞神奇的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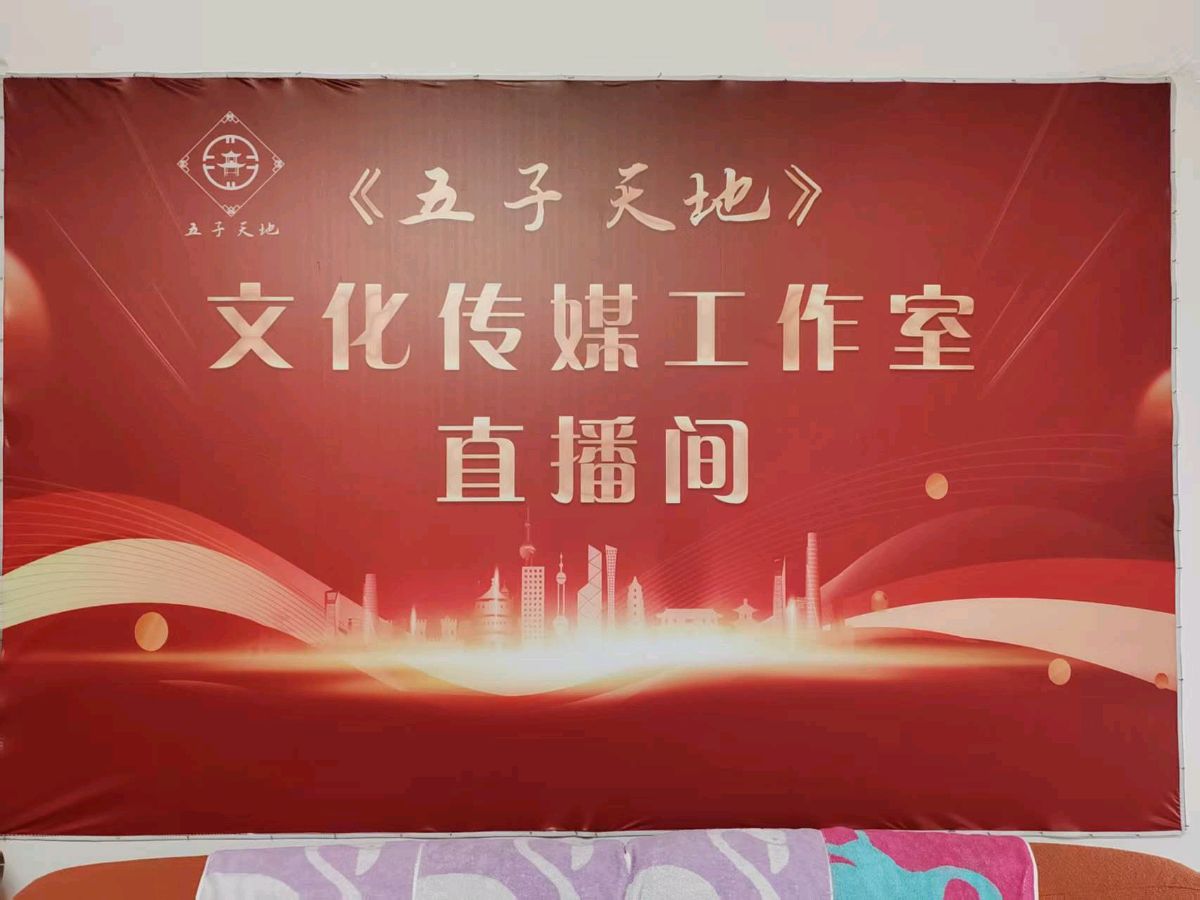
撰稿:王广杰
微刊制作:五子天地文化传媒工作室王广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