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世间风情】《心劫》连载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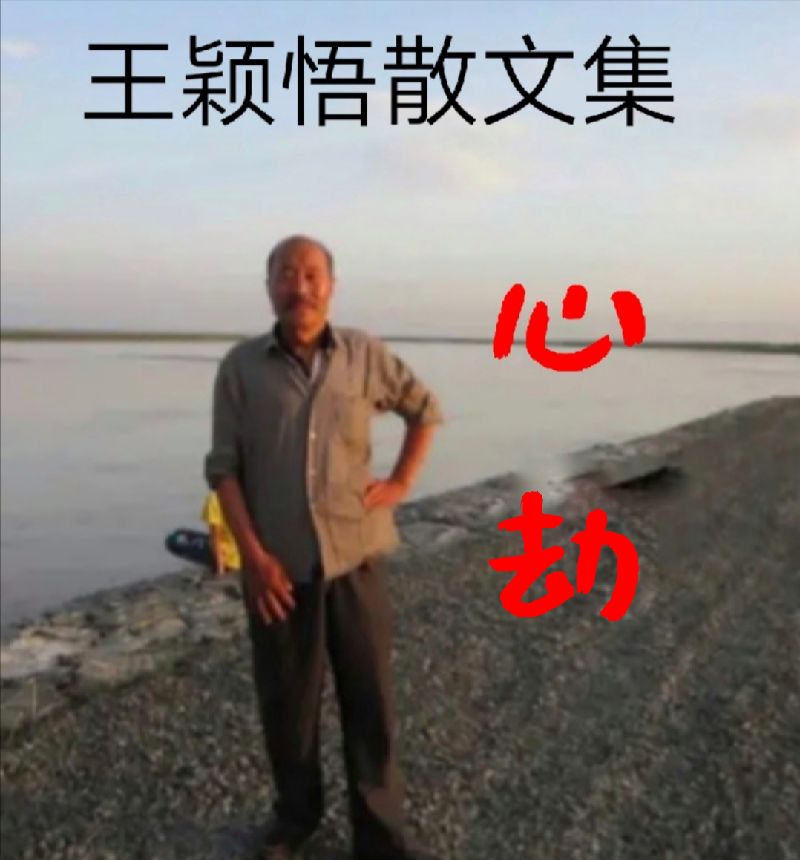

风雪东方谷
东方是麟游的一个乡,东方谷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山谷呈东西走向,沟底有一条弯弯曲曲近似干枯的溪流,沿河床两边散落着数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零星田块。一簇簇立在地头金黄色的玉米杆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收获完毕,播种的冬小麦在微风中摇曳着嫩绿的细叶。
在前方不远处的山崖下,坐北朝南并列着两大一小三孔窑洞。大窑洞是住户的卧室灶房,一孔是磨房及牲口圈,另一孔小窑洞是存放柴草和杂物的。窑前没有围墙,只有几株落尽叶子的树木,像卫士般忠诚地终年护卫着它的主人。
户主姓刘,名字不祥。别人称呼他“刘组长”。组长这个官衔在我们这些山外人的眼里微不足道,而实际上他是这方园三四里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管人、管地、还兼管钱粮。靠西边散居的四五户山农,划为一个组,总共二十几口人,都是他的子民,其权利之大无可比拟。反正这地方山高皇帝远,一人说了算,公社干部一年半载也难得来上一回,谁也懒得去管那些穷乡僻壤的琐碎杂事。
刘组长年约四十,中等身材,精明干练,眉宇间透着一股山民们少有的英武之气。后来得知他原也是山外人,解放前为了逃婚才与媳妇双双私奔到这里来,多亏这家老夫妻好心收留,从此隐姓埋名过起了安生日子。膝下一女年方十岁,老爹去世唯有老母在堂。一家四口,也算平安康乐。
垦荒大军的总部就设在这家住户的柴窑里,砍树搭屋,支起了一个可以盘灶做饭的简易大棚,可是这七八十号人的住处却成了问题,尤其是天气渐寒,隆冬将至,总不能让大伙露宿在院子吧。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刘组长的带领下,沿着沟沟坎坎,到处寻找过去先民们废弃的旧窑洞。这里安插三、四个,那里挤进五六个,就这样化整为零,将一个整体的垦荒大军撒落在荒山野岭之中,使这个亘古冷清的不毛之地处处呈现出生机。
由于住地分散,难以管理,最远的住地离总部有四五百米,况且沟壑相隔,上下难通。为了方便,只好以吹号为讯,早、中、晚上工、收工、吃饭皆以号音为准,实现了所谓的行动半军事化,又仿佛进入了大跃进时代。
要开的荒地其实就是半坡上的乱石滩,那里蒿草一人高,稀稀落落长着一簇簇狼牙树。此树是一种多年生灌木,身上长满毒刺,一不小心划破皮肤就会发青肿疼,奇痒难耐,因此吓得人们不敢碰它。要想开荒,就得先清除这些拦路虎,大家常常为了挖掉一棵狼牙树,几个人合伙干上半天,累得汗流浃背,这样就势必影响了开荒进度,因而受到了王领队的批评。——其实王领队原是大队里的一个副职,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这次进山开荒明知是苦差使,别的领导不愿来,才轮到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以为是垦荒总指挥,便趾高气扬地吆五喝六,指手划脚,扮演起了领导的角色。
然而真正影响进度的不是活累,而是人们在饿着肚子干活。进山前的美好憧憬被十几天来的现实击得粉碎。我们吃的是本地产的粮食,但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七两玉米,七两是什么概念?七两就是双手一掬。这是县上和公社规定的硬性标准,任何人不得逾越。在当时那种无任何营养补给的情况下,只靠这点粮食,能够保住饿不死人就已经是奇迹了,哪里还有力气上山下沟开荒干活呢?
上工号、收工号照样吹,挨批评、听训话天天依旧。王领队把刘组长的母亲认作干娘,住在了刘家大窑的热坑上,反正人家不挨饿不受冻。一月的开荒期限要坚持到底,不然回去后难以向上级交待。当时有些人捱不过饥饿,想要逃回山外,但怕被发现,被队里来一个“扣发口粮”的处罚,全家人将受连累,只好忍耐下去。
由于是湿玉米,磨不成面粉,上磨子以后,再加些水就像磨豆浆一样,下到锅里一煮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玉米糊糊。锅上面漂满了一层玉米皮,第一顿还好。黄黄的有一种玉米的清香味。第二顿就变成了粉红色,好像谁在里面撒了些红染料。后来才知道这是磨好的玉米糊发热变质的缘故。即就是如此,每次开饭时争先恐后,你拥我挤,生怕轮不到自己。端上饭碗就着有盐没醋没辣子的水煮白菜,狼吞虎咽,如同是尝到了山珍海味。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孔老夫子说过的“故此君子远庖厨也……”,他老人家可能是没有受过饥饿,吃不饱饭常饿肚子的人永远成不了君子!
可别以为,大伙吃的粮食是用牲口磨成的。那可是我们汗流浃背轮流推磨的成果。两人一班,整日不停。山里啥都稀少,只有一样不缺,那就是漫山遍地的硬柴。收工时,每人顺便捎一些就够大灶烧几天,只可惜有锅有柴却无粮米可煮,白白的浪费了这上好的丰富资源。
冬季时令,昼短夜长,饥肠辘辘,夜晚最是难熬,难以成眠,只好烤火取暖。这时有人说话,白天路过一片油菜地,顺手挖了一棵蔓菁边走边嚼,香甜可口。他听老年人说过,此物在过去年馑时,曾帮人度过难关。说着就带着两个小伙,顺着来路趁夜黑摸了上去。不一会,三人顺利归来,装满了一小口袋蔓菁。借着火光,我们抖掉泥土,用小刀胡乱切碎,借了人家一个马勺,管不了脏净,用沟底小溪里的水稍事冲洗,便架在火堆上煮了起来。不等煮熟,大伙便迫不急待的吃将起来,虽然每人只有几口,但却使我们这个小窑里同住的六个人度过了一个难熬的漫漫冬夜。煮蔓菁的清香在土窑里弥漫了好长时间。
最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就发生在此后不久,虽然已过五十余年,但却令我刻骨铭心,永难忘记,当时景况历历在目。
我们同住的六个人私下凑了一点钱,去向另一家住户买了些玉米面,并委托主人为我们烙成碗口大的饼子。怕走漏风声,大家推举一人去办。饼子烙好以后,趁着夜色拿回我们的住所。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望着香喷喷的饼子馋涎欲滴,个个瞪大贪婪的目光,生怕被别人抢了似的。有的人已经在咽着涎水。每人分得一个后,偏又剩下一个,使人犯了难,一时没了主意。庄户人最厚道。要是在平常年景,即就是毫不相识的过路人,若到饭时,不论走到谁家门口都会让你吃个饱,临走还会让你捎上一天的干粮,可是如今不同,对于每个早已面露菜色的劳动者来说,每口饭就是一分力气,就是活下去的希望。这也难怪大伙斤斤计较,实在是时势所迫,大家都吃不饱饭,人人都是一副穷酸相,再也难以维持那种同舟共济、宽和相让的谦谦君子之风。一个玉米饼六个大男人怎么办?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我耍了个小聪明,用数学几何上学过的圆周六等法解决了难题。切开的玉米饼六块一样大小,不偏不倚,大伙都露出了艰涩的微笑。有人说,还是念的书多了好,就是比别人聪明。我听了这个话觉得怎么听也不顺耳,就象万把钢针刺痛了我的心。是赞扬、是嘲讽或者是兼而有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难道就是我苦读一十二载唯一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发挥得这样不合时宜,这真是对“知识”这个神圣名词的最大亵渎,我自愧,我内疚,我感觉无地自容。此后几天我都沉浸在情绪极度低落之中。
阴云密布,寒风呼啸,纷纷扬扬下起了一场大雪。我们住的是人家废弃不用的窑洞,无门无窗无遮掩。初来时略事打扫,用玉米杆堵住窑口权作栖身之地,平常时节还可奈何,然而如今寒风刺骨,卷起的雪花飞进窑洞内,冷衾如铁,难以入睡。我们六个人只好拥被而坐,团团紧靠,互相取暖而眠。一夜囫囵觉,醒来已红日当空,但见日浮东方,好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对此良辰美景,我们却无心欣赏,此时却更觉寒气逼人,饥饿难耐。决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那种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这也真是辜负了神州大地上的多娇江山!




